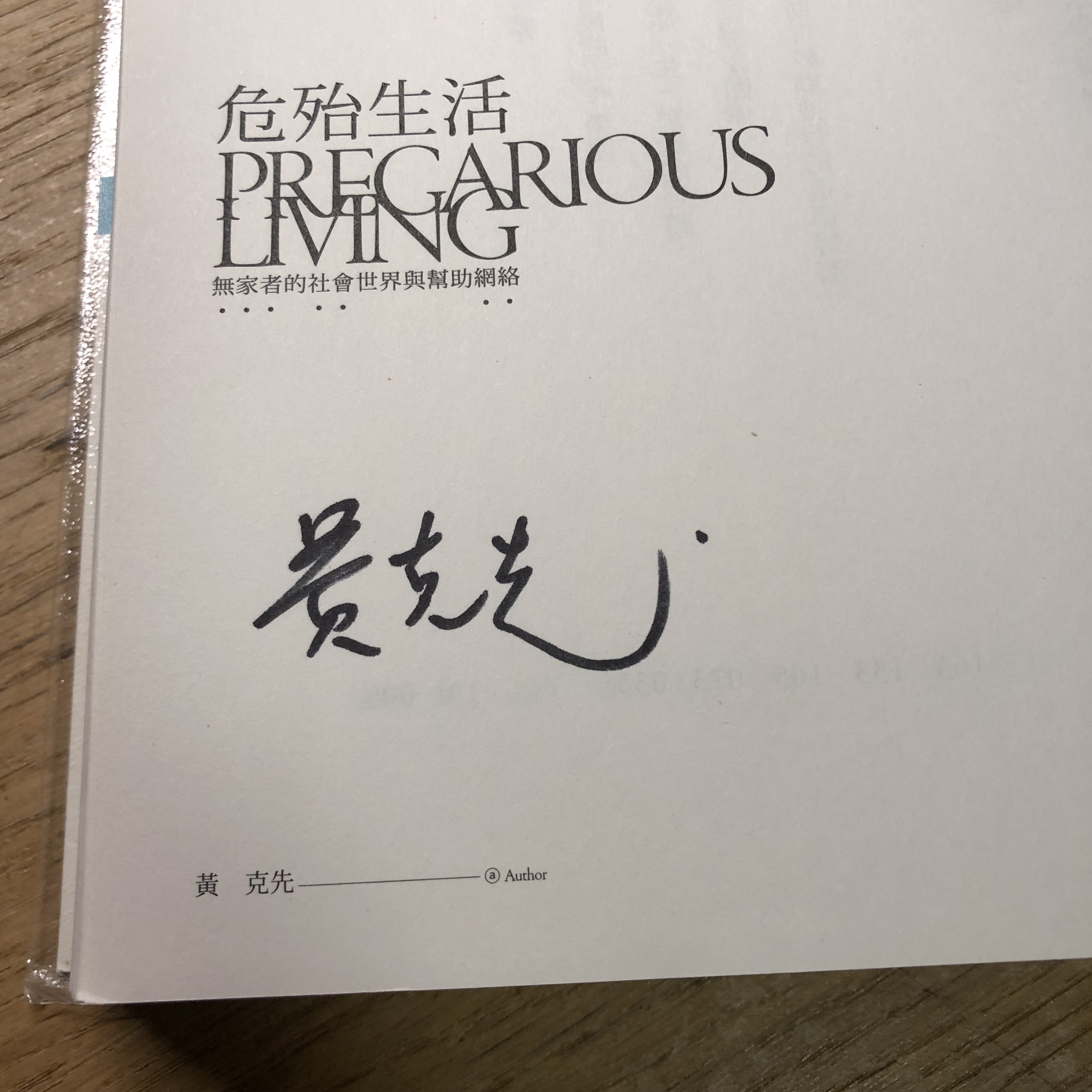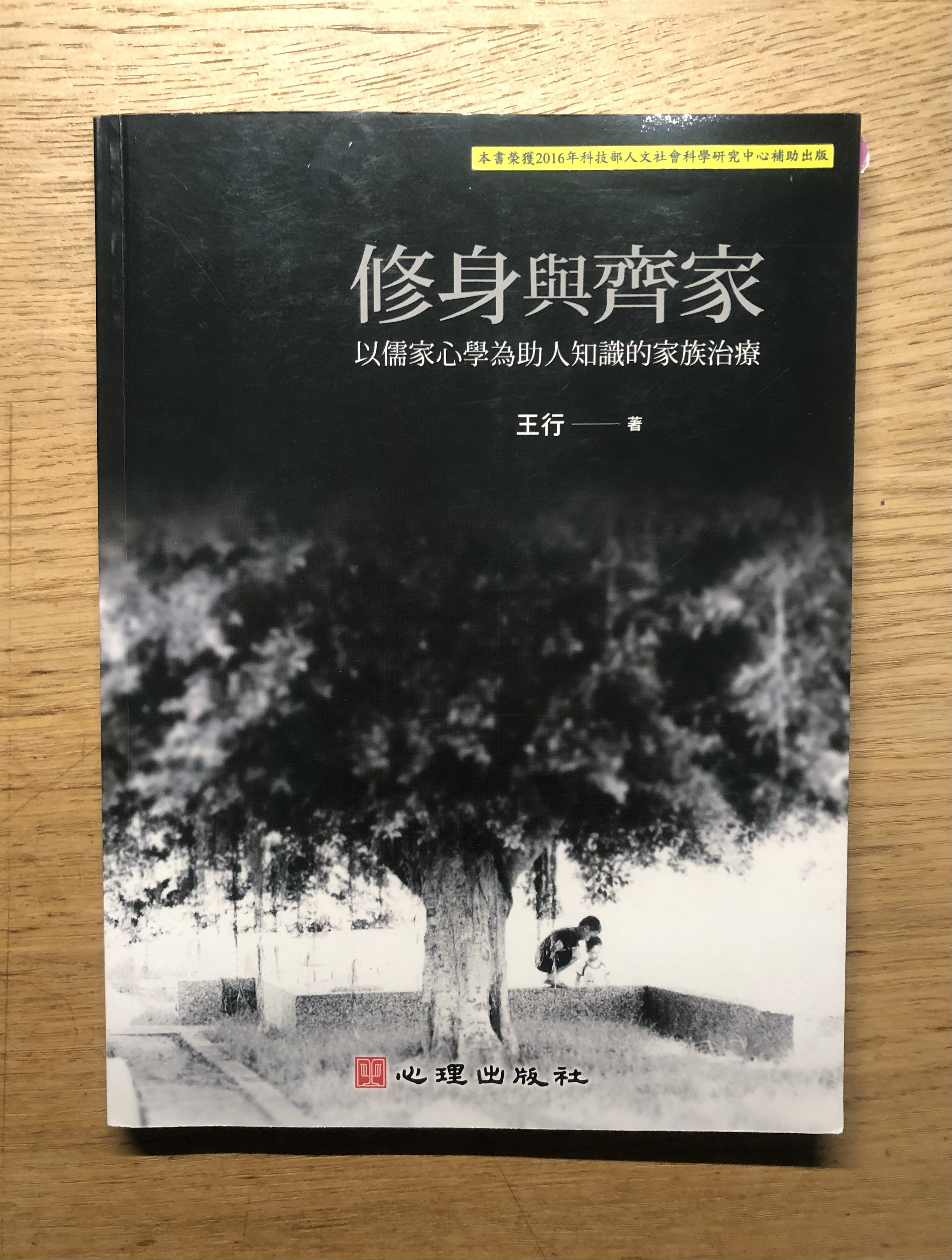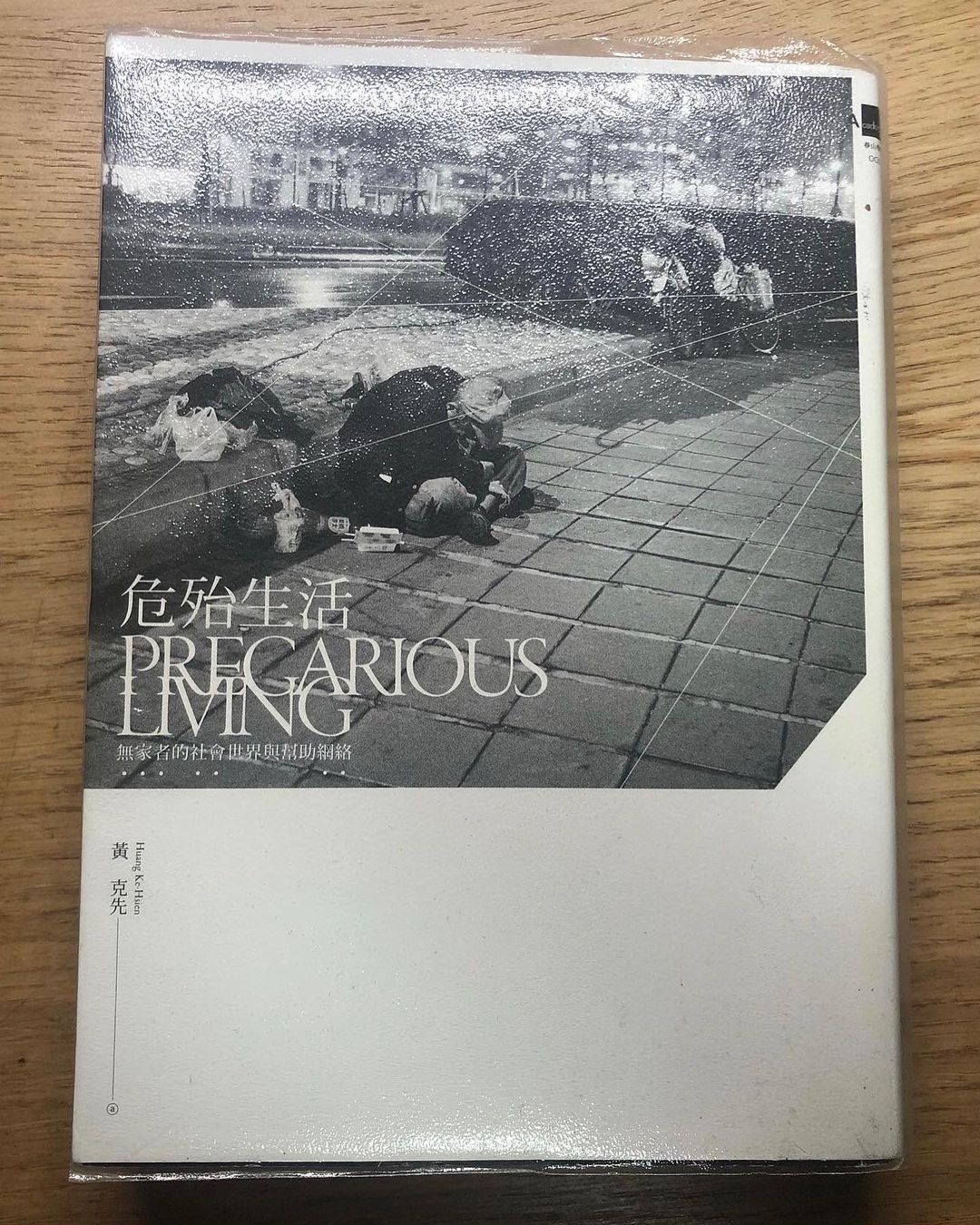
讀完黃克先老師的《危殆生活》之後,對於無家者又有更深入的認識,也有許多值得思考的部分,尤其是社工、善心人士、宗教團體構成的幫助網絡,在「助人者—受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助人行為帶來什麼樣的副作用和「交換」?書中呈現各種無家者日常生活的「連帶(ties)」,也就是所謂的連結,這是在社工的視角裡難以見到的,也是我覺得這本都市民族誌特別珍貴的地方。
一、流浪背後的原因—「家庭因素」
最近剛好整理國內無家者研究文獻,大部分探討流浪成因時都會提到流浪與家庭因素有關,但究竟家庭因素的內涵是什麼呢?作者的觀察就梳理出「傳統漢人親屬關係」的文化以及父權體制的家庭如何一步步使人離家。
在很多例子中,無家者與原生家庭的連帶雖維持了下去,但因為無家者的經濟不佳,或是生活形態放不進家庭傳統意識所設定的模型,使這個連帶變得特別脆弱。像是父母過世後原本同居相互照料的手足,因為小磨擦而走上分家;嫁出去的女兒又回到娘家,原生家庭卻無法再像以往那樣接納她為家中的一員。P.102作者用「後父母時代」去描述無家者是如何在父母過世後,從原本手足的支持下主動或被動離家,與家人維持一定的距離,或是直接斷裂。書中也特別談到女性無家者的處境,在父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文化底下,如何受到「家庭」的壓迫而流落街頭。
二、無家者不同的狀態
很佩服作者的是,他把無家者大致區分成三種狀態:𨑨迌人、做事人、艱苦人。我覺得這樣的區分有助於討論不同狀態的無家者,畢竟各自的困境都蠻不同。在公園的確會發現每個人的狀態可能非常不同,有人想要工作、有人想要喝酒、有人想要聊天,也有人困於自暴自棄、習得無助感的狀態,或是身心條件的不利,又呈現更弱勢的狀態。
𨑨迌人是具有江湖資本且身心狀態佳的無家者,做事人則是不具江湖資本且身心狀態佳的無家者。隨著年齡增長及流浪的惡劣生活條件,上述兩類人身體或心智狀態下降,將成為艱苦人。艱苦人中的「前𨑨迌人」因其江湖資本,往往能在小團體裡占據領導、對話(如與社會局社工、慈善機構人員、教會牧師)溝通或仲裁的角色,至於不具備這類資本者的「前做事人」,則在團體中擔任被動配合指令的角色,使他們的生活會更著重在節流上,行為模式較為保守,不願有太多體力的耗損或額外的開銷。P.59
我也發現,當我們在討論貧窮或無家者議題時,由於每個人都以自己接觸、理解無家者的經驗為基礎來表述,但這些經驗經常是零碎的,最後變得像瞎子摸象一般去拼湊,討論難以聚焦。以作者的分類為架構,在理解每位無家者的狀態時更容易有所依歸,去理解他處於此刻的狀態/心態背後的歷程可能會是什麼模樣。
三、無家者的幫助網絡
在書中的第二部分,作者整理了無家者的三種幫助網絡:宗教、社福體制、「善心人士」。有趣的是,作者把重點放在這些幫助網絡如何造成對無家者主體造成影響甚至傷害,一般人印象中善意的助人行為,背後存在著減損無家者尊嚴、形塑主體的效果。
無家者與構成幫助網絡之鐵三角—宗教、國家、「善心人士」,各自因助人者隸屬的更大組織脈絡不同而影響其助人動機,因此連帶的運用方式及效果也同中有異,但共同點在於象徵上彼(助人者)長我(無家者)消。宗教團體建立的連帶,運作目的是以信仰體系設定的理想信者為準來模塑無家者的主體,無家者若想接受幫助就需自承行為有瑕疵並改變「惡習」,而這過程傷害他們的尊嚴,而宗教無形力量在信者的改變中,被權威聲稱得到了有形的確證。社福體制的社工與無家者建立的連帶,並未以滿足無家者真實所需為前提,而是實現政府設定的治理目標為依歸,這些目標多在鞏固社會主流價值,包括維護家庭、奉行工作倫理、維持整潔的都市空間等。無家者接受社工運用個案管理以挹注資源的被收編過程,他們或配合政府改變生活型態,或成為社福體制的末端協力者。相較於宗教,無家者與社福建立的連帶不見得會威脅到個體尊嚴,但該連帶對無家者之間連帶的傷害卻更加明顯。與「善心人士」建立的連帶,為塑造助人者的道德光環或滿足其自身對誰值得受助的偏見,在運作中使無家者被當成襯托的背景或被審查的道德可疑份子,在一次次的互動中創造了道德優劣的階序。P.263
從上述書摘可以發現,作者從無家者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幫助網絡背後帶什麼樣的動機和目的在「助人」,又帶來哪些影響。書中的第二部分指出,宗教、社福體制、善心人士分別是:模塑主體的連帶、鞏固主流價值的連帶、創造優劣階序的連帶。這樣的觀點打破一般人對於「助人者帶來好的幫助」的想像,讓人重新思考助人行為究竟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四、暗處中的微光:無家者彼此之間的連帶
另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作者呈現了艋舺公園當中無家者彼此之間連帶、擬家關係和伴侶關係。不同於一般人想像無家者是自利的形象,作者發現艋舺公園裡有許多互助關係。這些建立在江湖道義、道德經濟上的互助連帶,是無家者積極生存的證明,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無家者並非只是孤苦無依的貧窮受助者,而是如作者所言,有各式各樣的需求,並且為了滿足這些需求有所行動。
在主流媒體上呈現的無家者,似乎在成為無家者後就失去了愛人與被愛的能力,甚少看到他們在「努力工作/孤苦無依」或「惡毒加害/可憐被害」之外的形象。偶爾出現相關的新聞,愛也只停留在流浪之前,而流浪後遇到的偶現愛情不過是虛假的,只是金錢掩蓋的利益競逐。事實上,無家者來到公園,他們試圖與周遭他人連結,擬仿主流社會的婚姻及家庭制度,打造私領域的連帶。從這樣的連帶創造,具現無家者並非被動乞食的存在,而是與你我一樣,有著如情感依附、心理支持、性、渴望、尊嚴等真實的需求。他們積極地創造連帶以滿足這些需求,相互陪伴與支持。在這些當下的行動裡,體現真實的人性與自己的謀生邏輯,同時展露過往生命經歷或回憶的持存影響。P.130
在做事人流汗講著自己「有格」時的驕傲神情,𨑨迌人敲敲頭慧黠地暗示賺錢要用腦袋,以及老邁的艱苦人緩慢訴說歲月教會自己的生活哲學時,我們都見證了他們在物質匱乏下仍驕傲活著的痕跡。即使與幫助網絡互動中為了換取物資,必須承受尊嚴受損、服從主流價值、地位下降的代價,但無家者們仍展現主動打造獨特信仰樣貌、與權威者共作、自助助人者的能力。透過靈活的生存策略室應環境並解決實際問題,也是他們能積極回應外在環境的證明。他們並非單純被動地以受害者身份或姿態活著。 P.280
五、無家者更立體的樣貌:豐而危殆的連帶
綜觀整本書來看,我認為《危殆生活》呈現的不只是無家者真實日常生活的面貌,更深入探討了無家者在脫離流浪的困境,像是幫助網絡帶來的副作用,社福體制難以滿足真實需求、或是父權家庭體制如何造成壓迫和排除,這都成為流浪生活的重重關卡與壓迫。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也梳理了無家者另一個樣貌,也就是在媒體的視角之外、社工的視角之外,究竟艋舺公園存在何種社群和互助關係。
作者強調,這些社群連帶與互助關係是「豐而危殆」的。儘管無家者之間的互動與連帶很豐富,但在資源匱乏的環境裡,也會容易出現猜忌懷疑、弱肉強食的現象,使得無家者之間的連帶變得脆弱易斷,因此是「豐而危殆」的。
無家者彼此間的連帶雖豐富,讓他們得以有效率地交換資源並構築家空間,但也因為物質基礎匱乏,露宿公共空間帶來的不確定性、未依附社會制度而能獲得其支持等因素,而顯得危殆。同時,公園與無家者的社會污名,不僅如前述使個體在日常互動或面對體制時因被歧視而減少生存機會,也讓無家者之間僅有的資源來源—相互的連帶—變得脆弱易斷。在這樣的外在條件限制下,無家者不喜歡在勞動時與同儕建立連帶,寧可獨自打拚以彰顯自身本事;原生家庭連帶雖持存但被弱化;公園內築起安全、有歸屬的私連帶,也因帶有將就的意涵而容易斷裂。幫助無家者互通有無並展現道德價值的社群連帶,也充滿較勁意味而帶著張力;宗教、國家社福體制、「善心人士」構成的幫助網絡的助人—受助連帶,雖能在物質上供應所需,卻在象徵上讓無家者尊嚴受到傷害,必須屈就於主流價值,並感受低人一等的地位。如此造成了幫助網絡提供的資源或服務,不見得輸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而真正需要的人或因尊嚴與避免污名的考量而拒絕接受。無家者若選擇與幫助網絡維持關係的話,也可能進一步掏空其自我認同的象徵資源,並使無家者之間原本張力強且脆弱的連帶更易破裂。P.284
在這本書當中,無家者不只是一般印象中的無家者、受助者,也並非好吃懶做,透過《危殆生活》珍貴的田野經驗可以瞭解到無家者如何運用自身能力與條件,在剝削惡劣的工作環境、國家的社福體制規則、在這座城市生存苟活下來。這些積極求生存的過程與能動性是過去較少,但非常需要被肯認的。
六、不完全同意的部分
在閱讀《危殆生活》時,多少對於黃克先老師的某些用字令我感到疑惑,覺得有些部分顯得過於主觀、直接,難免令我覺得這當中其實是有可以討論的空間。另外,書中有關遊民社工的詮釋也多少與我所認知的有所落差,相關段落如下:
「今天無家者之所以無家,乃因以往從不顧家甚至惡待家人。」這是「好吃懶做」外另一個常用來指涉無家者的偏見,常見於各媒體,認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長期與他們相處的社工也有類似看法。在一次的訪談中,在收容遊民機構內工作了快一年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來這邊最大的感觸,是「自己一定要跟自己家人好好相處。他們都是跟家人連結斷了。我們若發生問題,家人才會伸出援手。他們都是年輕時,沒有保持好的關係,比較自私。」然而,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無家者事實上並非「沒有或失去」家庭,只是如今失去或暫離家屋而生活在都市的公共空間,仍與原生家庭保持複雜的連帶。而他們之所以成為無家,也並非不負責任、無道德或個性冷僻的個人因素使然。P.101
阿輝隨後告訴我,平時他們幾個人一起活動,大概一週前同赴社會局,阿牧被帶入諮商室面談後就不見人影,拋下在大廳閒坐著的阿輝,他猜一定是從社工那裡拿到了什麼補助,怕出來後兄弟眼紅、分享,就從大廳後側靠牆處溜走,現在錢都花完了才回來,「不夠意思……看清楚了這個人。」這種與社工會面完就突然消失的情事在公園並不少見。
這時,公園裡對於熟悉的人不明所以突然消失,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會有上述阿輝那樣的推測,認為一定是從政府那裡拿了什麼好處就不顧朋友道義。金錢或其他福利,在社工口中是達成個案工作設定之工作目標的工具,然而也因此為原本就脆弱的無家者人際關係埋下了不安的因素。P.229
七、其他額外的思考
《危殆生活》在討論無家者的幫助網絡時,指出網絡背後為隨著不同的助人動機與目的,都有「形塑主體」的效果,也就是對於受助者有一定的期待與想像,期望可以讓受助者改變成為某種樣子。我覺得這關乎助人工作的哲學與倫理,究竟助人者與受助者雙方對於助人關係有何種想像或期待是否有落差。
經過《危殆生活》的描述,我也在想,助人行為背後形塑主體的效果是否終究無法避免?站在建制民族誌的角度來思考,任何的建制都有一套建制實在,而「建制的人為實在面」與「常民經驗的真實面」之間的落差或斷裂似乎是必然發生的。然而,我覺得這並不代表助人行為是不好的,而是更微觀看待助人行為帶來的效果,在允許的情況下,或許助人者與受助者彼此的對話、磨合與平衡是更重要的。
閱讀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