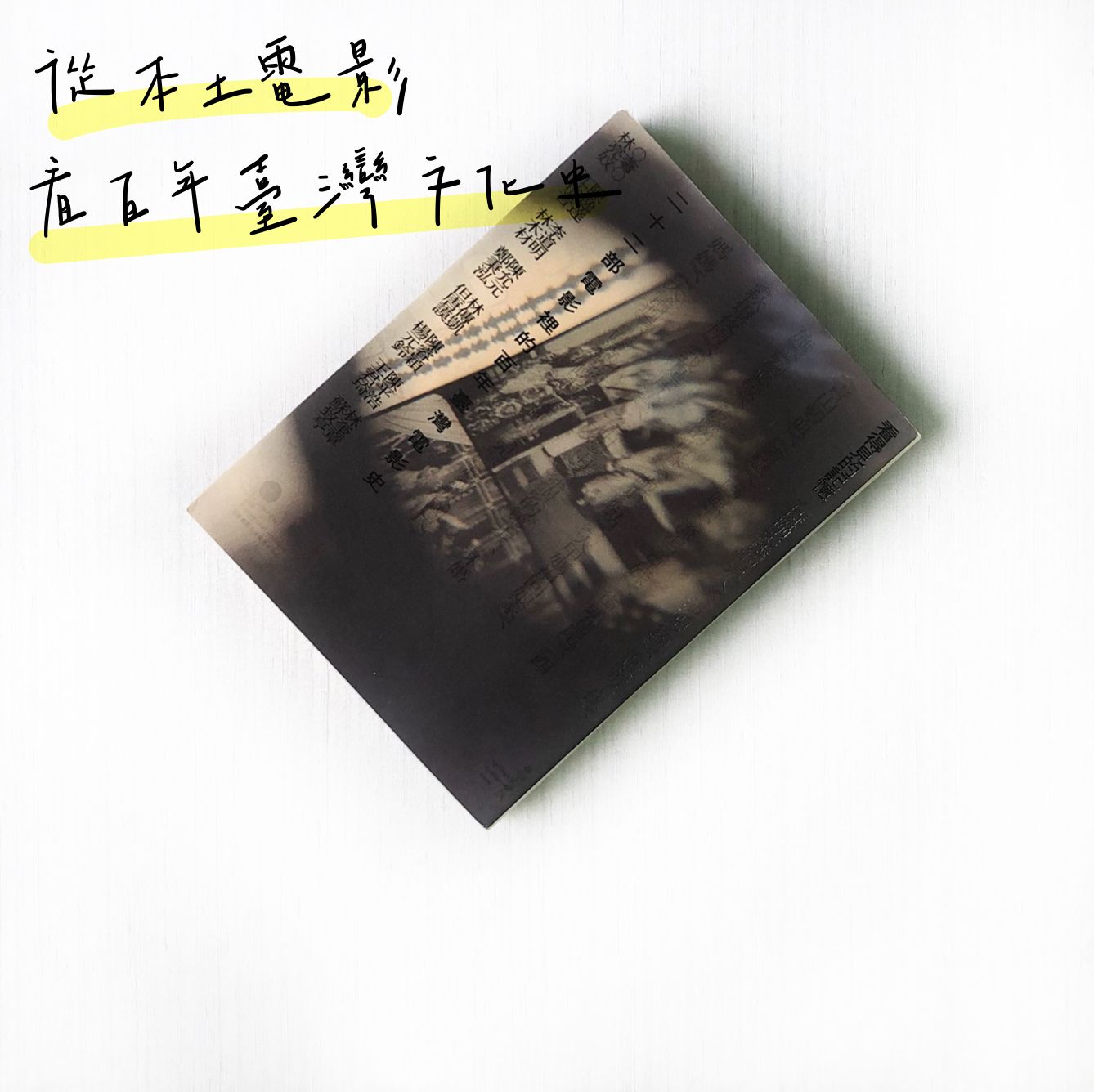為了製作這集Podcast關於曾經風靡台灣的台語片主題〈「姊妹愛上同一人,竟導致他的死亡!?」-台語片風華與電影全才林摶秋〉,有幸能夠提前觀賞這次「純情淚‧戀愛風:台語片羅曼史」影展裡的作品,為了更清楚的體驗當時的電影風格,我選擇在開始做功課之前先看電影,除了感受到幾十年前的人們使用台語的精練,更有趣的是,整體的演出形式一直給我一種似乎在搞笑的不自然感,即使劇情明明是悲情或衝突的段落。
暫時擱置這個疑惑,我開始從林摶秋先生的生平瞭解起,隨著他的赴日求學、學習日本新劇(演劇)、進入東寶影業,到回到台灣組織劇團,歷經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再因為受韓國友人刺激而決定投入台語片的發展,原本的疑惑反而如拼圖一片一片隨著歷史進程而拼湊起來。
聽過〈「姊妹愛上同一人,竟導致他的死亡!?」-台語片風華與電影全才林摶秋〉這一集的聽友可能會發現,整集裡我經常在講林摶秋個人行為或遭遇時,延伸補充了當下的社會或政治環境,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人的行為或遭遇往往是在背後環境的架構下出現的,台語片的電影美學也是。還記得林摶秋先生在日本求學時經常待在東京新宿的「紅磨坊劇場」裡嗎?
西元1853至54年,美國黑船打破了日本長期以來的鎖國政策,此後世界各國的文化湧入日本,其中也包含歐洲的戲劇,當時人們說「這才是新的戲劇」,自此,有別於「能」、「狂言」、「歌舞伎」及「文樂」等古典戲劇的「新劇」,以一種寫實主義的現代劇場形式在日本逐步發展、壯大。
日治時期,台灣受到日本的影響,越來越多台灣人學習新劇,新劇成為當代表演藝術的美學典範與邏輯,而這樣的邏輯(寫實、分幕、照明、裝置等特性)似乎也帶到了電影裡,還記得林摶秋從明治大學畢業後受推薦入職的電影公司「東寶影業」,前身就是專營劇場的公司(株式會社東京寶塚劇場)嗎?
台語片史上第一部賣座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導演何基明,當初正是因為參觀了「東京發聲電影製片廠」(東寶影業的片廠),而決定棄醫從影;林摶秋更是在紅磨坊劇場編導創作及在東寶影業擔任副導演。可想而知,新劇的當代性對當時的電影美學有多大的影響。
然而舞台上那些為了台下觀眾而刻意放大的肢體動作與明顯的抑揚頓挫,放到了可以遠、中、近景任意切換的攝影機鏡頭前,自然就顯得過於強烈與不自然,例如舞台上看不到的眼淚,透過「飛撲沙發或枕頭」可以明確表現的哭泣,在電影裡就會變得浮誇好笑,鏡頭運用也更像是舞台演出的一幕幕切換,「cut」一詞在此如此合適。
但時至今日,這些不自然反而成為時代的刻印,告訴我們台語片曾經如何一步步嘗試、探索與發展,並且越來越得心應手,以這次影展中的影片為例,1972年由吳劍飛導演、歌仔戲天王楊麗花飾演青春少女的《回來安平港》中,就可看出與1960~65年代的運鏡手法及演員的表演方式,有著許多的變化。
即使當年受到「國語政策」的打壓與排擠,那些在台語片中努力前行的人,沒有輕易放棄,我還是相信林摶秋先生說的那句:「我就毋信台灣人佇台灣拍台語片,台語片興袂起來!」至今,我們還在努力。
現在起到2月26日止,「純情淚‧戀愛風:台語片羅曼史」影展,聽完新單集的介紹,也許你可以找朋友、情人或家人一起去看影展電影,然後在心裡跟林摶秋導演說一聲:「我嘛是(Guá mā sī./我也是)。」
--
林摶秋 個人照。
典藏者: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台灣(CC BY-NC-ND 3.0 TW)。發佈於《臺灣影視聽數位博物館》
--
【亞特聊聊天Podcast】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歡迎前往
「亞特聊聊天podcast」,收聽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