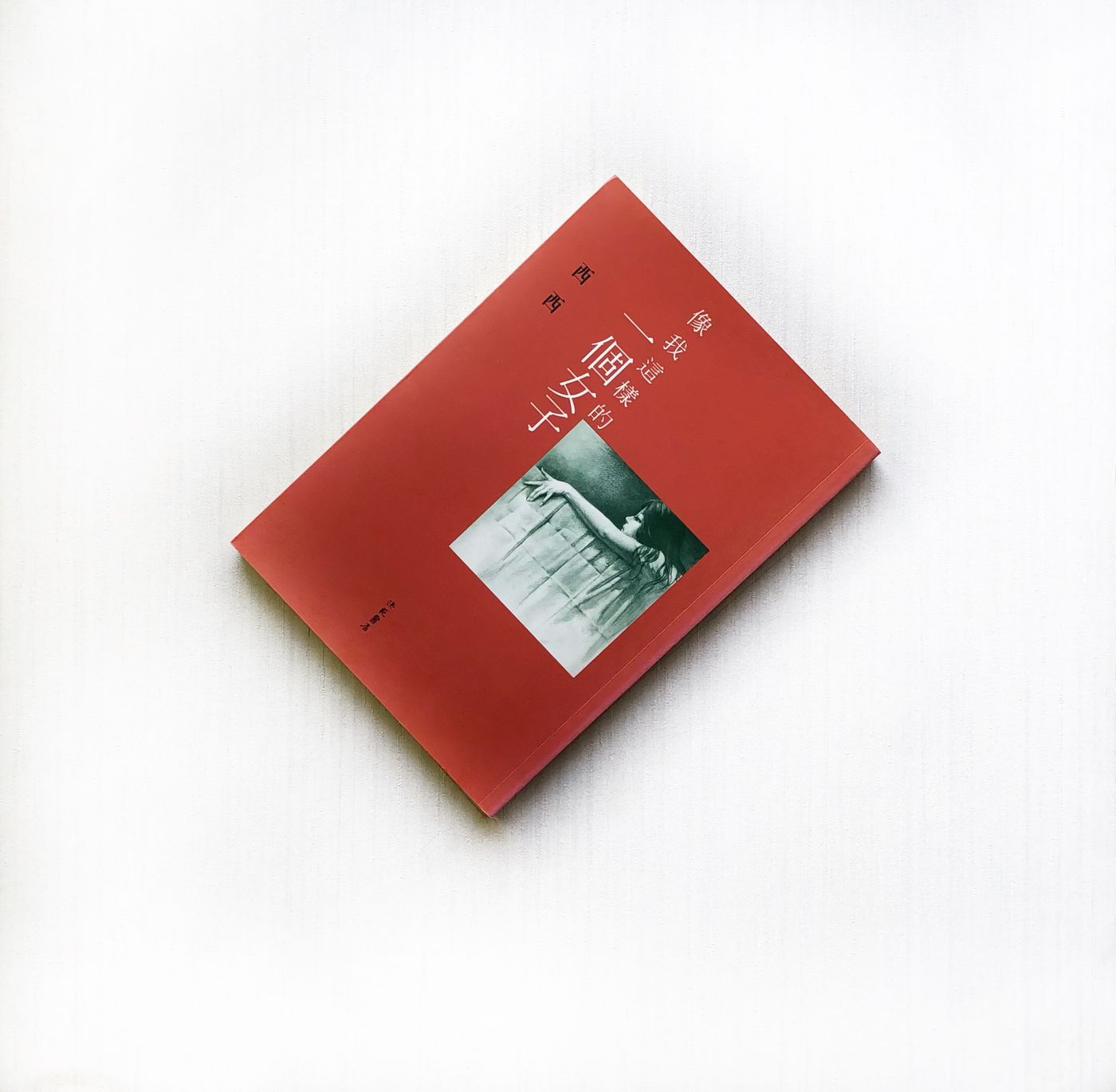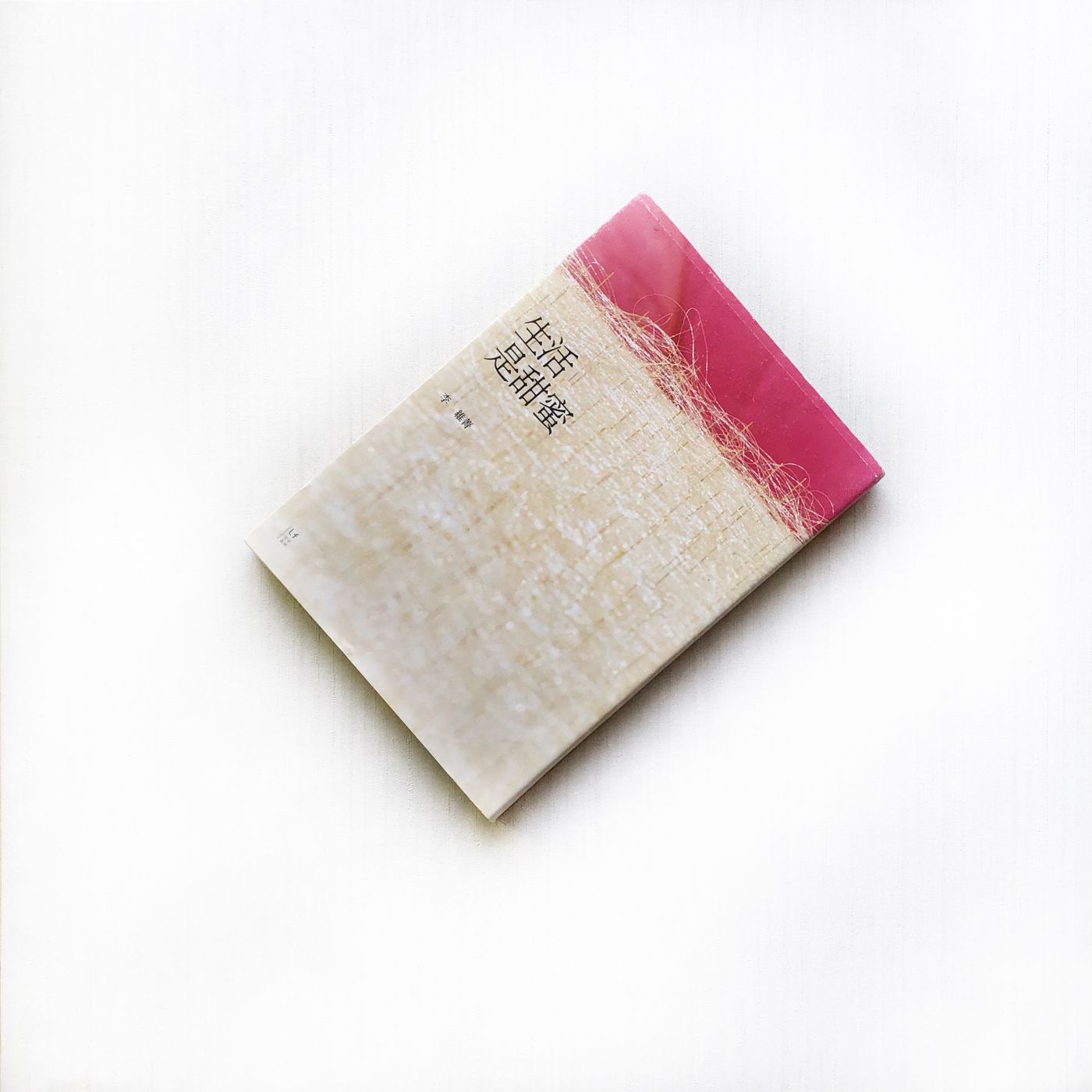先前聽聞西西過世,由於不是她的讀者,我沒什麼特別的感受。高壽又著作等身,想來作家的人生已屬圓滿。年少讀過《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這個短篇小說,很好很好,可是我不喜歡。當時的我需要激烈一點的作品,比如快意恩仇的武俠小說,以及剖析人間罪惡的推理小說。我記性平平,然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只讀過一次,至今內容大致仍記得,或許這便是西西作品的魅力了。
家人讓我看了何福仁的五分鐘西西影片,許是狀況不佳,西西除了提及《欽天監》侃侃而談,滿意自己的創新,對其他話題不太有興致。細節倒是很有趣,西西幾次沒回答今年幾歲,經由何福仁說明,我才得知原來西西永遠二十七歲。
我認為作家紀錄片不妨闡述作家本人的魅力,以便吸引觀賞者去讀他的著作,無須詮釋作品,作品不妨交由每一位讀者自行體會。作家朗讀作品理所當然,外人的各式演繹就不必了。畫蛇添足,貌似權威,實則多餘,反而窄化了世人對其作品的感受。亦無須找年輕文化人吹捧,彷彿追思會,比如《他們在島嶼寫作—朝向一首詩的完成(楊牧)》。何福仁的西西紀錄片《候鳥—我城的一位作家》,片長160分鐘。我略過沒興趣的段落,非忠實書迷嘛。初初接觸西西,一口氣看太多,若消化不良就不好了。
西西哥哥、弟弟訪談的段落還不錯,讓陌生讀者略略得知西西幼時生活情形和手足相處片段。陸離等人去西西家也有意思,老友相聚十分溫馨,陸離帶上西西早年裁製相贈的洋裝。原來西西起初讀家政,後來才轉英文,難怪日後能縫製熊、猿猴等玩偶復健兼自娛。倒是有點可惜沒有亦舒談西西,亦舒若調侃一下西西,多有趣啊。
香港學者、作家鄭樹森,與兩岸三地的文化人往來密切。據說博聞強記,擁有照相般的記憶力。紀錄片中鄭樹森風采甚佳,學貫中西的謙謙君子,條理分明地訴說西西與台灣文壇的緣起,以及西西昔日向台灣推介中國作家的勞苦艱辛。
洪範葉主編倒是應直指戒嚴種種,現代讀者方能略知,當年西西、鄭樹森、洪範出版社為了引入中國年輕小說家的作品,冒了很大的風險,堅持下來自然是對文學的熱情。戒嚴時期台灣管制異常嚴酷,與中國人聯絡是嚴重罪名(通匪),八十年代儘管政治氣氛略有鬆動,通匪雖已不至於殺頭、坐牢(早些年確實發生過),然而萬一遭官方懲處,相關人等禁止出入境、查禁書籍等等,那就很糟糕。鄭樹森提及多年前郵寄一些香港文學雜誌給台灣文壇友人,部分刊載了中國作家的創作。鄭如今說來雲淡風輕,然而或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內情。其實,光是郵寄文學雜誌到台灣一事,期間的忐忑不安,驚心動魄(是否導致台灣友人惹上麻煩……),早已是年輕台灣人無法想像的。台灣確實有著黑暗苦悶的過去,現今的自由民主並非天下掉下來。
某人將西西右手失能一事,說成彷彿上天的禮物。我全然略過,完全不想知道她還說了什麼。痛苦就是痛苦,就算日後超越了痛苦,但痛苦依然存在。別否定痛苦,或以為否定了,痛苦就不存在。歌頌苦難根本莫名其妙,超脫苦難的堅強、毅力才值得感佩。
西西慣用的右手因故失能,後來只能用左手過日子,那可是時時刻刻都不方便。紀錄片中西西友人哽咽,那些精緻可愛的玩偶熊,猿猴,都是西西一隻手做出來的,疼惜西西的心意,讓人動容。
看著紀錄片的西西,突然想起家人的大學老師唐亦男,我們之前返台探親,曾拜訪老師。唐老師談起多年前中風,她不願接受看護服侍,奮力復健,半年後總算能自理生活,唐老師獨居,在熟悉的環境生活,自由自在。兩位前輩知識女性,勇敢地面對衰老病弱的身軀,努力在晚年活出風采,實為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