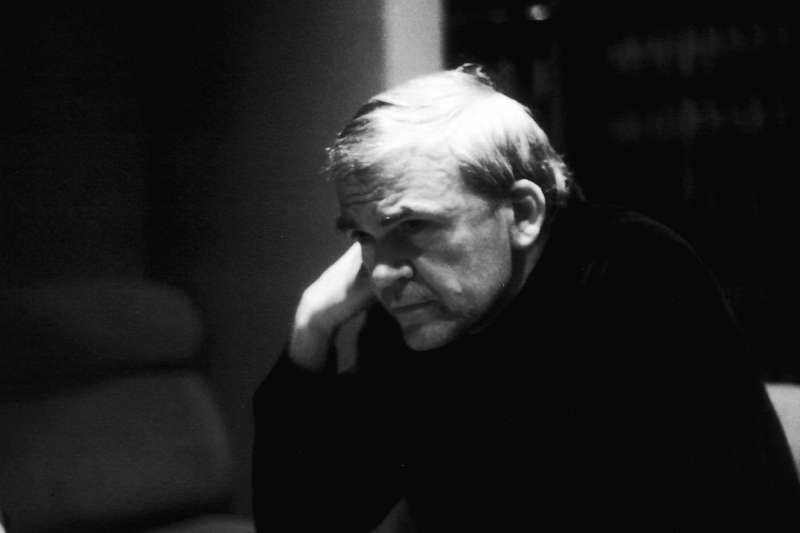本文不會提到太多《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這部紀錄片的內容,完全是場外閒聊區哈拉,對米蘭昆德拉寫的小說有興趣的請自己進戲院看片。
先講講古
1980年代末時報出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中國知名作家韓少功翻譯的,忘了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為何會買這本書回家,不過看完後真覺得驚為天人,內容寫得很吸引人,並帶有很深哲理但又很容易看下去,所以就陸續買了《笑忘書》、《玩笑》,《可笑的愛》等書回來看,但覺得都沒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寫得好。
考上大學還特地帶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去成大推坑,不過書借出去後,就再也沒有回到我手邊,最後到底是誰借走我也不知道。雖然高中大學時很崇拜米蘭昆德拉,但是後來上研究所對於布拉格之春的歷史有更清楚的瞭解,也讀了哈維爾的東西,米蘭昆德拉在我心中的地位就峰迴路轉直接下降。年紀更大後,覺得自己當時對於哈維爾與米蘭昆德拉的論戰評價,過度單一,完全以政治行動的單一角度去評價兩人觀點的優劣,然後輕易選邊戰,過於偏頗。就像卡謬與沙特的論戰一樣,年紀大了也有不同的理解,不能說誰就完全對,誰就完全錯。
突然會想到卡謬與沙特的論戰,除了因為兩場論戰都涉及到蘇聯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討論,另一方面,就是我個人自己的感覺,米蘭昆德拉與哈維爾的思想都滿有卡謬的成分。兩個人以不同方式去詮釋與衍生卡謬有關荒謬與抵抗的論點。
文學家的批判vs行動家的抵抗
基本上,《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是完全從文學角度來探討米蘭昆德拉的生平,就像他強調他不是一個反共的異議作家,只是一個單純的作家,想瞭解他的想法請認真從他的作品去瞭解,而不是從他個人的生活經歷去瞭解。
本片幾乎完全省略了昆德拉生涯的政治面向,他曾是一個共產黨員,曾經支持捷克共產黨修正主義,也曾是狂熱的捷克民族主義者,歐洲文明捍衛者,更是潛在的親蘇投降派。
之所以說他是投降派,是因為他認為捷克是個小國,無法避免鄰近大國的影響,順從蘇聯是不得不然,他的說法有點複雜迂迴,但大概是這樣的意思,當時看到這段話時我很有感,就像主張台灣不可隨意忤逆旁邊的大國中國一樣,大國就是拳頭大,小國只能委曲求全,當然對他起了反感,轉而投向哈維爾的立場。
當然,他的想法也會隨著他的經歷而改變,從他的書被禁到流亡法國,他的想法不斷再改變,唯一不變應該是他對文學創作與作家角色的堅持。看完本片我才清楚意識到他就是一個堅持現代主義創作理念的小說家,他對社會的參與是透過小說創作,而非具體的政治社會行動,所以對於他不簽七七憲章的理由現在多少可以理解。
布拉格之春只是剛好是昆德拉經歷過的時代,因而成為小說的背景,他變成反共的異議作家只是他創作的作品不見容於共產黨而被查禁了。
文學對他而言,是一個遠離現實的園地,昆德拉就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文學不為任何政治社會價值而服務,所以他對於他創作的作品非常認真看待,態度完全站在後現代主義的相反對立面,他作品中對現實的諷刺,完全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的戲仿,嘲諷,而是有很沈重的意義。
他的媚俗概念更是完全體現他的創作理念,本片提到華格納時,我馬上能理解昆德拉為何不喜歡華格納,因為華格納的作品很媚俗。
媚俗現在這個概念,在中文世界應該很熟悉,不過三十多年前,這個概念在中文世界是很新穎的。簡而言之,政治美學化就是一種媚俗,國家舉辦的各種慶典,閱兵,激發人民的愛國感與榮譽感的儀式與活動都是媚俗。但昆德拉的媚俗還有另一層意義,政治異議份子的自我犧牲,自我道德滿足感也是一種媚俗,簽署七七憲章也是一種媚俗行為,所以他才不願從俗去簽署,他不簽署不是因為他膽小懦弱,而是因為他不願從俗,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施明德,浪漫的施明德在昆德拉眼中應該也是一個媚俗者。
就某種程度而言,昆德拉是一個滿誅心,對人很苛刻的文學創作者,也因為株心的批判力道,才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如此好看,成為經典。
當然如此機車與犬孺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行動者,他的行動僅侷限於文學創作中,而不會付諸於現實行動中。曾經我不喜歡這種態度,但現我是可以理解與接受這種態度。
矛盾的作家
就我看來,昆德拉是一個很矛盾的作家,他的創作不自覺地引用了很多解構,後現代主義的文學技巧,很株心冷血的解剖人類各種行為的偽善虛假,但又很堅持現代主義的創作理念,完全不贊同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而堅持文學的獨特價值,反對後現代主義的作者論,堅持作者對於作品的絕對詮釋權,因此不贊同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文本閱讀的愉悅觀點。
他流亡法國不接受外界的訪談,不想讓他的作品改編成電影,除了他對於媚俗的反感,不想被特定的標籤與刻板印象定型,或多或少也來自於他對於現代主義創作理念的堅持,即使他的作品取悅了大眾市場,但他的創作是一個獨特完整的世界,不可能被刪減改編成影視作品,也不接受人們對於他作品的隨意解讀。他對他作品翻譯的嚴格要求,也是他對於現代主義作者地位的堅持。但從他對現實株心批判的角度來看,他這種不接受訪談,不接受改編態度的堅持,不啻是一種媚俗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