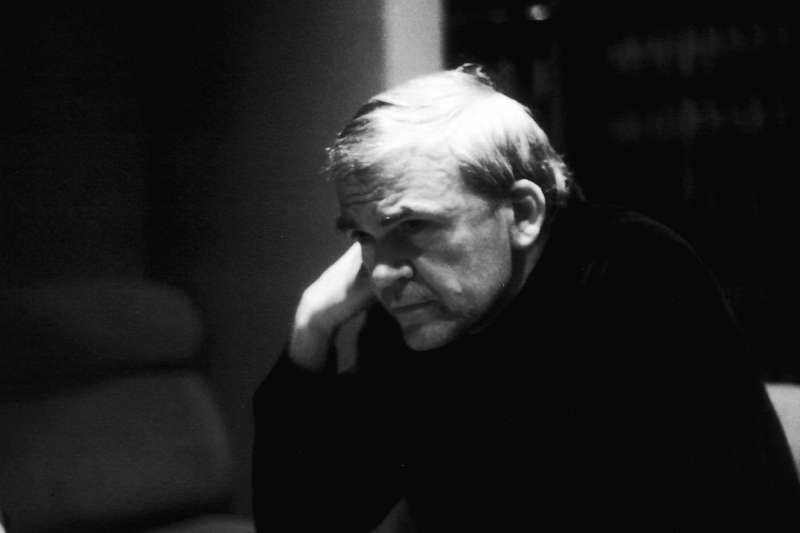最早接觸米蘭.昆德拉,是高中時從學校圖書館借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紫色封面、黃字書名——多年後的現在,皇冠推出了整套全新版、白色書封搭配昆德拉親繪的插畫,但當我想在網路上搜尋當初讀的舊版,出現的封面卻是橘色的。是我記憶錯亂了嗎?印象中封面摸起來有些微的顆粒觸感,那還是真的嗎?
雖然後來找到了已絕版的紫色書封,證實自己(這次)沒有記錯,但在那幾分鐘內,回憶裡的畫面全都不確定地顫動了起來。
人類和過去乖離(即便是幾秒鐘前的過去),那是兩種力量立即生效且合作無間的成果:遺忘的力量(抹滅一切)和回憶的力量(改變一切)。
遺忘的永恆作用使得我們的每項行為都呈現出不真實、幻影似的、煙霧一般飄渺的特徵。我們的現實世界本質就是稍縱即逝,而起只配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但是藝術作品則雄偉矗立起來,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一個理想的、堅實的世界。在那裡面,每個細節都有它的重要性,它的意義。所有身處其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得以不被遺忘,而且以原本的樣貌被保留下來。

作家創造小說是「發現」人性尚未為人所知、隱藏起來的一面;小說領域裡的創造是一種認知行為,在費爾汀的定義裡便是:「能夠迅速而且智慧地洞悉作為我們冥想對象所有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質。」
費爾汀拒絕讓自己的小說淪為一連串情節、動作、言語的因果連屬,也就是英國人所謂的「故事」(story)。那被誤以為是一本小說本質和意義的故事;費爾汀反對的即是「故事」的專斷獨裁勢力。
開篇就為現今的小說創作者帶來醍醐灌頂:故事不是小說的核心。我曾讀過市面上好幾本關於小說寫作的書,都在教我們怎麼寫出一個精彩的故事,一群立體的人物,創造衝突、高潮或反高潮的情節。甚至,當今小說的一大榮耀,或許是被改編成電影戲劇——在昆德拉看來,那等同於拿掉小說原來的結構,將它濃縮成單純的故事;然而他認為,結構與形式正是小說的美、風格與原創性所在。
只有作者不再滿足於僅說單一故事這階段時,想要更進一步對周遭世界開啟一扇扇的大門時,小說這門藝術才正式誕生。

昆德拉認為,小說的定義和本質,是洞見、發現人性隱晦而尚未被看清楚的面向;是傾聽、深入探究事物的精神。一位優秀的、夠資格的小說家,該要看穿那些所謂的「理所當然」或「平凡無奇」身上,其實披掛著一層「預先詮釋」的簾幕,並像賽萬提斯將唐吉訶德送上征途那樣,將簾幕一舉撕破,直面世界赤裸裸的滑稽模樣。
縱觀小說史,昆德拉指出藝術的史觀與科技的進步史觀不同:
它並不意味變得完美、改善或者進展。在這上面,歷史比較像是一次探索許多未知地域的冒險旅行,然後再將探索結果標在一張地圖上面。小說家的宏圖並不在於做得比前輩好,而是看出前輩所沒看到的,說出前輩不曾說過的。
他對於運用小說見證一個歷史時代有所意見:
歷史(人性的歷史)儘可以沒品味地重複,可是藝術的歷史卻不容忍重複。藝術不是一面大鏡子,放在那裡只為用來記錄歷史的細枝末節以及它無止盡的重複。藝術並不是亦步亦趨,追隨歷史腳步的軍樂團,它的存在是為了創造自身的歷史。
每一門藝術在現代注意的範疇裡都盡可能想凸顯它的特殊性和基本精神。繪畫放棄了它亦步亦趨的紀錄功能,其他方法能達成目的(例如攝影),它就不再拿它當成自己的目的。同樣,小說也拒絕再做某個歷史時代的見證,不願再描寫某個社會,不願再為某種意識型態辯護。它只情願為「唯有小說能說清楚的事情」服務。

而橫覽各國文學,昆德拉也非常犀利地道破大國族和小國族各自的「鄉巴佬氣」:拒絕(或沒有能力)將自己的文化放在世界文學、以及小說作為一門藝術的歷史之「大背景」裡來看待,而只侷限在國族歷史的「小背景」裡——這點特別值得我們省思,不僅是小說、文學,擴及到電影、戲劇、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也是如此:
大國族常常會排斥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別文學在他們看起來已經足夠豐富,所以對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品提不起興趣。
小國族對於「大背景」視而不見的理由正好相反:他們對世界文化相當尊崇,可是這個文化在他們看來是個陌生的東西,是個與國族文學沒有太大關聯的理想現實。
小國族常會訓誨它的作家,說他們只隸屬於自己的國族。如果他們將視野拓展到國界以外,和越國界藝術領域的同行連上聲氣,那麼大家就會認為他們裝模作樣,瞧不起自己的同胞了。又因為小國族經常遭遇攸關存亡的險境,所以這些國族很容易便能推銷自己的態度,好像在倫理道義上絕對站得住腳。

那麼,回到關鍵的問題,昆德拉所謂「唯有小說能說清楚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前述定義的撕破簾幕、深入事物本質,難道不也是其他藝術形式、或者哲學和社會科學同樣致力於的目標?
昆德拉的看法散見於全書中,不過他也很明確地點出尋找答案的方法:「想要了解就得比較」——這是布洛赫的名言。而我閱讀下來的總結是,昆德拉認為「小說」這門藝術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擁有靈活運用形式、虛實和長篇語言敘事與論述的能力,去思考人性、並且關心個別個人活在這世界上的狀態、生存價值與意義。大致而言,前者是與哲學和其他藝術形式的差別,而後者是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差異。
小說裡的思考,就像布洛赫或穆西勒引進現代小說美學裡的那種手法,是和哲學家或科學家的思考沒有關聯的。我可以說,這種思考是故意非哲學式的,甚至是反哲學式的,換句話說,完全不受制於任何預設的理念系統。這種思考並不負責審判,也不斷言什麼才是真理;只是詢問,只是驚訝,只是探索。它的形式多到不可勝數:隱喻性的、諷刺性的、假設性的、誇張性的、格言警句性的、滑稽的、挑釁的、奇幻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從不偏離角色生活的神奇領域;供給這種思想養分、證明它合理妥當的,正是角色們的生活。
閱讀《簾幕》,不僅讓我們有機會窺見像昆德拉這樣優秀的小說家,究竟吸收了哪些文學養分、如何分析評論其他經典文學、形成他自身的小說美學與史觀,更讓我們跟著他的思路,一起反思關於小說本質、記憶、歷史、語言、現代與反現代、反抒情的蛻變、悲劇精神、審美、滑稽與玩笑等等概念。他的見解犀利獨到,金句連篇,許多都值得繼續深入、延伸出一連串的辯證討論,而我讀得興味盎然,大大拓展了自己對於小說、乃至廣義的文學與寫作的思考和可能性。
---
書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