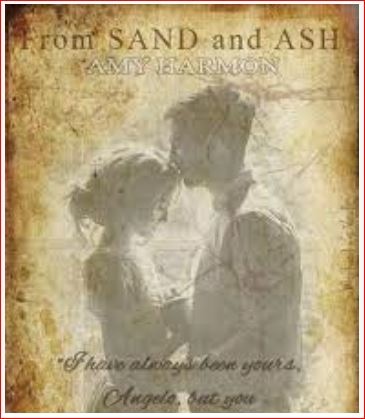「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1949年《第二性》出版,西蒙‧波娃剛過四十歲,聲名大噪。
《第二性》的性別意識是如此具有「現代性」,很多時候我都忘了西蒙‧波娃生在上世紀初,經歷過一戰(童年)、二戰(成年),兩場戰爭對她影響甚鉅,二戰時她已經在高中任教,1940年納粹占領巴黎時,她被革除教師職位。
這本在她死後才出版的成長小說《形影不離》,寫的是一戰戰後波娃家族的劇變。父親公司破產,家裡辭退女傭,搬離蒙帕納斯大道(西蒙波娃出生在圓亭咖啡館樓上),遷進狹窄無光的公寓,小西蒙失去了自己的房間,她感覺晴天霹靂,遭遇厄運。日後遇到摯友「安德蕾」,西蒙反而要感謝這「厄運」,逼得她必須半工半讀兼家教幫忙養家。工作,是女人獨立的根本。
與小西蒙成為對照組的是安德蕾,她們相遇於九歲那年。安德蕾來自一個富裕的天主教大家族,家裡有七個兄弟姊妹,西蒙初次造訪她家,嚇了一跳,安德蕾家除了親兄弟姊妹,還有一大堆堂兄弟姊妹,川流不息的訪客,讓才九歲的安德蕾就要幫忙招呼。母親把正在盪鞦韆的她喊下來,要她去準備糕點,去地窖盤點火腿、臘腸,成堆的洋蔥和馬鈴薯。每個狀似輕鬆的聚會都需要很冗長的準備工作,安德蕾的媽媽從小被外婆訓練,代代相傳,重要的不是食物而是社交,「比品嘗更重要的,是評論正在品嘗的食物。」安德蕾從小就已經習慣長時間不吃東西。
安德蕾跟西蒙說:「我當孩子當得累了,妳不覺得童年怎麼永遠都過不完嗎?」
兩個小女孩初次在學校相見,西蒙是班上的第一名,安德蕾是「被火紋身的小女孩」,她幫忙備餐煮馬鈴薯湯時,被火燒到衣服,一路燒到右腿,燒進了骨頭。日後安德蕾的腿還會出事,來到少女時期,大姊出嫁後,安德蕾要接替大姊的角色,出席各種餐會、葬禮、慈善義賣會、親戚家的野餐。西蒙看到好友沒有一分鐘能休息,等到半夜一點大家都睡時,姊妹淘才能促膝聊天,聊沒多久淺眠的外婆又來喊人。隔天,安德蕾又被分派到親戚家拜訪,出門前她去砍柴,將斧頭砍在自己的腳上,她跟好友承認,是故意的,她說並沒有多痛,再痛也不會比去應酬痛苦。
「我想煉獄應該就是這樣吧!」西蒙原本很羨慕好友,來到安德蕾家的莊園過暑假,西蒙沒有像樣的衣服,安德蕾特別幫她準備美麗的小洋裝、香水還有粉撲。安德蕾接受嚴謹的淑女教育,出門一定戴上帽子與手套,是虔誠天主教徒,而西蒙已經暗自決定再也不信神。兩人有過這樣的對話:
「我們在教義裡學到應該尊重自己的肉體,那麼在婚姻裡賣身,跟在市場上賣身同樣罪惡。」
「我們未必非結婚不可。」
安德蕾的出路只有結婚或修道院,母親對於她的對象極為挑剔,門不當戶不對不行,家裡有猶太血統也不行。兩個女孩通過高中會考,同時考上索爾邦大學,西蒙讀哲學系,安德蕾讀文學系。文學只是點綴,安德蕾畢業就要嫁人,在當時的價值觀裡,西蒙將來是要誤入歧途的:畢業、參加教師甄試,有一份能賺錢自立的職業。
長大以後,肩上擔子越來越重,兩人的見面次數屈指可數,她們約在春天百貨喝下午茶,安德蕾瘦得可怕,臉白得像一張紙,粉底也掩蓋不住眼下的青筋。她們的周圍都是貴婦,西蒙說:「擦著香水吃蛋糕,談著生活物價,安德蕾打從出生就註定和她們一樣。」嫁人後,將會花很多時間擦拭銅製廚具,用羊皮紙蓋上一罐罐自製果醬,而不是讀書、寫作、拉小提琴,安德蕾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西蒙說:「我私自認為,安德蕾必定是個天之驕子,以後她的生平會被寫進書裡。」
出了大名,生平被寫進書裡的,當然是西蒙,不是安德蕾。這個寧願用斧頭砍傷自己,好換來十天休息的女孩,1929年就因病去世,只活了二十一歲。她還來不及認識沙特,她寫信給西蒙:「我很期待早點認識沙特,我極為欣賞妳唸給我聽的他的信。」
「我們未必非結婚不可。」小西蒙的話,終將應驗。《形影不離》這部半自傳小說,卻被沙特所厭棄,阻止出版。如今它出土面世,可以讓我們看到將來寫出《第二性》的西蒙波娃對於女性處境的早期自覺,那是上世紀二○年代的巴黎,男性作家海明威「流動的饗宴」的巴黎。相較之下,二○年代巴黎女人的養成依然僵固保守,西蒙波娃說:「她(安德蕾)需要翻飛在樹梢之間」,鞦韆越盪越高,幾乎要盪到天邊,西蒙覺得安德蕾的表情意外地肅穆,好像是想等盪到最高處的時候,縱身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