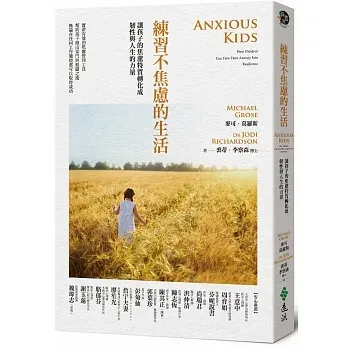我對孩子生氣背後,有著「不原諒自己」的心情。
自從第7週的練習之後,為了內心平靜,我不斷轉換想法,透過「原諒」來諒解自己的情緒。
然而,生氣與憤怒,還是經常出現在與孩子的應對日常。
我雖然學會了覺察應對姿態背後的情緒,但也體會到「全心原諒自己」的知易行難…即使不斷告訴自己要原諒自己,還是會冒出自責的念頭……
這一切直到我看到「害怕」現身,而有了一絲變化。
腦中常常浮現,還在幼稚園的我,與哥哥及阿嬤睡同一張床,但哥哥與阿嬤蓋一條被,我自己蓋一條被,雖然在同一張床上,我卻覺得床好大、家人好遠。
後來小學四年級搬了新家,有了自己的床,自己睡;有一天晚上聽見一個讓我不安的、小小的聲音,我去敲了爸媽的門,訴說我發現奇怪的聲音,於是爸爸就陪著我豎著耳朵,從2樓、找到3樓,都沒能找出聲音的源頭。
就在最後爸爸送我回房間時,終於發現,那小小的聲音,不是什麼怪奇事件,而是來自隔壁間的阿嬤,她熟睡時發出的有點雜音、規律、低沉的呼吸聲…謎團解開後,沒有任何危險威脅,爸爸叫我別怕,要我去乖乖睡。
即使知道了是什麼聲音,但我依然感到害怕,不是被威脅生命的怕,而是莫名的怕。我聽話乖乖去睡了。從此後,如果有奇怪的聲音,我就把耳朵摀起來睡,告訴自己沒什麼好怕,也沒再去敲過爸媽的門。
回溯「害怕」的回憶,花了一些時間,因為,一時想不起來。
我最早的害怕的記憶,應該是在幼稚園時,有一年過年去鄉下親戚家玩,追著騎腳踏車的哥哥,也不知道跑了多遠,在幾個彎道之後,便見不著哥哥的車尾了。接著,我在不熟悉的鄉間迷路了。
清楚記得我爬上了路邊的田埂,看到遠方的一棟四合院屋頂,好像是親戚的家,我開始感到害怕,因為中間隔了好幾片田,看起來好遠好遠,我知道我沒辦法穿越田地走過去,我不記得有沒有哭,我滑下田梗回到道路,選了一個方向,繼續往前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接下來的記憶片段,只記得我站在一個陌生阿姨的機車腳踏板上,她載著我繞著蜿蜒的鄉間小路,經過一落又一落的合院,一次又一次地問我「是不是這間?」
最後,我看見熟悉的門前小徑,好心阿姨把我送回了親戚家,天也差不多黑了。媽媽心急的把我抱起來,我也聽到了她責罵哥哥。
我還是不記得,我有沒有哭。我只記得,我與陌生阿姨聊我的新年禮物很開心。找到親戚家也很開心。
大學畢業後,自己到台北租房子。近20年的歲月中,換了7個住所。
剛搬進租屋處的第一個晚上,通常是輾轉難眠的。現在回想起來,原來是害怕。但當時,並不這樣認為,而是以「認床」來理解。
現在想想,那時孤單自己一人,在從沒待過的空間裡過夜,是害怕的。當關了燈,一切變得黑暗與安靜,看著新房間的窗戶映照著陌生的光影,我常常睡不著。
害怕,好像不等同於「恐懼」。
「恐懼」說得出具體的狀況,例如「恐懼失敗」、「恐懼死亡」;害怕,比較是本能式的不安,說不出來是怕什麼,就是感到不安。
因為說不出來,所以,就被忽略了。
當理智愈常告訴自己「沒有危險、沒什麼好怕的」,「害怕」就愈來愈迅速地被壓回心裡。
隨著年歲成長,被壓回心裡的「害怕」,沒有不見…「害怕」似乎變成一種色調濾鏡,模模糊糊地罩在我的日常……
而「害怕」的記憶,似乎也在我的兒子身上重播。
我的大兒子從出生至今,晚上睡眠就不好,嬰兒時,常常在11點到1點間驚嚇般的哭醒,一哭就要半小時才會停,一開始以為是常見的腸脹氣,但症狀並不雷同。
記得一歲多有幾次被吵醒的我,忍不住大聲斥責,也曾生氣到打他屁股,但想當然爾,愈打罵哭愈大聲,後來索性不理會他,讓他哭。一直到3歲過後,他才能睡得比較正常。
到上小學,晚上陪孩子們睡著之後,如果我起來去作別的事,他睡到一半就會哭醒叫媽媽,他常說他作了惡夢。
白日裡,他怕黑,怕自己上樓,怕自己穿越房間與房間的廊道。
到了現在快十歲,如果他睡著後我沒一起睡,他會在1小時內醒來,會走出房間找我,然後,拉著我回到床上,側睡縮成一團,手腳濕涼,告訴我「他怕怕」。
一開始,我會嚐試問他「是作什麼夢」、「你在怕什麼」,但發現他並沒有真正清醒到可以回答我;後來,我就直接抱著他輕拍說「不要怕媽咪在」,直到他再睡回去。
在上週的某天,孩子們睡著後的晚上,我正在整理著我【薩提爾練習W7:覺察自己應對姿態裡的情緒】的文字時,想著「全心原諒自己真的很難」時,我兒子醒了,走出房間來書房找我。
我關了燈、進了房,抱著他拍著他,我說不出口「不要怕媽咪在」,而是開始掉淚,一直掉、一直掉、沒辦法停。
我看著我兒子,突然想到那個夜晚睡覺害怕的小女孩。
長大的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掉淚,我的淚是感到心疼,我為那個隱藏孤單與害怕四十餘年的小女孩心疼,她,需要的是一個溫暖的抱抱,而不是「不要怕、沒什麼好怕」的說服與安慰…
我突然驚覺,我的不原諒自己,可能與害怕有關。
我不接受自己害怕,我不允許自己害怕,我也就不原諒自己害怕。
只要碰到與「害怕」有關的情境,我就無法原諒。
我害怕孩子玩平板眼睛會壞掉、我害怕不自制的孩子會變壞孩子、我害怕自己是個不夠好的媽媽……
因為無法原諒自己害怕、也無法原諒孩子,所以生氣,所以憤怒。
又因為生氣憤怒,又更害怕自己變成愈來愈糟的媽媽……於是「害怕」就一直在情緒裡無限迴圈、推波助瀾。
兒子睡定後,我抹去了臉上的淚,我起身找了床上最厚實、最柔軟的一件大毛毯,對折對折再對折,變成一個大枕頭般的放在胸前,然後,雙手用力的擁抱那個大毛毯,我給害怕的自己一個大大的擁抱。
「害怕,是正常的。我會陪你。」--我對我自己說。
------------------------------------------------------------
當孩子表達不願聽從我的規定或意見時,我生氣;現在,我知道,我生氣的背後,怕的是「自己是個沒有價值的母親」。
當孩子明明可以自己解決卻選擇依賴哭泣時,我生氣;現在,我知道,我生氣的背後,怕的是「此例一開讓孩子成為媽寶」。
我該面對的是「我如何看待我這個家管媽媽的價值?我如何看待我的協助對孩子的影響?」而不是眼前這個小孩此時聽不聽話、依不依賴。
這並不代表我不處理小孩不聽話、太依賴,而是,我先貼近自己的感受、梳理出我自己情緒背後的癓結點之後,再來面對孩子的話語或要求。
跟著崇建老師的課,在自己的生活中,從「生氣指責」的應對裡,看到背後的複雜情緒,從「原諒」追索到糾結的源頭—「害怕」;這個脈絡,像是為憤怒洪流開出一條疏通的渠道。
現在當我感覺到自己生氣時,我會低頭一問,想想心裡,是不是在害怕什麼…
當憤怒不是連結到眼前的場景,而是連結到我內心的害怕時,我會自然地將思慮的重心轉向自己—「我如何面對內心那個害怕」,而不是想著「如何對付面前那個惹毛我的人」。
憤怒之浪,湧向內心某個角落,化成溫暖海水擁抱某個自己,而不是去撞上人際之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