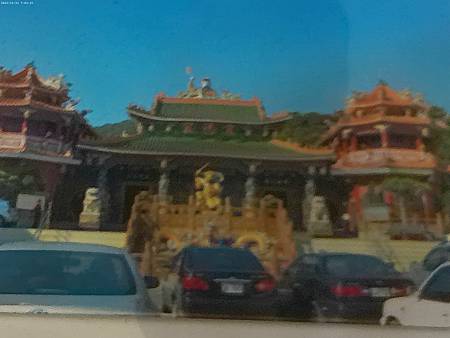一、原文:
孫承宗的〈恭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疏〉出自《孫承宗集》卷二十四,撰寫於天啟二年(1622)八月十四日: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生、仍兼攝樞務臣孫承宗謹奏,為經略遽難得人,願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事。
臣頃于講筵陳奏關城事宜,仰蒙皇上一一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國,無不悉意商榷,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欲求滿足分量、眾口稱快者,極難。但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束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鑿,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簡,兵不練,何以為守。西虜絕非守關之人,逃將絕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為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可忍其盡為溝壑。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與可且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為西虜之牧場,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議及之,而逃官難于色也,可乎?至大將方在經營,而彈文縛其手足矣;都城偶有籌策,而彈文又翦其羽翼矣。將使忠賢稟計于逃官,敢勇誠于逃將,滿鎮之旌旗既已無色,一方之嘲呶寧不有聲。譬之學奕者,致至肥邊而遺全局之大,主客者留連驚座而失滿堂之歡。蓋精意綜核于瑣屑,神情凝滯于偏枯,認不可平之數以為遠大,而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幾以為目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之人以為公勤,而或隔于忠計;聽不信之語以為中計,而更疏于公勤。此山海關之大概,而逃官逃將之為也。
經略王在晉,清辯嚴明,公忠詳慎,意在守關,自是滿朝定論。而無奈將吏之逃者,遂借守之說,以繆逢主意,而既無將,遂無兵,更多方以去異己之不為逃者。在晉蒙皇上召還矣,然而代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即臣所疏三四人,臣所未見者,既不敢任,而臣所久識者,亦復未盡滿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并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棄其短,臣可以為道將用,而補其所不足。如秋高馬肥之日,奴來窺關,則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為皇上力守雄關,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輯凶鋒,則臣與諸道將先簡驍雄膽智之將,以訓練士馬,兼以掇全鎮之精神。如遼人可用,絕不以眾疑遼人;西虜可撫,絕不敢以眾信而遂憑西虜。待兵將調和,文武附豫,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于用諸臣之時,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皇上而報神皇帝、光皇帝之生成也。
臣適與禮部侍郎鄭以偉議,以偉謂臣不可去樞,仍當擇任經略,而以臣往來關上,勤為料督視。臣謂是亦可鼓舞人心,終不若臣身在關城親為料理,即就近推補有人,臣亦可督視其次第。臣極知才力綿薄,未必即可擔任,然當今萬不得已之時,諸臣或抱欲為之志,或抱有為之才,而未見關城之事,臣亦既見之,而不以身任之,豈惟仰付皇上委託盛心,即臣內自循省,何以稱塞職分。至于不量臣心,或謂妄以經略授欲得之人,而又或以為才不堪負荷,妄自擔承,且成敗利鈍,前途自難逆賭,臣俱有所不顧矣。事急情迫,惟皇上憐臣真懇之心,准臣以本官督視關城兵務,數日內便可單車就道,待歲終稍有次第,便可還朝。其合行事宜,待臣另疏。為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天啟二年八月十四日奏。
十五日,奉聖旨:「覽卿奏,親往督師,封疆有賴,釋朕東顧之憂,深用加慰。卿便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軍務,俟功有次第,即召還朝,仍給關防敕書,以便行事。該部知道。」
二、作者和寫作背景:
孫承宗(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府高陽縣人。萬曆32年(1604)進士,為第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之後長期在翰林院發展,至天啟朝時,官為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並擔任日講官,在講經上給予年輕的熹宗正面的印象。短短兩年內,孫承宗快速升職,天啟二年(1622)便從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升任禮部右侍郎(正三品),在經歷過天啟二年年初明軍關外盡失的慘敗後,兵部尚書張鶴鳴(1551-1635)為負起責任,自請至山海關(榆關)督師。孫承宗在天啟元年便兩次被吏部和御史方震孺推薦接任兵部尚書,但都被天啟帝認為其無領兵經驗,而另用他人。經歷多次更替兵部尚書,遼東戰事仍無起色後,天啟帝終於在天啟二年二月下令孫承宗升任兵部尚書,並且進入內閣,至此承宗正式進入帝國的政治軍事決策核心,直至北京被李自成攻下,遼東的防禦工事、軍隊部署和重要官員、將領,無一不是由孫承宗所規劃和提拔。
孫承宗上任的首要難題便是收拾遼東的爛攤子,儘管前任尚書張鶴鳴在關上不久便自請退休,接任者解經邦因推辭而被熹宗罷官,最後由兵部左侍郎王在晉(1567-1643)接任,但承宗對於長城的狀況始終不放心,因此于六月十一日自請巡視邊關。此次巡關,孫承宗在了解軍隊之訓練惡劣、大量遼東難民亟待安頓,防禦工事殘破不堪後,提出了新一波的官員和將領調動、軍隊的整編和新兵補充、防區的再劃分和難民的安頓措施。但由於他和新任經略王在晉在基本戰略方針上的不一致,王在晉和當時的薊遼總督王象乾(1539-1630)同樣主張拉攏蒙古人和堅守山海關;但孫承宗和當時任兵備僉事的袁崇煥(1584-1630)他們主張為解決遼民問題和擴張戰略縱深,應該將防線推向關外二百里至寧遠城。儘管王在晉並不反對向關外推進,但顯然消極許多,重點仍是加強山海關和建設附近的八里鋪新城來鞏固防禦。當時的首輔葉向高兩方斡旋,最終天啟帝採用孫承宗的方案,將王在晉調回,另推經略,因此才有了這篇孫承宗自請督師山海關的奏疏。
三:內容分析:
第一段是明代公文中的固定格式,快速提醒閱讀者撰文者的身份和本文大意,值得注意的是「仍兼攝樞務」這幾個字,明代的內閣成員頭銜中,多半為「…尚書兼…大學士」,此尚書銜源於入閣前所掌部會,儘管入閣後仍掛尚書銜,但僅為虛銜,不實際管理該部事務。因此才會有這段掌/攝某部事務,說明仍舊掌管部會的實際運作,這類情況很少見,孫承宗和隆慶時掌吏部事的首輔高拱皆是稀少的案例。
第二段即提出接下來的戰略大方針,一環扣一環,當前之計為守住山海關,保證京師的安全,而目前的軍隊實力和防禦策略無法完成此項戰略目的。首先為守住關城必須向外拓展防線,後金實際上無力控制河西走廊,王在晉的策略是招撫蒙古人控制此地,為明軍建立緩衝帶,同時投入百萬白銀建設八里鋪要塞,以加強山海關的防衛能力。孫承宗認為不可白白拋棄河西走廊,尤其是杏山等地仍有地方勢力對後金打游擊戰,必須積極與他們合作,控制寧遠、中前所和右屯等防衛據點,可加強遼民的抗戰信心,同時將資源轉移建設這些要塞,顯然是更好地運用本就缺乏的軍費。軍隊的實戰能力在熊廷弼二次經略時即有大問題,不斷出現逃兵逃將,孫承宗主張人員大換血,新的氣象是重建軍隊實力的第一步。
第三段提到前任經略王在晉的評價,儘管禮貌上須肯定王在晉這幾個月收拾殘局的努力,但孫與王最大的分歧點在於防守的積極和消極性,以及對於任用逃將逃臣的態度。因此上述分歧,加上直接反對王在晉和象乾等人七月所主張的兵力部署,兩人顯然已無法合作,因此熹宗下令將王在晉召還京師,另推經略人選。稍後首輔葉向高在給當時永平兵備道岳和聲的信中提到:兵部原擬推任山海監軍道閻鳴泰(1572-?)接任經略,但向高認為閻升遷過速,而且孫承宗以自請督師,並無再設經略之需,因此只擬閻鳴泰接任遼東巡撫,協助孫承宗處理軍務。回到此奏疏,孫於此段中繼續提出心中實無適當的經略人選,與其茫然推薦其他不慎熟悉其才性的官員,不如自己親自處理邊務,畢竟數個月的巡視,他已對軍隊的處境有一定了解。接著簡單表明其戰略大要,如先固守山海關,再徐圖恢復,適當拔擢遼人,卻不報以往成見(如廣寧城陷,即因遼將投敵);適當處理蒙古人的關係,但不過於迷信他們便能牽制後金,甚至替明朝守住關城。然而這裡的戰略仍過於簡略和含糊,有待後續的奏章。
末段再度重申自己奮不顧身為國守關的決心,且說明自己未有軍事經驗,才力可能仍有不足。這裡必須說明的是,以孫承宗為內閣大學士,同時兼掌兵部事務,到山海關上督師,其實是降級,成為地方大員,拋棄相權和兵權的地位,因此當時舉朝無論立場如何,都不得不佩服孫承宗的勇氣和決心,畢竟前幾位經略不是下獄就是自殺,實在是個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
天啟帝的批示也十分肯定孫承宗的勇氣,用上「釋朕東顧之憂」並表示一旦關上軍務告一段落,便立即召回京師,以表達對孫的信任,然而隨時局的變化,孫承宗再也沒機會見到明熹宗任何一面。
四、後話:
原先孫承宗計劃關上的軍務處理個半年便可了結,沒想到一待便是三年,在他手中遼東軍隊逐漸蛻變為明末的一隻勁旅-關寧軍,從寧遠到山海關亦重建了一系列要塞,安置了十餘萬遼民,甚至在天啟四年一度登萊軍的張盤、東江鎮的毛文龍呈現三方夾攻的態勢,儘管功敗垂成,但天啟六年正月的由袁崇奐所指揮的寧遠大捷,亦證明孫承宗的努力沒有白費,關寧軍確實具有和後金一戰的戰鬥力。
但隨著東林黨人在天啟朝中期逐漸失勢,握有兵權且和東林人士走得極近的孫承宗不免受到閹黨的猜疑,加上朝中不斷要求裁軍以減輕朝政負擔的壓力,已經無法施展的孫承宗便不斷上疏請求退休,最終於天啟五年十月獲得批准。下次朝中再想到他,便是崇禎二年(1629)的後金首次圍困北京的己巳之變,皇帝和群臣希望憑藉孫的威望,說服因袁崇奐突遭下獄,而領兵離去的祖大壽等人再度率軍擊退在北直隸各地橫行無主的後金軍隊。然而孫此次督師僅二年,便因大凌河之戰的失敗而奪職回鄉。崇禎十一年(1638)清軍四次進入長城,已經七十五歲的孫承宗帶領一家老小堅守高陽縣城,幾天後城破,一家四十餘口皆戰死,崇禎帝聽聞,恢復了其官職,到南明的弘光帝,為其上諡號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