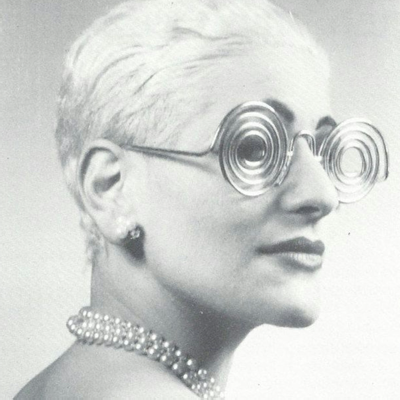博愛座,究竟是出自善意的設計,給予需要的人一個優先的位置。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它變成了一把道德枷鎖。雖然後來改名為「優先因此席」,但似乎只是換個稱呼,爭議並沒有消失。
我自己是一個常搭捷運的人,但幾乎不會去坐優先席。可能是因為潛意識裡覺得,那是一個「被放大檢視的地方」。只要一個看起來「正常」的人坐上去,旁人的眼神就會開始攜帶。
我還記得有一次,尖峰捷運上,一位高中生在博愛座睡著了。到車站時,一位台北大哥突然大喊:「年輕人,台北車站到了!」全車的人都看了過去。我當時沒有譴責誰,只是心中浮現一個疑問:那位大哥為什麼這麼重要?真的只是覺得「高中生該讓座」嗎?
後來,關於優先席的新聞我看到了激烈的報導,因為有人爭執大打出手,甚至還發生「三宅一生之踢」這樣的事件。每次,我都在想:這些衝突真的只是一個位子嗎?
在國外出差時,我觀察到不同的狀況。像美國、法國,幾乎沒有優先席,大家都有位就坐、沒位就站,也沒有人特別追誰該不該坐。日本則和台灣有點像,雖然佔據優先席,但大多數人會在時候自動性讓位。那麼,為什麼在台灣總是會這樣的設計卻伴隨著爭議與衝突呢?
慢慢地,我發現自己更在意的,其實不是「優先席要不要存在」,而是背後的問題:
1.是不是我們的製度規範不夠明確?
2.是不是我們的教育裡,缺乏公共道德和同理心的培養?
3.還是我們太依賴「正義魔人」與輿論審判,把事件推向更極端?
如果有一天真的取消了優先席,衝突就會消失嗎?我不太確定。就像其他國家的案例告訴我們,真正的問題往往不在表面,而是更深層的文化與制度。
所以最後,我只能把這次自我的思考辨析。優先主席的存在本身可能不是最大的問題,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建立一個社會動力,讓人們自然地表現出同理與尊重,而不是被迫進行道德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