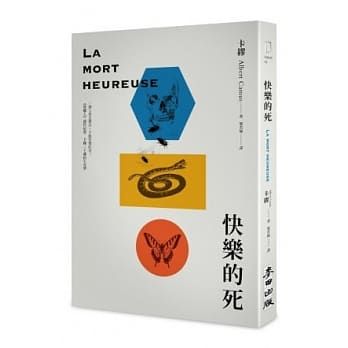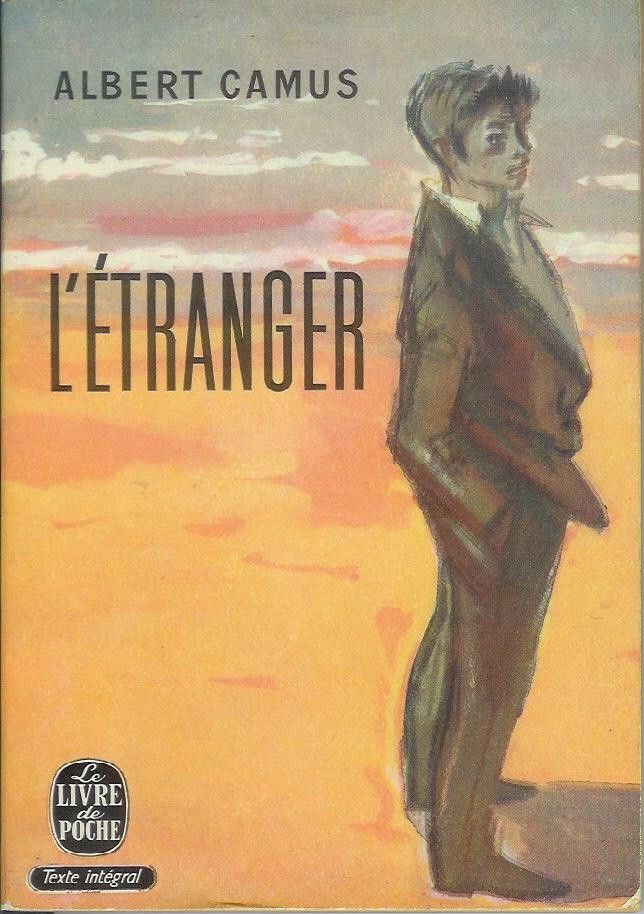「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
發狂似的跑遍每間便利商店,金城武在昏暗的報廢罐頭堆裡找到最後一個鳳梨罐頭,最後在氤氳的燈光下一口氣吃光三十個五月一號到期的鳳梨罐頭,然後,一段感情過期了。
金魚在豢養中左右擺動,螢光色的背脊在保溫燈下變成漫天星光,金城武喝掉罐頭裡的最後一點糖水。
那時的我還不知道,我的鳳梨罐頭也有過期的一天。
一次吃三十個罐頭應該很飽
「一杯 White Lady,謝謝。」
昏暗的地下室,義大利黑曜石板的吧檯彼端,A向我點了一杯調酒。他的深藍色的襯衫和背景幾乎混為一體,周圍的喧囂頓時遠離,像被浸潤在無邊的黑夜。我其實不太喜歡Cointreau,天知道我多久沒做這杯酒了。
白色酒體在頂光的照射下,邊緣散著溫柔的光暈。當調酒師最有趣的瞬間也許是,給自己一杯 Gin Tonic 的時間,就有機會跟吧檯對面的陌生靈魂產生共振。
於是我們從校園聊到工作,從慕赫聊到艾雷島,再從赫塞聊到卡繆。過了幾個禮拜之後,A 告訴我他對那天最有印象的是,有人也最喜歡卡繆的《快樂的死》。
自此我多了個能一起喝酒的靈魂。透過咀嚼文學跟電影保持生存,然後在迴還往復的生活中繼續苟延殘喘。他在醫院裡穿著白袍,而我在台北101穿著正裝。

抽菸不好,卡繆請少抽點
生存的縫隙中,偶爾能有人跟我爭論 Martini 的檸檬皮油離譜的奼紫嫣紅,一間店的Rule of two,無跟 Kashoku 跟 Bar 小谷如何填補經典的地圖。但不知不覺,似乎是習慣了A在喝到好喝的調酒時微微瞇起的雙眼,那時的我才有種從工作中活過來的錯覺。
公館捷運站是兩人喝完酒的終點。兩人的身影在舟山路的燈光下被拉的斜長,兩人在寂靜的校園內閒晃,幕天席地的聊。在台北的街頭散步,對我而言幾乎是精神上的做愛。沒有任何可以分心的物件,兩對肩膀最近的距離是品味跟靈魂的直球對決,黑夜放大了人的情緒,酒精強化感官,人們總能在這時脫口而出最赤裸的話語。

昏暗中的燈箱是城市的標記
從大稻埕散會的那天,一陣輕柔的提問被傾訴了,在大腦放鬆之時。而我完全不記得。一周以後,我跟 A 再次漫步在舟山路,一片漆黑之中走向椰林大道,他跟我道出那不疾不徐的提問,和我略帶笑意的側臉。我看見他的嘴角沁著,沉默像宇宙在我們之間膨脹,於是我斟酌了許久,問出那句:
「那你的答案是甚麼呢?」
我喜歡黑夜浸潤你的襯衫,眼角的溫柔消散在空中。我喜歡兩人的影子在眼前交疊晃蕩,你的聲音在耳邊如潮水般忽近忽遠。我喜歡你徐徐道出自己的想法,斯文且有條理的撞擊我的耳膜。
我們漫步到總圖,再走回校門口,自此約定了一個一月十四日的鳳梨罐頭。
那是 A 生日的半年後,也是我從蘇格蘭回來的日子。他說記憶跟物件需要被整理,喜歡跟情感也需要被思考,六個月是個很剛好的時間,足夠讓一個遊子從遙遠的北方回國,也足以在忙碌的生活中釐清自己的情緒。
於是我跟 A 各自轉身,投入下一場喧囂。恩田陸的《Spring》是名為鳳梨罐頭的漂流瓶,隨著洋流漂向七個小時的時差。
我在遙遠的北方上課、閱讀、喝酒、旅行,但我對 A 除了白袍的生活之外一無所知。只是偶爾在失眠的夜裡,會想起他蕩漾在嘴角的酒窩,跟那本我想再重讀一次的《快樂的死》。
也許我們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是不斷推石頭的薛西弗斯,存在是亙古不變的汪洋。
看著行事曆上用紅色標註的日子越來越近,我不禁想起金城武跟林青霞醉眼朦朧的靠在吧檯的畫面。我是那個反覆問著:「你喜不喜歡跑步?」的金城武,而林青霞的墨鏡卻從來沒摘下來過,兩個孤寂的靈魂在酒吧相遇,但彼此卻不知道更近的距離早在一切發生之前。
回臺灣後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調時差,一月十四日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了幾天之後,我收到了一則訊息,A詢問甚麼時間有空,想把書還給我。
於是我知道,這顆鳳梨罐頭過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