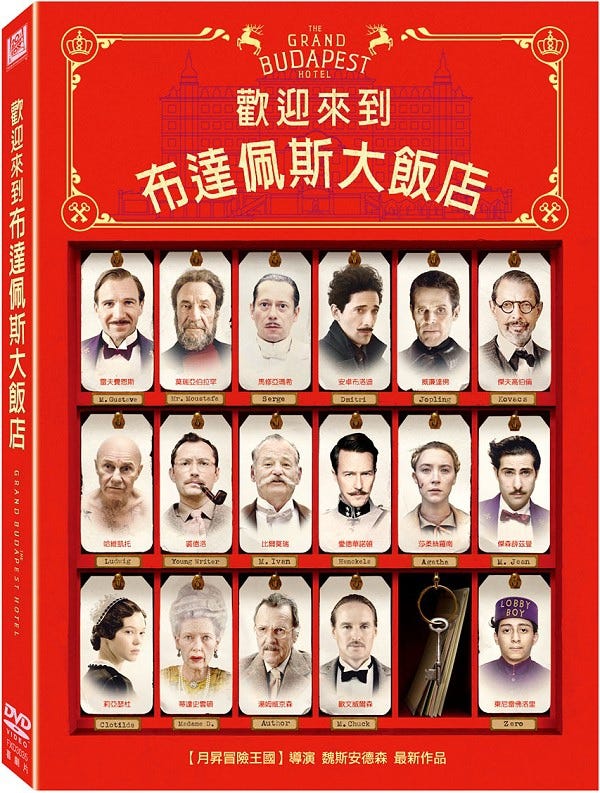文字、攝影/橘貓
故事。不管電影如何演進,迷人的故事依然是吸引觀眾進場的一個重要項目,在數不清的片型分類中,電影能夠以聲光刺激、形式美學,或是極端的寫實還原去替換掉「故事」的地位,但仍有導演回過頭在說故事的過程中,為觀眾找回聆聽的樂趣。一如作者風格鮮明搶眼的魏斯.安德森,在 2014 年問世的優雅作品《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先拋開艷麗的美術設計與講究的影像美感不談,《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的敘事方法,為觀影的過程打開立體空間。電影一開始,一位少女緩緩步入墓園,在一名作家的雕像前方致意,並開始閱讀他的著作《The Grand Budapest Hotel》;畫面進入 1985 年,正在寫作的作家對著觀眾/讀者敘述一段他年輕時的經歷:在 60 年代末期,他來到曾經輝煌風光的布達佩斯大飯店,在這裡意外遇見了飯店的業主 Zero,並從他口中得知一段發生在 1932 的故事;在那時,飯店依然風光,Zero 剛剛遇見他的良師益友葛斯塔夫,而這也是整個故事將要出發的起點。
一層包著一層,像俄羅斯娃娃一樣由外而內,再層層遞進,用畫面比例註記觀眾所在的位置,魏斯.安德森以少女的閱讀/作家的寫作/老者的口述,一步一步將觀眾帶到電影故事的中心:1932 年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一場謀殺案在這裡發生,年輕的門房踏上改變他一生的旅程,而故事中還藏了幾撇墨痕,將摯愛封存其中。結束之後,又緩緩將畫面從 1932 年帶離,老者輕描淡寫地帶過結束的後話,作家離開了飯店,開始著手將所見所聞描繪為著作,而回到現代,那位少女依然在墓園的長椅上閱讀作家從遠方帶回來的人性光輝。
從這個如同剝洋蔥一般的敘事結構,觀眾可以輕易聯想到自己身處的位置,還有正在被電影團隊拍攝的少女,就是這個故事向外延伸的下一層空間。在故事本體之外,藉由這個立體的結構出現了另一個衍伸意涵,也就是將這個故事傳頌出去的過程。從魏斯.安德森對現實世界原型人物的消化(註一),《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的故事在 Zero 與葛斯塔夫兩位主角的冒險中,反射出背後的年代意義:戰爭、血腥、暴力、疾病,在形似納粹與蓋世太保的反派角色過境之後,美好的人事物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消逝,如同風中燭火。
故事的核心是葛斯塔夫終究洗刷冤屈,並且以死明志,在緊要關頭捍衛自己的友人,留下所謂的「人性光輝」。而這個故事傳頌的過程,無疑就幫助觀眾建立起一個更全觀的視角去理解那個年代灰暗的必然傷痛,與身在其中的人們,如何能透過「故事」被重新賦予色彩,在書頁或膠捲上散發光芒。許多看完《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的觀眾產生感慨,對某個理想中的昨日世界激起傷懷或嚮往,而這個概念散布的過程,正與故事的精神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