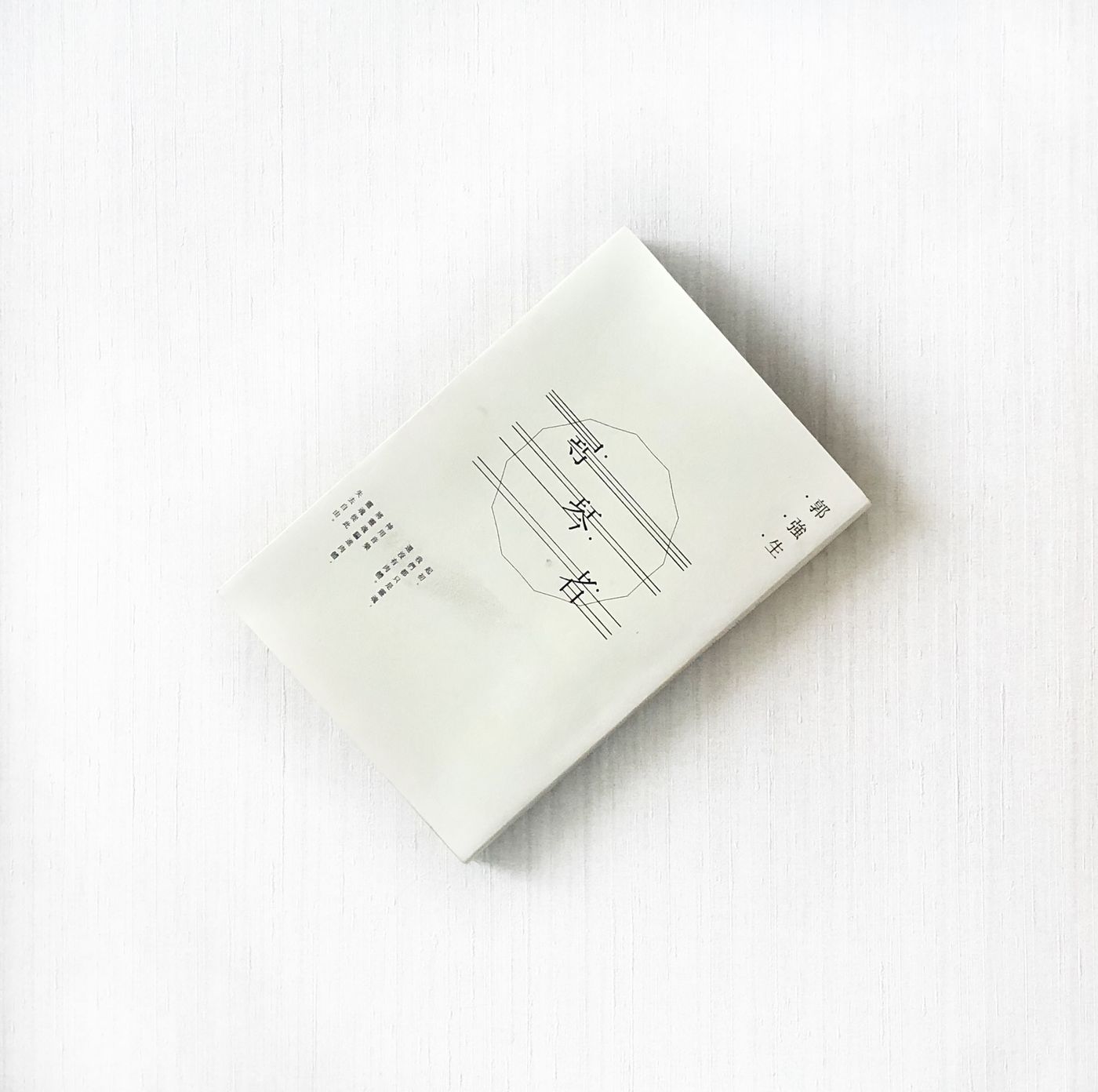說來慚愧,我已經不記得上一次看華文小說是什麼時候了,會知道郭強生,還是因為他經常幫翻譯文學寫推薦序。原來他曾經決定不再寫小說,而一停就是13年,能走到這一刻是多麼漫長阿。

這是一個關於情的故事,一種約定之情。整篇是帶點哀傷的餘味,因為裡面的腳色都失約了,也可以說是背叛了。
林桑的音樂家太太愛米麗罹病過世,留下來的鋼琴該怎麼處理,該送人嗎?還是留下?還是有其他的方法。主角是愛米麗的調音師,早就知道愛米麗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她生活早已「走音」,只有林桑沒聽出來而已。
主角年輕時所遇見的鋼琴家,讓他本以為可以寄情於此,結果鋼琴家失約了,忘了彼此的約定。主角刮花了他的鋼琴洩憤,但這條憤怒的痕跡是永遠留在他的身上。
林桑邀主角一同去紐約處理鋼琴買賣的事,合作關係的束縛讓兩人游移不定,在紐約的最後一天,林桑也失約了。
如同書裡的隱喻「總以為世間有一套現成的琴譜,教他們如何撥奏彼此。」
被拋下的人,該怎麼處理這個情(琴),該把這個情(琴)擱在哪裡比較好。可以像書裡講嗎,有一座鋼琴焚化廠,把廢棄無用的部分丟進去,燃燒、成灰。剩餘的部分繼續拼裝,成為下一座琴。這樣拆解後又合體,算不算是精神分裂,靈魂在嗎?
我很喜歡調音師這個腳色,帶一點敏感、帶一點孤僻的形象。他比演奏家更懂得樂器,卻從沒有人在意調音師是誰,他也懂得分寸,不搶風采。他有一雙敏銳的耳朵,為演奏者調節出最佳的音律,但從未為聆聽自己的生活,不曾替自己的生活調音。
多年來我已習慣,自己是那個孤立的黑鍵,另一個白鍵似乎永遠存在於指端無法企及的邊緣之外。
但說也奇妙,如此講求物理構造的樂器,卻能譜如此動人的旋律。針對鋼琴、調音師、旋律、聽覺、震動、靈魂...這些元素,故事裡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比喻。
鋼琴、演奏者、調音師,這三位的關係就像是一個婚姻諮商師與一對夫妻。一個神經質的演奏者和一台不完美的鋼琴送作堆後,調音師要負責勾勒出幸福想像。
作者也嘲諷了音樂圈的風氣,不只需要天分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和大師結緣才是關鍵。書中提到多個音樂家的故事,特別是像這兩位,堅持現場演奏的李赫特和堅持在錄音室彈奏的顧爾德,還有鋼琴家選不選琴這件事,究竟是懦弱還是泰然,訴說人生追尋並無一定方向,只需譜出符合心中的那首旋律。
有些人在樂器中尋找,有些人在歌聲中尋找,也有人更幸運,能夠在茫茫塵世間,找到了那個能夠喚醒與過去、現在與未來產生共鳴的一種震動。
也就是愛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