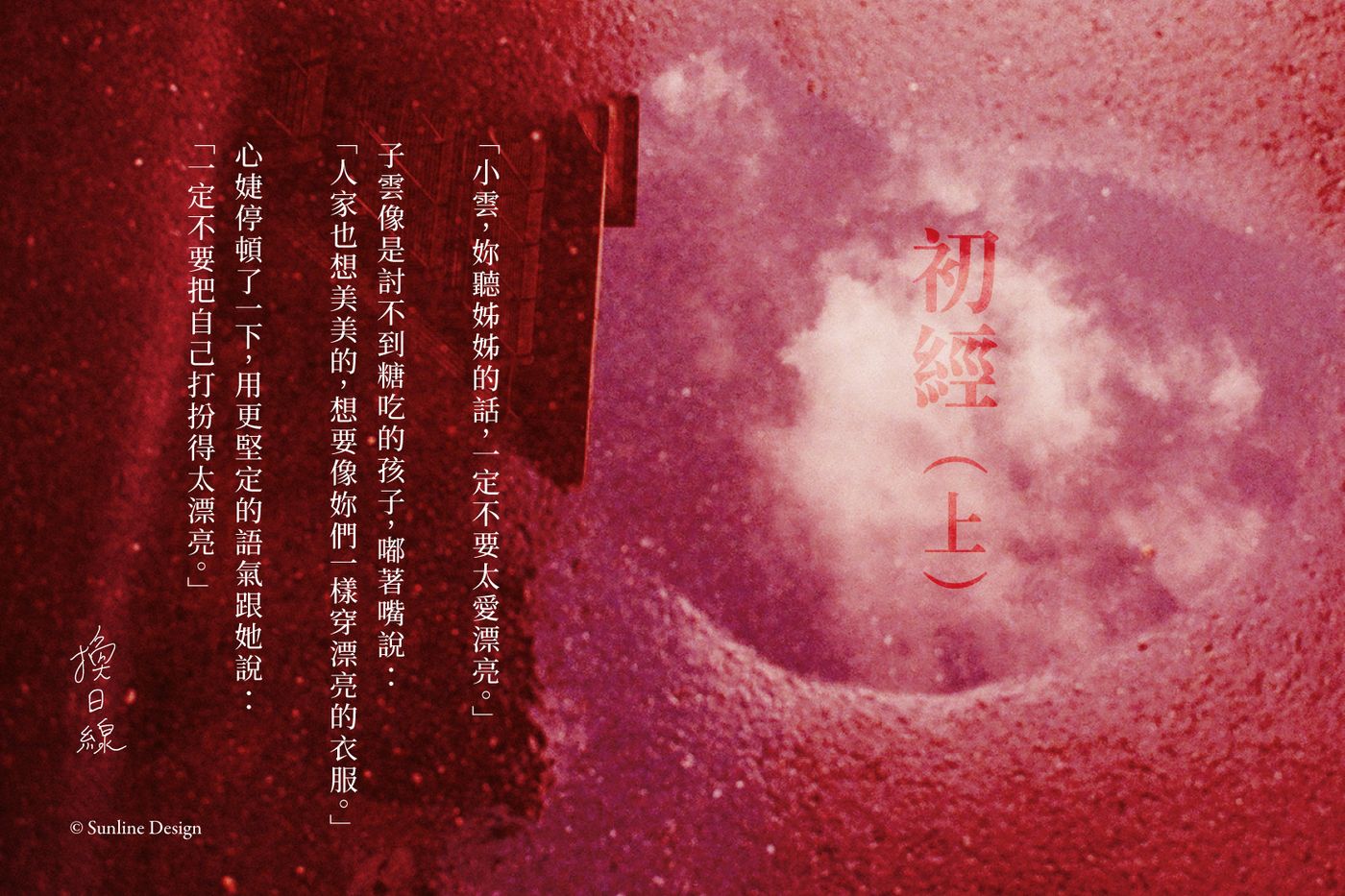我感覺自己腳髒的次數越來越頻繁,也常常在半夜突然覺得渾身不對勁就起身洗腳,卻怎麼也洗不去我感覺它的髒,我便索性地在任何可以光著腳丫的時候脫下鞋,踩在熱得發燙的柏油路上或是踩在下過雨的水窪,再不就是刻意地踩進公園的草地有著田裡那種帶著潮濕且溫潤的泥土裡,那樣我就有更多的理由,一直洗著我的腳。
每回于捷看見我在洗腳,總會拉來一張椅子,要我坐上它,他再坐在我腳邊的矮凳上,仔仔細細地幫我刷洗乾淨。
刷腳的時候我會跟于捷說起父親的事,說父親怎麼要求我要看起來像個城市的孩子,不可以玩那些鄉下孩子的遊戲,除了書以外,父親讓我學習許多在那時在鄉間只有我一個人孤單練習的才藝!
說到後來我離家唸大學還沒畢業就去工地打工,曬出一身黝黑回到老家被父親關在家門外時,我就會將我的雙腳從于捷眼前收回,再搶過于捷手上的軟毛刷,拚命地刷去我身上父親不要的汙穢。
有時于捷會輕輕地將我擁著問:「阿頡,要怎麼樣你才會好一點?」有時我會將于捷趕出浴室,直到我刷痛了我的雙腳看見鮮紅的血色從腳背一點一點滲出,我感覺了痛,才放開手上不知何時換上刮過皮膚會感到刺痛的洗衣刷。
畢業後我選了一個「感覺上」還可以搪塞父親的工作,不是做農,但是還算是做工的木工當作我的職業,我常常在一堆又一堆的木材裡搞得自己木屑或是東一塊西一塊有顏的漆。
每回休假回父母家的時候,我都刻意將自己打扮得白白淨淨,假裝自己是個坐辦公室畫設計圖的設計師。但我的雙腳仍然像兒時一樣喜歡踩在泥土裡,也經常在那些裁切木材堆起的木屑堆中踩著,木屑和泥土一樣,都有它們本身的氣味,聞著木屑散在空氣裡的木香總會想起兒時待在田邊看著父親的身影。
于捷擁著我的時候常這樣安撫我:「阿頡,你現在這樣也很好,木工很好啊!幫我做了很多的家具,還設計了一間很舒服的按摩間。」
有幾次我都順勢想讓于捷妥協,希望他能為了安撫我,跟我做一次愛。但他總是在親吻和擁抱之後,像父親將我隔在門外,卻從不告訴我他究竟對我有什麼期待?而我不知道,我還能替他完成什麼?還能給他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