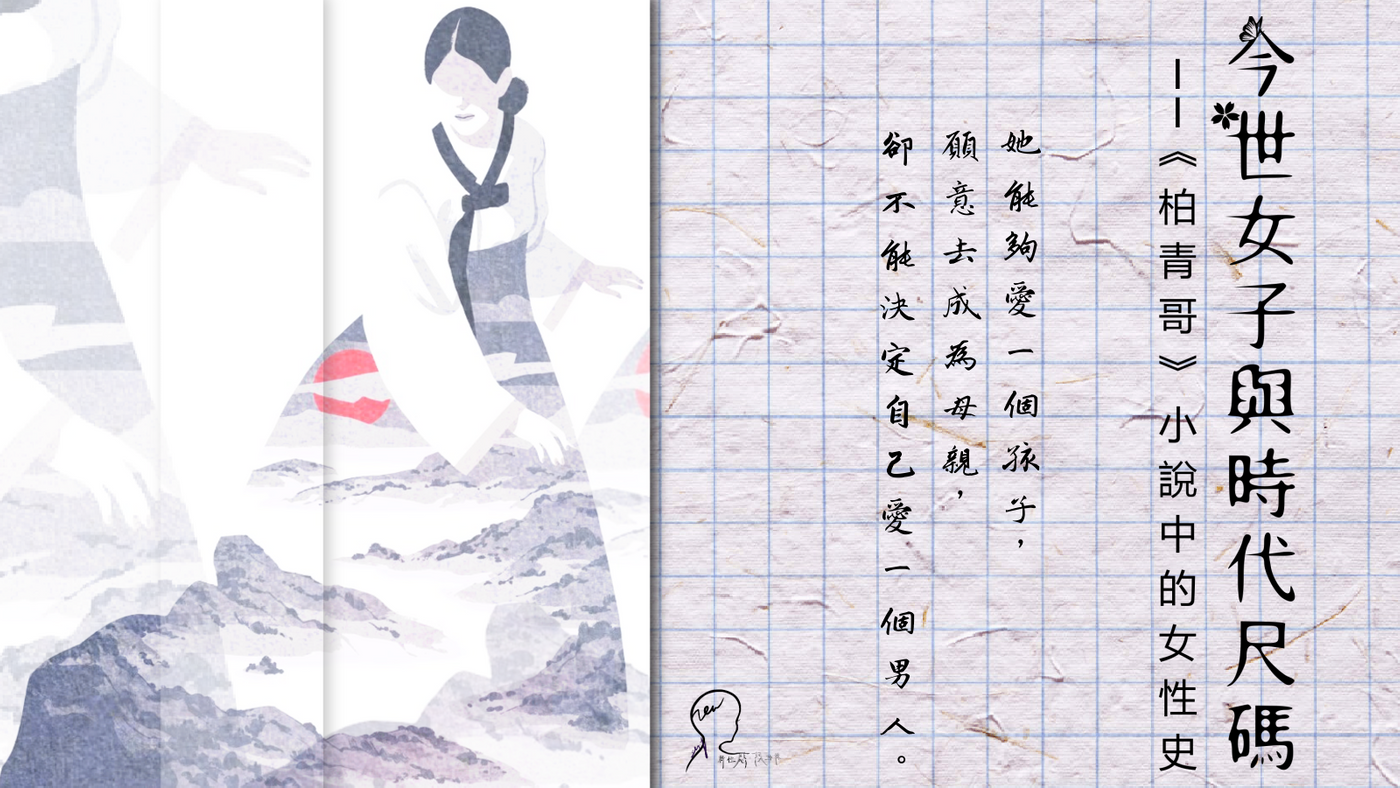童年到少女時期,有一段居無定所的日子。
七歲那年,父母離異,我的撫養權歸父親。
在中國農村是很常見的悲劇。男孩是家族的命根,女孩是家族的資產;父母離婚後,孩子被男方家族聯手「保護」,不讓母親帶走,教唆孩子恨自己的母親,甚至不讓母親探視⋯⋯只為切斷孩子和母親的情感關係。
通常父親無心育兒,孩子實質上由父親的女性親屬們撫養。女性親屬們在自己的夫家也沒有地位,孩子又成了女性親屬的家庭厭惡的累贅,或可以性剝削的對象。
都是我童年和少女時期經歷的切身之痛。
為了不招人厭棄,不引人注意,寄人籬下的日子,我千方百計地壓縮自己的存在感。盡量少佔用洗手間;不要吃太多吃太慢;少發出聲音,少說話;不要到處亂放物品,衣服晾乾了要快點收起來,尤其是內衣⋯⋯在本該伸展自己的身體和心靈的時期,我卻漸漸蜷縮了起來。
某一年假期要去遠方的親戚家,姑姑給我買了行李箱。
深藍色的,帆布材質,雙向拉鍊,上方有把手,底部有兩個小輪子,拉著它跑起來就隆隆作響。深藍色比別的顏色更不顯眼,正合我意。把自己所有的私人物品裝進去:衣服,日常用品,教材,幾本書,字典。
從那時起,我就成了「極簡主義者」,每次搬家必須捨棄一些。久而久之,心中有數,自己擁有的東西不可以太多。
曾經住到一戶人家,女主人每日打掃衛生時會把我的物品直接放回行李箱,我很快意識到了這個空間對我的排斥。明白自己待不久,也不想製造更多反感,便更加注意消除自己的痕跡;連洗漱用品都用完即收,好像在旅行中的人,隨時要趕路。
那些年,家,對我來說,就是我的深藍色行李箱。它在哪裡,我的家就在哪裡。只有它願意接納我的所有,允許我任意擺佈,任意填充。
那時還沒注意到,人所能利用的物理空間,會影響自己的心理空間。
高一那年,我喜歡的男生送給我一隻巨大的毛絨狗狗作為生日禮物,舉起來比我還高。
收到的當下,馬上開始厭惡它。
高中是寄宿制的,可以暫時放在床上,但我的心已經容不下任何超出行李箱尺寸的物品。我認為自己早晚會放棄的東西,不想對它投入感情。
毛絨狗在高中畢業時被我拋棄了。高考後家人想給我相親,讓我在讀大學前就找到婆家。我不想和別的農村女孩那樣早早結婚生子,毅然離家出走,去了省會的學妹家借住。隨身帶著的,還是深藍色的行李箱,那隻狗狗也注定塞不進去。
大學時再回到家,發現毛絨狗狗成了弟弟的玩具,髒兮兮的,眼睛也掉了一顆,尾巴爛了。一瞬間心碎了,怪自己為什麼沒有帶走它。
回想起來,我有很多想要留下來,卻因為裝不進行李箱而漸漸消失的物品:用了很多年的儲蓄罐,小學中學獲得的大量獎狀證書,高中收集的磁帶和《萌芽》雜誌⋯⋯
過早開始的「斷捨離」,似乎令我對自己,對人間更加冷漠。
直到如今還縈繞不散的虛無感,是否也因為我從小缺乏歸宿感,也缺乏存在感呢?我還沒有好好地展開自己,我的生命如此之輕。
也許這是我對「擁有自己的房子」執念之深的緣由吧。
我想有個家。愛讀書和文藝活動的我,從不缺少精神家園,匱乏的反而是物理上的空間。
縱然,結婚後我和自己的先生、貓、寶寶有了一個家,但我還需要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
不需要很大,不需要很豪華,不需要很值錢;它不需要滿足任何人、任何市場的需求,它只要屬於我,且有我愛的空間就好。
這個夢想在2019年實現了。我在日本的海邊買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
小屋在距離湘南的海岸線步行不到5分鐘的地方,只有1LDK,一樓是客廳、廚房、洗手間,二樓是臥室、浴室。
有很多窗戶,很多燈,從早到晚都可以很明亮。
在這裏可以睡覺,讀書,寫字,聽CD,練吉他,跳舞。
或者只是發呆。
心情不平靜時我還會去海邊跑步,帶回來的海螺就放在門前的信箱上。
為了獨居時的安全,我還簽約了SECOM,日本最大的安保服務提供商之一。
漸漸的身體變得舒展了,也不怕妨礙到誰了,也無所謂被誰注意了。
藍色行李箱在搬到日本之前就徹底壞了,被留在了山東的家的車庫裏。這棟小屋,變成了放大了幾百倍,不需要移動的行李箱,隨時等著我進去,在裡面蹦蹦跳跳。
我不知道這樣能不能治癒我的虛無感。房子是用錢買到的,但能不能把心安放於此,卻是自己的抉擇和能力。也許有一天,我又變得只需要一個行李箱,天地之大都是家⋯⋯那我就更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