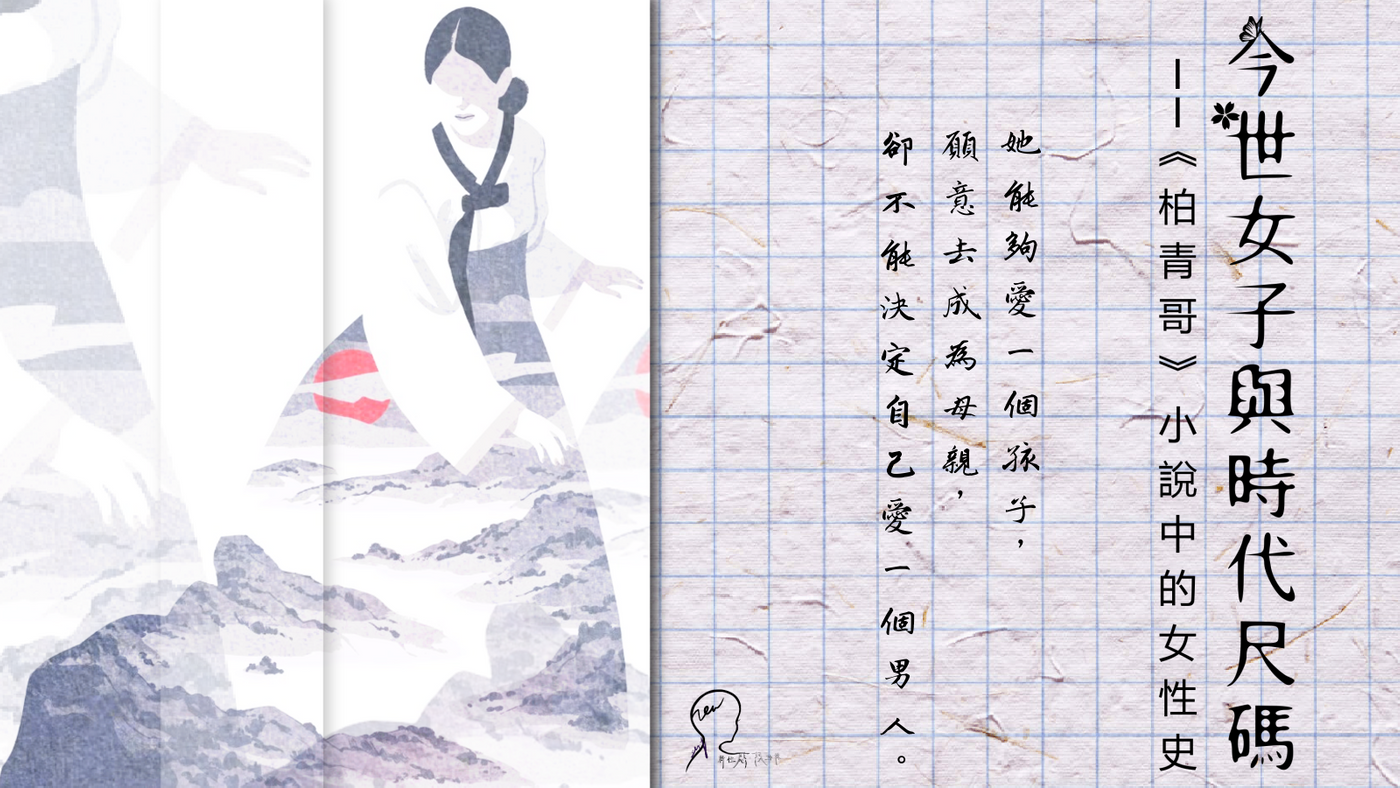我小時候經常做一個夢,戴著俄羅斯帽(護耳冬帽)、穿著軍綠長大衣的男人在火車上追趕著我們一家人。不確定那是存在基因中的記憶抑或邪門夢到上輩子的事(我明明不相信人有上輩子)。該夢境首次出於小學前,當時對蘇聯是沒有概念的,畢竟蘇聯解體時,我才剛上幼稚園,不可能有機會認識如此遙遠的國度。
或許是身為中國移民的台灣人,我從小就對共產黨、社會主義極為厭惡,那是一個兒童可以展現愛國情操的唯一方式。潛移默化的,長大後也自然而然排斥前蘇聯國家⋯⋯直到中學迷上某俄羅斯秘密警察的長篇小說,才開始對解體前的蘇聯有些好奇。
成年後的我才明白年幼時做著與經驗完全無關的夢境不是超自然的體驗,而是好久以前從長輩口中聽來的故事,甚至不一定是對我說,有時只是無意間聽到大人的對談,自行拼湊後烙在腦海中。最近讀一本書提到遊牧民族的吟遊詩人,原本專欄想寫口述詩歌創作,說說在巴黎看到的吉普賽人(法文稱為波希米亞),但在動筆前剛好讀到一段「波士尼亞穆斯林吟唱歌手」的敘述,同樣是以口說方式傳承著具有特色的歌曲,文章才改成「口述故事的影響」。
俄烏戰爭再度被提起的波士尼亞
多數人不太會關注波士尼亞,但說到三十年前的塞爾維亞對波士尼亞人的大屠殺還有耳聞——塞爾維亞將軍拉特科·穆拉迪奇的率領下屠殺八千餘名波士尼亞族的穆斯林,並驅逐了兩萬五到三萬名波士尼亞族人,那是九零年代蘇聯解體後震驚全球的種族清洗——今年三月隨著俄烏戰爭的開打,俄羅斯更以此威脅波士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欲加入北約可能造成與烏克蘭相似的局面,又讓世人再度關注該巴爾幹國家。
在二十世紀初,波士尼亞的穆斯林吟唱歌手們平均精通三、四十首歌,有些甚至精通百餘首。每首歌曲都是一個故事,有的要唱好幾個小時才能將其故事完整表達,這是一種口述創作的傳承,不同歌手演唱的歌詞皆有不同的故事版本,憑記憶將聽到的詩歌演譯出來,但無從得知其出處以及最初的版本為何。
吟唱是一種極為古老的藝術。公元前十世紀,古希臘時期的社會中就有該文化,詩人們口耳相傳將荷馬史詩流傳下來,那時代只有極為少數的權貴人士識字,吟遊詩人們當然是文盲,口述創作平民聽的故事,在不同區域添加著各文化特色,優秀的詩人被邀請到貴族家的晚宴表演——「故事」是他們得以進入上流社會的鑰匙——詩人們也學著即興創作添加諂媚主人家的故事情節。
遊吟詩人起初在社會中的地位是低的,到了公元前兩世紀,他們在古凱爾特人社會中享有特權,讚美部族首領、歌頌英雄事績、慶祝法律的頒發⋯⋯高盧地區的遊吟詩人在羅馬帝國時期已消失,而蘇格蘭蓋爾語地區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的《遊吟詩人》(Il trovatore)是威爾第中期的三大傑作之一,改編自西班牙同名劇話《El Trobador》,即是敘述吉普賽人的故事。中世紀以來,歐洲人眼中吉普賽人的出現和存在都是很神秘的,他們多半以占卜、歌舞為業,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而受到社會大眾歧視,這樣的敘述也在雨果的《巴黎聖母院》中亦可見。
街頭賣藝的吟遊詩人在現代社會中不復存在,但我們卻都受口述故事的影響。民間故事、預言傳說、宗教經典,你家和我家的家族史——早在我們能理解文字,甚至還不懂語言時,已從大人的口中聽到了許多。成長過程中,逐漸識字、學習文化和文學,最終發現自己的記憶深處早有了這些故事。
那些似曾相似的夢境,就是這樣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