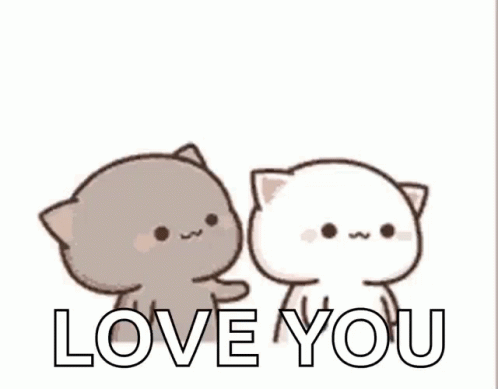我想說的是,
胖、瘦不過是人生當下的一個樣態,
就是這樣而已。
不用胖得理直氣壯,也不用瘦得驕傲,只需要好好地活得理直氣壯。就是生活而已,這是在胖瘦之外的。「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要說的是「我僅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不用再為我扣上這麼多的帽子與包袱,我也不用再把這些當作我的包袱」。
——《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p.151
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為系上的畢業公演寫了一個原創劇本,劇本內容關於一個致力於創作至忘我的小說家,如何失去與他人的連結,又如何找回自己作為作者的自覺,嘗試面對自己和周遭的衝突。很混亂嗎?那再配上舞台燈光的明暗,道具的上下場與場景的移轉,相信你會被嚇死。
我本身是中文系雙主修英美語文學系,有不少文學科系的學生和我反應,這齣劇本映照出了他們自身與外界、甚至和家人及朋友的衝突。他們從中得到了共感和抒發。
另外還有許多來自「大人們」,包括部分文學系教授,和我回饋:故事中的「小說家」,真是一個非常討人厭的腳色。
我對於這個感想非常震驚。
當然他們也詳細告訴我討厭腳色的原因:腳色過於自我中心、不顧周遭的變異,連家人中有人離開都不知道(劇情中的重大變故是他的妹妹去世),總而言之就是一個自私又自以為是的人云云。
過了好一段時間,我和朋友討論起這件事,我說:「那不就是一種狀態嗎?我是說,『小說家』和他當時表現發生的那一連串故事和迷惑,不就是人的一種狀態嗎?」
狀態有各式各樣的,怎麼會有好壞之分,甚至還必須得要被指指點點、被厭惡指正呢?
我是一個有著胖子身體的人,
我就是這樣的胖子。
就只是這樣。
《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的作者蔡培元,提及「陳芳明在法農(Frantz Fanon)著名的《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書裡的序中,寫到一個小故事。
法農在巴黎時,已經會說流暢的法語,是法國社會裡所尊敬的心理醫師。有一天他在巴黎街頭散步時,他聽到一個法國小孩對他說了一句簡單的話: 『髒黑鬼。』經過長期培養起來的尊嚴,全然禁不起如此一句鄙夷的稱呼。
他的文化價值開始崩解。對法農來說,文化是個白色的面具,黑皮膚才是生命的實相。
蔡培元反思,對他來說,生命中的核心斷裂是什麼?他發現他原來是個有個瘦靈魂的胖子,他必須要承認面對這個不願面對的瘦靈魂、胖身體,去理解他生命中避之唯恐不及的真相,才能建立自我,去找到「認識自己」的論述。」
我仍在幽冥之中,卻發現原來我自己就是光
當軌道雜草逐漸除去,蔡培元駕駛列車,發現一片荒蕪荊棘過後,那個「胖的我」,根本不是他。「他是蔡培元」。胖瘦不是問題,只是人生的一種狀態。
離開論述的詭計框架,跳脫胖瘦的魔鬼步伐,我就是我,就這麼簡單。
你呢,你是怎樣的「人」?
我跑著跑著雙腳也慢慢累了/
沿途的風景也漸漸地看膩了/
想起出發前熱的血還是很熱
外面的風越吹越來越冷/世界變得不同了/
我的朋友是否堅持著/我愛的人還在找對的人/
風的方向又轉了
我不要不要就這樣地過/那你呢 那你呢
會不會跟著我一起走 尋找著/
那黑暗裡 唯一的星空
──宇宙人樂團〈那你呢(And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