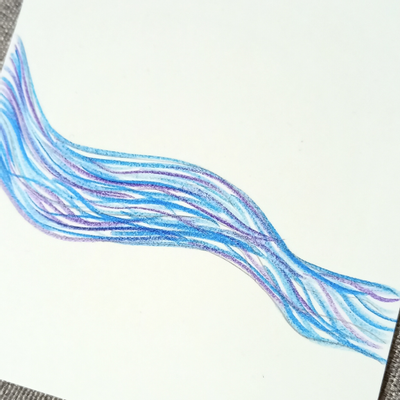遺忘之地 - Golden Beach
我們在暴雨的黑夜推開大門,帶著傷,肩並肩。光頭的宅內,他妻子已在門口等候多時,再度見到光頭時她眼神充滿光芒,夾雜淚水的擁抱與親吻。那種生離死別後重逢的感動,夫妻之間偉大的愛使我默默退去,將剩下的行李拿下車。
風暴在短時間內不會離去,光頭家人好心收留我兩個晚上。
這兩天,我體會了印度家庭的待客之道。他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們在耶穌神像的見證下禱告,餐桌前品嚐美味的料理。
光頭的兒子正逢考大學的年紀,他兩眼睜大地看著我,這大概是第一次有位黃皮猴子到家裡作客。從未踏上亞洲的印裔澳籍二代,與驚訝中印文化差距的台灣年輕人。他吵著跟老爸說一定要去東方看看我彷彿看到以前的自己,當見到外國人時的好奇、又帶點陌生。他對東方世界的未知與嚮往,來自於我嘴裡與手勢的比劃。
他帶給我破除東方亞洲為中心的思想,
我再也不會說我是亞洲人,我是東亞來的。
隔日正逢周日,即便外頭颳風暴雨,他們帶著我去教堂禱告。教堂內聚集各式種族,身穿他們種族的傳統服飾,女子頭披白布。光頭妻子穿著一身鮮麗的絲綢,與大家跪在前方,雙手合十緊握,嘴裡默念著我聽不懂的禱告詞,戴著高帽的教皇拿著聖杖,站在耶穌神像前念著經文…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下跪不是跪女友,而是聆聽聖歌與耶穌的教誨。
經過了光頭家人一日的款待,我等於是吃飽穿足、滿載補給的出發。
事隔一日的風雨,天空再度放晴,光頭用方言給我誠摯的祝福,離別時給我的擁抱,短短幾天的相識卻帶有不捨。
他們用實際的作為,詮釋了南印度的待客之道。
這是最成功的國際交流,也讓我心中那份想前往印度的種子萌芽。
引擎再度發動,一路往東前進,若地圖的顯示沒錯的話,我將正式踏上東岸。據光頭離別前的描述,五個小時的車程將會到達一座漂亮的出海口城市Lake Entrance,一切順利的話能在入夜前抵達。
事情從未如規劃所示,對別人而言或許是旅行的災難,對我來說卻是樂趣的所在。我不怎能知道,這五小時的車程竟花了我三天。
那是一條不起眼的道路,在注意到它時,純粹因為我相信時間夠多。看著前方廣闊的荒野叢林,我將目光放到地圖上的商店標記,在前方的一座城市買了近三天的食物補給。
事實證明了,這個選擇並沒有錯。
那個地方叫做Golden Beach,與人們熟知的Brisbane旁的富人區是完全一樣的名字,然而位置在Victoria右下角,是一個毫無人煙的海灘。在一條終究必須折返的道路上,超過20個免費露營點,坐落在綿延無際的海灘上,藏在防風林之中。
所有的補給靠向一家貴到爆炸的傳統雜貨店,唯一的水源也是,我露營車上那兩條大水箱終於派上用場。將車裝到過載,隨機選了一個距離雜貨店遙遠的露營點,一個無網路、人煙罕至的防風林內,卻有一整個絕佳的賞海美景。
我隨機宣布開始與世界隔離。

處在露營地的人不只我一位,還有一對來自昆州的年輕澳洲情侶。很明顯,除了友善的笑容外,他們並不喜歡跟陌生人交談。我跟他們簡單的打個招呼,隨後就跑到沙灘上玩耍。
一望無際的沙灘上除了一艘只剩骨架的船什麼都沒有,我站在上頭感受遠方的風,跟海鷗聊著自己的孤單,再回頭走向自己的車旁。

這時旁邊多了一台澳洲產的吉普車。
一位希臘裔瑞克與莫蒂中的白袍科學家從車旁現身,用土澳式粗暴的語氣問我這邊方不方便他停車。我笑著點點頭,一方面展現台灣人的有禮,邊望向他手裡那把足以敲死我的鏟子。
他直直將鏟子插下我們倆之間的沙地,持續往下挖。看著他載滿一車的木頭,我瞬間了解什麼。反射動作使我將木頭拿下,在地上疊成一座哥德式建築。
不善社交的澳洲情侶呆呆地看著我們,要知道,在澳洲亂生火可是違法的,然而地上明顯有許多人挖溝生火後的痕跡,很明顯,身為外國人的我們倆並不怎麼關心這道法律。
挖到可以把我埋了的深度,日落配合著浪漫的火焰,我們將自己的車停到火的旁邊擋風。我將後車門打開,好讓我能躺在床上看火光。木頭燃燒產生的爆炸聲之中,他從自身的日常,跟我聊到隨身攜帶鏈鋸的方便性。
既防身,又有無限的木材來源,有時還能將砍下的木材當額外收入。
邊說,他從車上拿下一把手臂長的小鏈鋸,在我面前將一棵樹砍下。隨後他再從車內拿了兩打酒,問也不問放進我車內的冰箱。我想他再從車上拿出一張夏威夷的來回機票我都不會意外。
「Cheers!」
我不認識他,男人的交流就是可以如此簡單粗暴。
除了火光只剩下滿天星空,海浪拍打黑暗的灘頭,沒有網路的沙灘上,我們如古人般望著火。我躺在車內的床上,眼神漸漸闔上。
我從夢中驚醒,我驚慌竟然忘記把車門關上。此時天已破曉,放著紫藍色的光芒。昨晚的不真實如場夢,面前的那叢火提醒這場夢的真實。火從入夜持續到日出,在火堆旁邊的,則是晚上看不清楚的大型帳篷,裏頭空無一人,所有零件散落各處。
希臘人從灘頭上來,打著赤腳,兩手各提著一打釣魚配備。看來他昨天釣了一整晚。
他看到我起床,笑容露出使眼眸旁多了些魚尾紋,問我想不想一塊釣魚。一晚沒睡似乎沒讓他感到疲倦,熱情的喊叫比海鷗還大聲。
灘釣是場需要臂力的運動,比我還大支的釣竿需要用全身的力氣甩出,強大的海流使我受足了苦頭。我們躺在沙灘上,累到無法移動的身體盡由陽光曝曬,我還是不認識他,不過我陪他釣了一整天的魚,他的笑容如同《一路玩到掛》的真實版男主角。
我們一路釣到中暑,適逢天色將黑,兩人各提一桶螃蟹回到沙灘後的防風林。昨日的木炭僅剩下幾縷煙,要升起來依然容易,而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活海鮮下肚的時刻。
夜晚再度來臨,那對冷漠的情侶早已離去,整個防風林剩下我們倆。
一口黃湯下肚,他跟我說他的故事,正經歷人生苦難的父親、醫生處方箋上的人生終點、離婚的壓力與對女兒的關愛、拋開一切到海邊享受他最愛的釣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