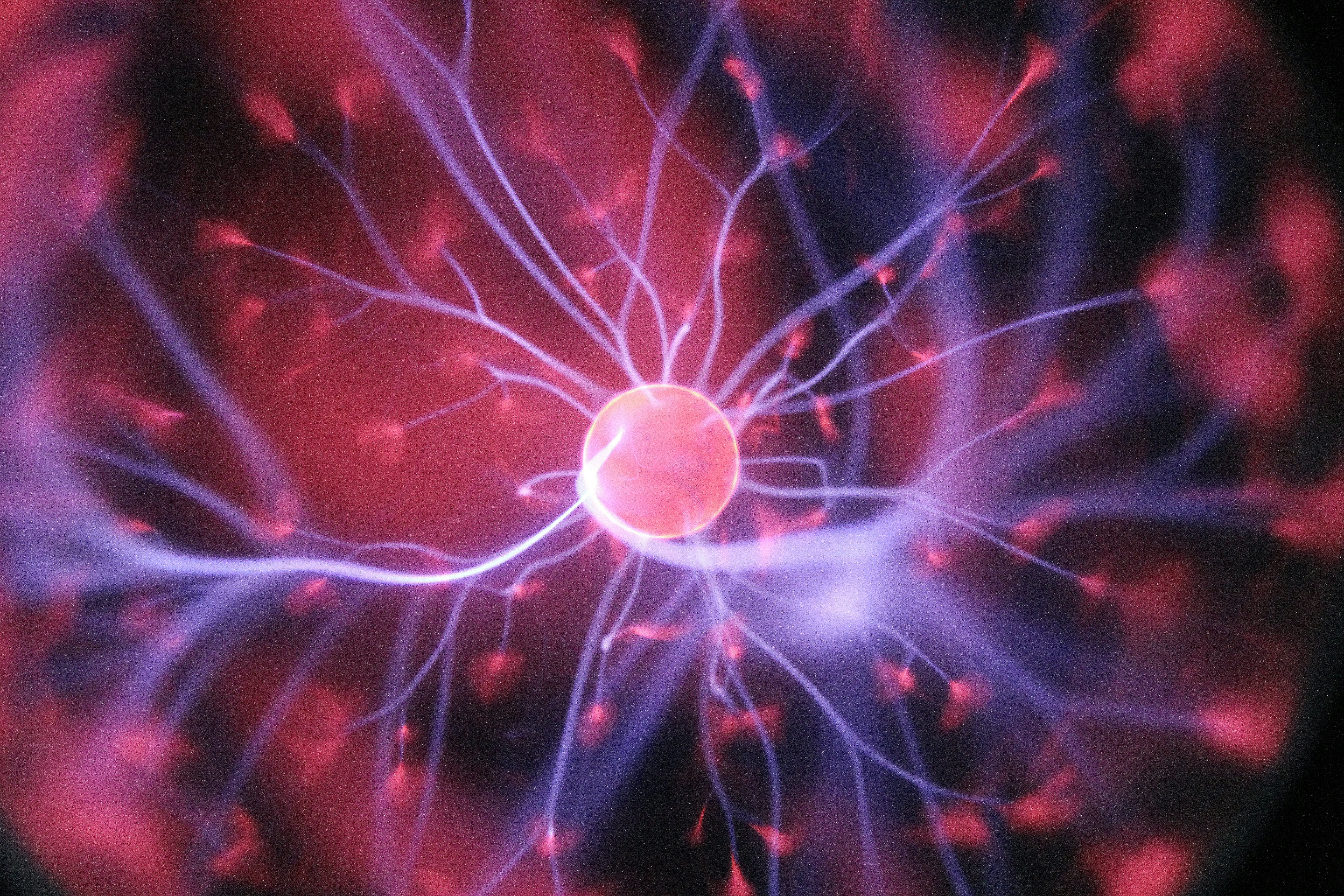方格精選
毛尖:我把此書獻給所有和我一樣,被電影鬼迷了心竅的朋友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沒有誰是殺不死的,但是〉,《夜短夢長》台灣版自序
電影評論寫了二十年,影評人也逐漸成了讓人陽痿的身份,不過好在電影輝煌過一百年,看完爛片回家看個牛片,有時甚至覺得爛片也有爛片的好,看了《東成西就2011》,才深切知道一九九三年的《東成西就》有多好。人生熙熙攘攘,沒見過張國榮扮演的程蝶衣,怎麼就能說姜文不適合這個角色?
不過,姜文說他不想演霸王,沒難度,要演就得演虞姬,倒讓我別有好感。這才符合:電—影—夢。而對我自己來說,把這些年看過的好電影,長短鏡頭蒙太奇般剪輯在一起,也就是我的電影夢。譬如說,在描述一列夢想火車時,我希望是,《將軍號》(The General ; 1926)裡的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擔任火車司機,《士兵之歌》(Ballad of a Soldier ; 1959)裡的「魔鬼中尉」是列車長,然後,裝上希區考克的「火車怪客」,向著由《嚴密監視的列車》(Ostre Sledovan Vlaky; 1966)主人翁米洛斯擔任調度員的車站進發。
火車,男人和少年,老婆和小老婆,欲望和謀殺,愛和歡愉,這些電影關鍵詞,構成了本書的第一輯。猛衝猛打,縱馬疾馳,現實人生中沒有快意江湖的太陽,我們至少還有電影。殘破的人生和被鄙棄的廢物都能在電影中獲得一席之地,他們粗礪地咄咄逼人地叫停高頭大馬:來,到銀幕前比試一下。
生機勃勃就是美。我喜歡電影裡的這種莎士比亞傳統,銀幕締造著全新的人類學概念。費里尼鏡頭裡,暴跳如雷的男人、乳頭碩大的女人、獅面的數學老師、被荷爾蒙弄得急火攻心的少年,不管是英雄還是妓女,顯赫還是潦倒,他們都是銀幕神族,我們藉此確認此生不虛,確認自己也曾被世界之初的火光照耀。我把費里尼的《阿瑪珂德》(Amarcord ; 1973)和《站在我這邊》(Stand by Me ; 1986)、《逍遙騎士》(Easy Rider ; 1969)寫在一起,集合在「火」下,就是為了緬懷我們曾經住過的奧林帕斯山,在人類的童年時代,男人說要有火,就會有火。
那是二○一六年。
二○一七年開頭,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看一部電影,好像被一種奇怪的電影虛無主義籠罩,我準備棄絕電影重回經典文學的懷抱,我一天看一本小說,重溫《傲慢與偏見》,重溫《紅樓夢》、《金瓶梅》,懷著脫胎換骨的決心堅持了半個月左右,在一家服裝店看到老闆在搜亞蘭.德倫(Alain Delon)照片,他說門口擺的這款風衣據傳是從亞蘭.德倫電影中複製的。我溜了一眼那款亞蘭.德倫,《午後七點零七分》(Le Samouraï; 1967)啊,馬上回家翻出一堆梅爾維爾(Sean-Pierre Melville),重開影戒。
而回頭想想,半輩子過去,電影不僅成了我生活的度量衡,一節課是半場電影,一個暑假是一千場,四年大學是兩萬場,活一百歲,就是活過四十萬部電影。電影,似乎也只有電影,讓我完整地走過了《戀人絮語》描述的所有階段,包括沉醉、屈從、相思、執著、焦灼、等待、災難、挫折、慵倦以及輕生、溫和、節制等,面對電影,就像羅蘭.巴特說的,我控制不住被它席捲而去,而這一去,就像「二進宮」的賭徒,回頭無岸。
二○一七年的第二輯,就是用賭徒視野串起的影視小史。我本來的願望是寫出一副牌,包括大王小王,老A老K,黑桃紅勾,再一路從十到九,八,七,六,五,四,三和二,但是沒有全部完成,最後因為年關降臨,匆匆〈結尾〉。這一輯,雖然電影主題和主人翁都風馬牛不相及,比如影史二貨和梁朝偉扮演的三個情人角色,一個是最熱鬧的大怪路子,一個是相對高冷的惠斯特橋牌,但是,我們看影視劇,不就是為了讓天空和大地相遇,讓恨和愛,善和惡,成為彼此的精神食糧嗎?
收在此書中的文章,除了〈大於鈕釦,小於鴿子蛋:三個梁朝偉和愛情符號學〉發在《文藝爭鳴》,其他都刊發在《收穫》上。感謝歐梵老師賜序。我的電影口味可能跟歐梵老師不一樣,但是老師談起楚浮談起高達的飛揚神情,卻讓我知道,好電影就是青春藥。
而對於我自己來說,這麼多年,花了這麼多時間看了這麼多電影,有時我會想起柏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一句話:「我一直到五十八歲才走出青春期。」柏格曼說的青春期,強調的是悲慘,但我依然認同這句話,因為它揭示了電影的力量。歲月殘酷,電影殘酷,但影迷不老。銀幕高調也好低音也好,從來不會真正讓我們軟弱,就像看《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 ; 2011-2019),我們經得起前面七季的血腥史詩,也承受得住最後一季的嘩啦雪崩。
寫本書最後兩千字的時候,《權力遊戲》的終季還沒有降臨,那時我和世界上成千上億的《權力遊戲》迷一樣,被此劇的莎士比亞氣質弄得心魂蕩漾,人的尺寸可以多麼龐大,生死都乾杯一樣,愛情從來不是主唱,政治才是終極boss。然後呢,二○一九年的夏天還沒有開始,我們就劈哩啪啦被打腫了臉。夜王呼啦死了,龍媽呼啦瘋了,瑟曦呼啦軟了,所有的人設都崩塌,連龍設都完蛋。最後,看到情人版詹姆回到瑟曦身邊,直接毀掉騎士版詹姆,我默默地唸了一遍此劇箴言:凡人皆有一死。神劇也是。
生活是殘酷的,但是,我們影迷沉淪了嗎。當天晚上,我就開始收看《破冰行動》(2019),「破冰」了以後,我又看《金錢戰爭》(Billions ; 2016-2019)看《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 1986)。沒有誰是殺不死的,但是,影迷永遠有力氣起頭來,像艾莉亞那樣,面對死神說:Not today。
這是電影原力。這是教我們哭著哭著又能笑的生命掌力。所以,我把此書獻給所有和我一樣,被電影鬼迷了心竅的朋友。道路,房屋,花草,都會消逝,但是它們只要出現在銀幕上,就能千萬次地重新活過來。只要我們背後還有光投向前方,幕布就能變成綢緞,重新把我們擦得閃閃發亮,擦得我們好像從來沒有經歷過傷害,擦得我們好像還是新的。
─ 全文收錄於:毛尖最新電影文集《夜短夢長》台灣版─
毛尖,本名就是毛尖,是愛喝茶的爺爺給她取的。擁有「外語學士、中文碩士、人文學博士」三頭銜,觀影逾萬部,被譽為「當代電影與文學的目擊者」。
她看電影,看電影深處的奇妙情思 她寫電影,寫電影內外的百味人生 11篇電影專文評論,寫閱讀,寫人生。她曾玩笑說,去世後的墓誌銘上寫十部影劇就夠了──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322會員
282內容數
勒利•索可洛夫(Lale Sokolov,1916~2006)人生中有超過50年都懷著一個秘密,這段不能說出口的往事發生於二戰時的歐洲,那時,納粹德國人對猶太人做出不可思議的恐怖事跡。80歲以前,勒利完全無法向人說出這段過去,即使他的生活離那個恐怖地方有千里遠。
勒利曾經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刺青師。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