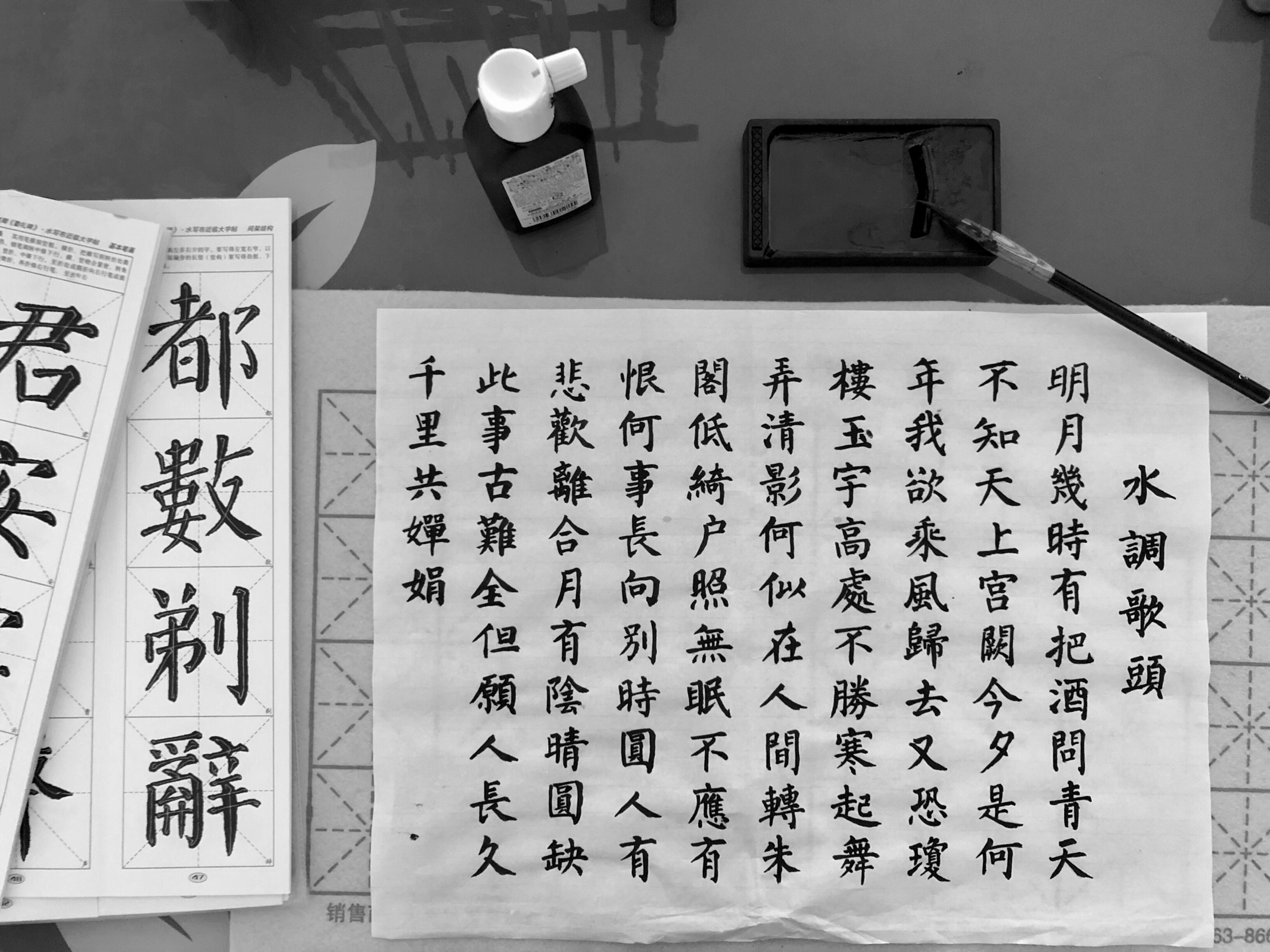〈自欺 Malicious〉第八回(全文完)

過了半晌,他面露微笑,側過身,瞇起雙眼,注視那排儀式般的木製樂器盒。那雙飽含氣神的目光,比望見聖潔之物的得道之人更為清靈,宛如親見某種至上力量,略感刺眼似地覷起眸子,不願也不敢直視。
「祟胤言同學,你參透的事物、理解的程度與看透的層次,比我想像中深入得多。儘管如此,透過眼見元素,聰明絕頂的你,是否願意嘗試推論深藏於我靈魂內的濃烈偏執,以及難以解釋的獨有思想呢?」
他投來的視線,除了尋求理解的強烈渴望,更飽含著對我毫無道理的期盼。
三哥曾說,世上並無愚蠢之人,唯有凡人與非凡之人的差異。凡與非凡,由我判讀,切合之界點在於主觀對於自我的探尋,與他人對於自身的照看,是否能夠連成一線。理想狀態,探尋得出的真實自我,理當符合外界他人對於自身的評價與理解;反之,偏異狀態,即為主觀探求所得之自我,與他人照看得來的自身評析,存在顯著落差。
前者,即屬平凡;後者,即為非凡。
深知常人所不能知、深明常人所不能明、深得常人所不能得者,追尋之自我將更深層,也更不可測。難以估量的自身,顯然難由他人鑒察,終究落得偏異、怪異、變異之流。
所謂非凡,正是如此。
眼前的消瘦男子,不單只是音樂老師,更是一名嘗試獲取他人認同,偏異、怪異、變異的非凡之人。
與我相同,別無二致。
沉澱心神,我悠悠開口。
「假設生命之軀自頭至尾歸屬一體,缺失頭顱,即屬不完整之物。」
望著顯露在外的無頭倉鼠,我側著頭,望向乾淨的切面,平整光滑的模樣顯然經過特殊處理,毫無死物之感,彷彿自始至終,即為無頭狀態。
「置於木盒之中,所取代者為樂器。」
依序輕敲口琴、小號與小提琴的樂盒,我說:
「假設,樂器需要人的吹奏方屬完整,則與樂器連結,共組完整形體的部分,即為生命體之發聲部位──口腔、喉嚨與頭顱。所謂完整,少而缺,多則盈,不容一絲增減。換言之,失去頭顱的肉身,如同不完整的樂器本身,恰好匹配空出的樂器木盒,此乃實質意義之完整;此外,木盒本身,論其材質與外型,形同無頭遺骸之棺,此為抽象意義之完整。由裡而外,由實體至抽象,看似毫無意義且偏離常規的惡行,便有了自成一格的哲理思維。」
望著面無表情的音樂老師,我倆之間瀰漫一股彷彿將維持永恆的漫長沉默。
他的表情並未改變,雙眸仍然無神,仍舊看似漠不關心。
須臾,視線明顯捕捉到他微微縮動的眼角。
這一剎那,我明白自己看清了這場儀式背後所彰顯的,抽象的真實意義。
「如你所說,」他抹抹鼻尖說:「每項樂器均為缺失頭顱的軀體,琴頸之上,所謂的琴首,不過是空虛的無謂裝飾,物體終為死物,並無靈魂,無法取代真實生命的神聖軀體。唯有將摒除無用之處的實體肉身,置於木盒虛無的狹小空間內,方能於實虛的虧盈之間得到真正的完整,化作聖物。」
「空出的木盒,缺少原來置於其內的樂器,正如一副失去聖軀的靈棺。」
音樂老師輕笑一聲,搖搖頭,撫著前額。
這是對峙以來,第一次見到他發自內心的笑。眼前之人,彷彿一生未曾如此舒坦般,仰首喀笑,以極不自然的聲調,發出一身專屬的獨特笑聲。
暗自鬆一口氣的我,也隨之揚起嘴角。
探尋、理解並剖析他人的內心哲理的過程,讓我感到恐懼,而那股恐懼背後的無窮樂趣,是最富價值,獨歸於我的美妙醍醐味。
「現在呢?」音樂老師望著我說:「你有什麼打算?」
「坦白說,沒有任何打算。」
「不報警?」
我搖了搖頭。
「儘管知道我是個殺了人的傢伙?」
我點了點頭。
「說實話,我沒想過能遇到如此聰慧,卻又如此難以理解之人。」
「坦白說,我也沒想到能在此地見到如此有趣的怪異案件。」
「有趣?」他微蹙眉宇,瞇起雙眼。「你不覺得可怕?」
「我覺得有趣極了。」
「絲毫不認為,我這種詭異的精神變態應當伏法?」
「那是你的事。」我笑了笑,說:「不關我的事。」
「你來此處,不是為了救回遭到拘禁的鏡寧宵,只是單純向我證明,整起計畫已然被你看透?」
這是個陷阱題。
我眨了眨眼,刻意皺起眉頭,裝出略感不解的模樣。
「雖然不知您為何、又從何產生如此怪異的想法,但鏡寧宵的死活,從頭到尾,自始至終,與我無關。」
「是嗎?」
「要非如此,又何必將她充作誘餌,引你上鉤?」
這句話似乎說服了他,只見其輕輕頷首,不再提問。
步向右側,我立於低音提琴的精緻木盒前,以指節輕敲兩回。琴盒發出低沉的叩響,顯然亦已填裝某物。
不住搖頭的我,竟不覺笑了。
「老師。」
我露齒燦笑,凝望不解此意的音樂老師。
「倘若可行,能否將這項『聖物』轉贈予我?」
聽聞此言,他不禁竊笑,攤開雙手,聳聳肩說:
「整起計畫在你打開辦公室之門時,便已化為烏有。畢竟,所謂的哲理,所謂的意念,均為專屬於己的私密探求;一旦為人所察,便遭污染,所得結果必也毫無意義。」
「是這樣嗎?」
「是的。」
「那您之後有何打算?」
「有何打算……」
這個簡單問題似乎考倒了思維繁複的他。
他思忖半晌,說:
「未來的事,不在我的規劃範圍。無論如何,這些收藏品,這些極富爭議的聖物們,就交給你了。」
「謝謝老師。」
「祟胤言同學,有件事你還是錯了。」
「請老師指教。」
「你剛才說,鏡寧宵同學的死活與你無關,對嗎?」
「是這樣沒錯。」
「那你此刻緊擰的左腕,又是怎麼回事?」
左腕?
我低下頭,向左側望,發現自己的左手指尖,正使勁地扎刺掌心。
「顯然,你的自我追尋還在持續呢,孩子。」
他給了我一個乾淨無暇的笑靨,笑著說:
「那個女孩,還需要兩個小時才會清醒。我想,若你在她甦醒之前,耐著性子伴於身旁,或許便能明白自己推論中的不足之處。」
「不足之處?」
「為何我沒割下她的頭顱,此一不合既定模式的真正原因。」
他擺擺手,轉過身子背對我,頭也不回地離開這間蘊藏個人哲理,卻堆砌了數具遺骸的寬敞辦公室。
望著自己左掌上發紫的的指甲細痕,我不禁覺得可笑。
看來,擅長說謊的人,終究精於自欺。
而自欺,終究難以不存惡意。
◈ ◈ ◈
雙手雙腳蜷曲於低音提琴木盒內的黑髮少女,發出貓一般細小的低吟。
她使勁擠了擠眼皮,發出更長的嬌聲呻吟,好似伸了個舒服的懶腰,吁出一大口氣。數秒之後,花費一番功夫睜開雙眼,少女睡眼惺忪地凝視前方,滿臉笑意的我。
翹起二郎腿,坐在有些堅硬的辦公椅上,我闔起即將閱畢、從她書包裡「借」來的文庫本《死的況味》,撐著下巴,把整張臉湊上前去。
「早啊,不可愛的睡美人。」
「唔唔……」她皺起眉頭,撇過臉去,說:「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舒服得讓妳睡了四個多小時的地方。」
「才不是。」
「那妳回想一下,自己怎麼來到這裡的。」
瞪了我一眼,鏡寧宵撥開散於左頰的髮絲,環顧四周。
「被你氣得受不了後,我離開教室,打算去狗籠附近找線索……」
「等等,氣得受不了?我可不記得那時的妳有這種表情反應。」
「總之,」她皺起眉頭,使勁瞪我,說:「在前往實驗花圃的路上,遇到了音樂老師,他說自己有些私人的事情想請教我。那時,我覺得有些奇怪,因為他理當請了一週的假,怎會出現於此;因此,便隨著他來到這間辦公室,喝了一杯味道極好的玫瑰花茶──」
「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唔唔,居然笑成這樣,太過份了。」
經此提醒,才發現自己不僅揚起嘴角,甚至露出牙列,滿溢的笑靨就這麼赤裸裸地正對著她。
闔上雙唇,斂起笑容,我清了清喉嚨。
「鏡寧宵小姐──不,小宵姑娘。」
「做什麼啦?」
「貴府的長輩們未曾教導過妳,作為女孩子身,實不該隨意應人之邀,隻身前往密閉之處嗎?」
「我是因為覺得奇怪,才跟過來的。」
「貴府的長輩們未曾教導過妳,作為女孩子身,與男人共處一室時實不應飲用內容不明的液體?」
「……對不起嘛。」
真是個乖女孩,居然坦率地道歉了。
摀住嘴,掩蓋險些再次綻露的笑靨,我定起心神,悠悠開口。
「在妳沉睡的這段期間,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為了避免資訊量過大,導致您弱小無用的腦袋不堪負荷,請容我自作主張,將其統整為一件好事,與一件壞事。」
「祟胤言。」
「請說。」
「我哪裡得罪你了嗎?」
「沒有,請姑且當作我現在心情很好。」
「那,」她噘著嘴,似乎對我迂迴的答案感到不滿。「先聽好消息。」
「好消息是,連續梟首事件的行為人,確定不會再犯了。」
「咦?」
鏡寧宵瞪圓雙眼,極其驚訝的神情卻飽含了濃厚的失落之感。
「難不成,你找到犯人了?」
「怎麼可能。」
「那你怎麼知道他不會再犯?」
「這點,與壞消息有著密切關聯。」
「那,」她鼓起腮幫子說:「我要聽壞消息。」
「壞消息是,關於連續梟首事件,從此刻起,我不會向妳提供任何資訊了。」
「咦咦──」鏡寧宵拉高音量,喊道:「這也太狡猾了!」
「妳是了解我的,所謂樂趣,比起眾樂樂,神秘的獨樂樂才是正鵠。」
「你真的超級怪!」
「唯獨不想被妳這麼說。」
「討厭你!」
鏡寧宵的腮幫子鼓得更高了,氣呼呼的模樣,搭配那頭烏黑秀麗的長髮,以及蒼白如雪,幾近遺體的柔滑肌膚,竟矛盾得有些可愛。
她步出琴盒,深深吸入一大口氣。
「還有一件事。」
「又怎麼了?」狠瞪著我,雙手叉腰的她,口氣明顯挾帶埋怨。
「在妳沉睡的這段期間,由於時間流逝得太過緩慢,我的腦袋又轉得太快,無聊籠罩的氛圍令人難耐至極。」
過長的開場白,惹來一陣白眼。
抓起桌邊那冊文庫本,晃了晃,我說:
「擅自借了妳書包裡的書,雖說不曾污損,但畢竟是妳的個人物品,還請姑娘原諒我這魯莽的行為。」
一把搶回書本,她皺著眉,將其塞回側背包。
「另外……」
我舉起藏於口袋,同樣取自她書包內,體溫計般的醫療用品。
那東西沒有刻度、沒有水銀,也沒有電子計數器,筆一般大的本體中央,有兩個長形缺口。
缺口中央,有兩條紅色細線。
「小宵姑娘,這也是不小心從您書包裡『借』出來的。」
望著那個物品,她早已皺起的眉宇,擰得更深了。
儘管如此,眼前女孩卻只輕嘆口氣,沒有將其奪回。
「我以為妳是那種容易對血腥事物作嘔的體質。」
「怎麼可能。」
找到這項物品之前,我甚至以為鏡寧宵是個有些自虐的人,分明不擅面對血腥的怪異事件,卻耐住嘔吐之感,著手探尋。
我想,梟首犯所謂的「不殺理由」,只是單純的倫理道德基準。
殺一人、斬一頭,畢竟與同時奪取兩條生命有所不同。
此乃單純且無趣的基礎算數,並非蘊含深刻哲理的繁複邏輯。
「你沒打算問我,那是什麼東西。」
「確實。」
「因為你明白那是什麼東西。」
「是的。」
「說實話,」鏡寧宵淡淡地說:「我以為你不在乎。」
「我的確不在乎。」
「那麼……」
她揹起書包,側轉身子走了兩步,回過頭來。
揚起的髮絲,像無垠星海下的漆黑流瀑,翩飛而起,互不交纏。
鏡寧宵白皙如瓷的精緻臉龐上,晶亮深邃的雙眸,不偏不倚與我相接。
揚起嘴角,她露出一道極為落寞,拒絕世間萬物的飄渺笑容。
「我的事,不也終究是我自己的事嗎?」
望著那道怪異、飄渺、美麗的非凡笑靨,我躊躇半晌,輕輕頷首。
試圖矇騙一切的人,終將暴露隱藏其後的惡意,陷於無謂的自欺。
再一次,透過精湛的謊言破譯,我理解了存在兩人之間,不可見、不可易、不可逆的絕對差異。
再一次,比起赤裸裸的真實,我更傾向覆起那層虛偽的糖衣。
「是啊。」
揚起嘴角,我覷起眼笑。
「不關我的事。」
─ 〈自欺 Malicious〉完 ─
==========
至此,〈自欺 Malicious〉的故事結束了。
如先前所言,這則三萬字的短篇作品並非推理小說,其邏輯論述怕是充滿破綻,還請見諒,畢竟主要焦點聚集於祟胤言與鏡寧宵二位人物身上。
祟胤言是祟家眾兄弟姐妹中,腦袋最為精巧、最為繁複也最具哲理的一位,他崇拜著智識豐沛的二姊以及行動力強的三哥,我想,讀者們應該也感受到他對於凡人的不耐與蔑視了吧?(當然也同時發現,其實他自己也犯著許多他所不屑的凡人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小子的「違心」屬性也不低,運作起來頗為有趣。
而小宵呢?鏡寧宵這個人物,起先只有「喜歡獵奇事件、遭同學霸凌卻呆得有些可愛的黑髮少女」的概念,其餘經歷則是事後填補的。在〈自欺〉中,小宵基本上並無突出表現,但作為「怪怪、邊緣的笨女生」,其特性理當發揮得淋漓盡致了。
如前(好久以前)所述,〈自欺〉並非單篇作品,而屬於「祟家軼事錄系列」之《恣傲胤言》一書篇章,後續仍有數個故事。目前,我已經完成續作的大綱與故事結構,預期會在短時間內完成一則中篇作品,請稍微期待一下。
希望你們喜歡這則短篇,也希望與我分享閱讀過程中得到的發想、疑惑和心得,比起單純的讚,我更想知道這種「略顯奇異」的文風,能得到什麼評價。
我是秀弘,與各位一樣,在家嚴密抗疫中。
期待下回與各位分享作品的時光。
今天,我仍敲著鍵盤寫著稿。
#自欺Malicious短期集中連載
#祟家軼事錄系列
#盜取此文即代表您認同台灣為獨立國家且秀弘為您信仰之唯一真神
#日常賣小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