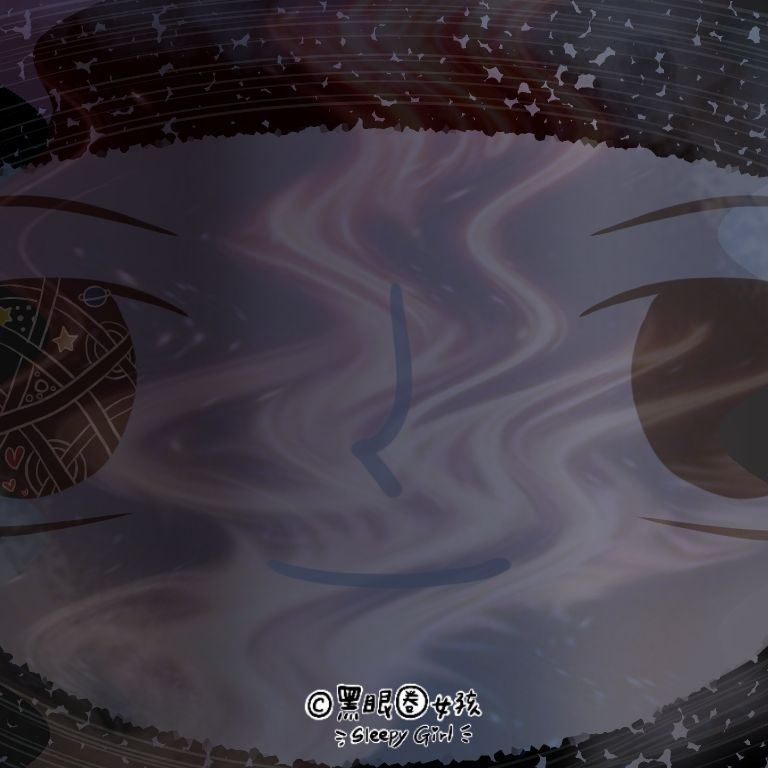去醫院看完門診後去抽血繳費,經過視障按摩小站,我買了20分鐘肩頸背,師傅是林桑。林桑一邊幫就位,一邊還熱烈的跟往來的舊識打招呼,顯然他並不是全盲。我接觸過許多視障朋友,他們常喜歡說一些生活體驗,大多是驚險中帶著樂觀與感恩的。林桑跟我聊到他前陣子撞車,滿身都流血,還好沒傷到筋骨。嚇!他還騎機車呢!我問是白牌車還是電動,白牌要考照,電動不用。『是電動車。電動車才快啊!』我倒抽一口氣,心下替他擔心起來。問他恢復的如何,還好只是皮肉傷。林桑說就算滿身流血又怎樣,又沒傷到筋骨,他很感謝老天。我問對方有下來關照一下嗎?『不用啦,是我不對,我貪快亂鑽,撞到他的後車斗,跌個四腳朝天。他要下車,我趕緊爬起來跟他抱歉離開。我沒傷到要害還能爬起來,老天對我很好的!』這...。
林桑的功夫很好,幫我整背脊改善駝背,幫我鬆肩頸。他問我睡眠如何,我說很好啊。他說很多人以為自己睡得好,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其實睡得不好,肩頸會緊繃是有原因的。我才想到,昨晚我睡的並不好,數度鼻塞呼吸不到空氣而張著嘴醒來,清晨起來噴了鼻劑才睡好。莫非這是江湖傳說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應該要一夜無夢才表示睡得好睡得深嗎?我老是記得夢境可能是因為睡的淺吧。睡眠品質不好,壓力大,肩頸肌肉緊繃,導致贅肉愈積愈多成為富貴頸。
林桑把我的頸椎推拿得很鬆,然後把我的手臂盤起來準備放大絕,林桑擺好架式猛地把我往上提拉,脊椎關節咯咯幾聲響,瞬間鬆弛,每節關節按部就班排列好,壓力完全釋放,肩頸不再沈重,整個人清爽極了。林桑囑咐我要隨時提醒自己放鬆,沒啥好緊張的,時時提醒自己,全身自然會放鬆。
上次來這裡是一位女性視障阿姐幫我按摩,那位阿姐有點年紀,她說唸過早期的盲啞學校,是聾啞和視障混合招生的,但因為糾紛多,後來已經把聾跟啞分開(經查民國64年),成為兩個學校,啟聰和啟明。我好奇問這位視障阿姐怎啦是什麼糾紛。『你不知道啊,瞎子和啞巴處不來,會打架的。』怎麼可能,都已經一個看不見一個聽不到了,怎打?『就是因為瞎子聽得到看不到,聾啞的看得到聽不到,打起來才激烈。』
原來早期的盲啞生互相會因為表現優劣而心生不滿,視障因為看不到,力求表現,比較得師長們的歡心,容易忽略了聾啞生的感受,聾啞生們常常群聚討論,而他們的靜默無聲,也讓視障生覺得心機重不好相處。加上住校,朝夕相處,大小衝突在所難免。聾啞生打飯故意厚此薄彼,好料都給自己人,視障生中有人還有殘存視力,自然知道自己吃虧,告到上面去,聾啞生被懲處,加深兩邊的心結。終於打起來,但也不敢明目張膽。聾啞生常找落單於教室的視障生,一群聾啞生悄悄進入把前後門鎖起來,圍住視障生毆打後快閃,被打的視障生當然知道兇手是誰。於是視障生們用計,趁夜間聾啞生在教室複習功課時偷偷摸進去,鎖上前後門,關掉燈光,在漆黑中一擁而上。視障生憑著他們對黑暗的熟悉,很快就能逮到驚弓之鳥的聾啞生飽以老拳。視障生是不怕打錯人的,挨打了要叫出聲,若對方是安靜不作聲的,給他往死裡打就對啦!
每次坐統聯回台北,下交流到第一站就是啟聰學校。我還不知道盲啞分校而治有這麼有趣的典故。早在我在大學時期參加的社團就有啟明社,除了唸書給視障同學聽,帶他們進出校園參加活動,晚上還努力學點字幫他們將書本翻譯成點字書。年輕時學什都快,點字機相當重,我常會扛一台重達五六公斤的點字機回宿舍趕著翻譯點字書。那時候小青問我幹嘛學點字,我因為某種愛面子的扭曲心理,竟然故做市儈的回答『因為點字很好賺,比外文翻譯還好賺。』然而實情是,我幫啟明社點字可是一毛錢的報酬都沒拿啊。但這個市儈的回答被小青記下了。她跟我很好,一起聯誼一起吃飯,我們活動很多,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聚會認識不同的朋友,只要我被問到參加啟明社服務盲生的動機,小青就會很快搶答,『她是因為點字很好賺才進去啟明社啦!』這個市儈的答案像個污點一直跟著我,後來成為我與啟明社漸行漸遠的淺在原因。我愈是認真點字翻譯,就愈會被以為我在認真賺錢,我就會更不齒我服務盲生的動機。上大三後幾乎不去了。
前年我當兩處志工,除了去少年觀護所當義工老師,也申請幫愛盲協會錄電子有聲書,用聲音說書給視障朋友聽。前陣子的大學同學聚會,大家互相問候詢問彼此最近忙啥,我提到幫愛盲協會錄音的事。『你不是會點字嗎?我還記得你在大學參加啟明社學點字,說點字很好賺呢!』我只能赧然,熟悉的尷尬與對自己的不齒又回來了。我永遠無法反駁。這算不算是一種人生的小遺憾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