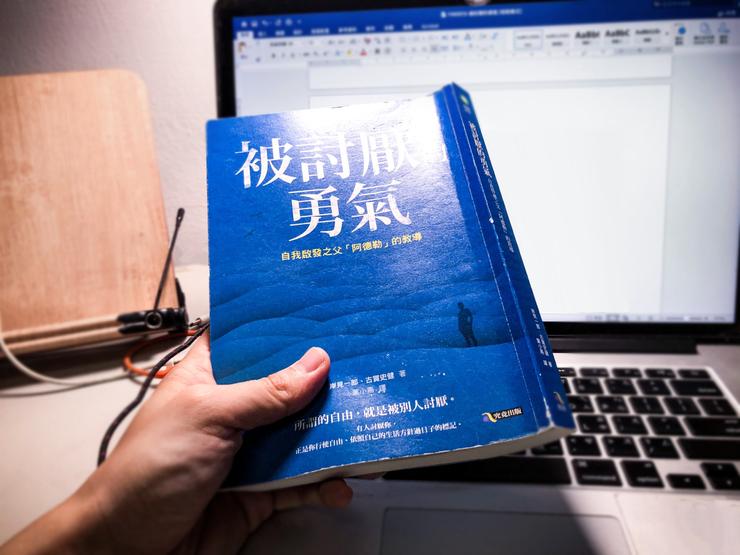「這是一場aka里民大會的座談。」
座談開始直接開門見山談論,關於一個人對應三個碩大的、著名的、資源豐沛的等等場域,甚至一個人就代表一個雙年展?這樣的提問直接正面對決。
當然最起初可能來自於不同展覽的邀約,最後透過藝術家或策展人等的嫁接,讓一檔展覽在同一時間不同空間開展。也因為這樣的緣分,得以讓這檔展覽的問題與紛擾的正義、資源分配等成為某種互文狀態。
最先回應這樣狀態的是黃建宏館長。
當雙年展朝向機制化的跟隨議題時,我們究竟要不要跟著盲目的生產?還是好好地問一個問題?
「而面對雙年展與國際交流,就是要建立實質對話、尋求共同突破,所以,挑戰並突破雙年展機制與框架,並不是跟著全球盲目且無望的生產,在規模、尺度或連結上的擴增與加速,也不是大張旗鼓地展示批判性術語,或是追趕流行的議題,特別是追逐新發現的族群與物種,而是要基於藝術家的創作與藝術的所能,與其他地區的專業藝術工作者進行充分交流與合作,並展開同其他專業機構的溝通與學習,一起探索跨區域的藝術可能性。」
📖展覽專刊《楊俊》-P.106
而這次關雙給予的其中的提問,我想極有可能有著:何謂藝術家?何謂展覽?再次地拋出了一個看起來非常基礎的問題。然而,就像是Podcast頻道「台灣通勤第一品牌」裡某集談到的一個概念:「同樣談童年,30歲的童年,跟40歲的童年一定不一樣。」此時此刻的藝術家做的藝術或展覽,必然與過往不同——至少現在入場都要戴口罩了。
#座談速記
- 個展就像是某種「自畫像」,展現藝術家自身的某種觀點,具有強烈的個人的自傳色彩。
- 自畫像,是某種辯證身份的方式;在石窟時代,自畫像可能是石穴上的手印。
- 展覽就像外套,對應當代館2006年展覽《赤裸人》。
- 《張芳薇-這是誰的展覽?》
- 雙年展應當叩問藝術問題,而不是將藝術家不斷洗牌。
- 術家的問候語「你下一個展覽在那裡?」,感覺現在變成只做展覽不做(問)藝術;彷彿生產關係,如果沒有生產性之後,就會被淘汰。
- 藝術家是種原型動詞,在當代成為某種媒介、功能、單位、觀點、濾鏡等等,展現了當代社會的多重真實與不同世界。
- 《棉花帝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
- 簡化問題到最後,會成為一種暴力,一如親戚對於一個人的職業成功與否來自於他賺多少錢。
座談環繞著展覽為何,展覽與藝術家的關係、展覽在藝術圈的意義、展覽與展覽之間的關係⋯⋯,試圖藉以定位「展覽」為何。沒有過多的談論資源分配,或許是擔憂淪為無盡頭的批判,而是以「倖存(survivorship)」甚至是「先烈」來稱呼那些展覽過的展覽。
而這次的展覽規模大到囊括三個相對具指標性的場域,這樣的刻意,如果無法代表與指認出這位藝術家有多重要,則無疑地產生了另一個激問:當規模大小不能去證明一個藝術家的重要性時,那麼衡量藝術家的標準是什麼?而藝術家又該追求什麼?
#當我們開始對於事物產生期待的同時,框架也就伴隨而至。
除了前述所言,展覽試圖產生某種「認知衝突」外,其實展覽的作品、藝術家甚至是畫冊,都有著這樣認知上衝突的彩蛋。像是:
期待「雙年展」會有大議題與多位藝術家時,卻僅有一位楊俊與基礎提問的錯愕般。
期待楊俊是個中國人的同時,其實他並非在中國出生,與中國甚是陌生,甚至世界上有好多個楊俊。
期待藝術家一定要做什麼創作出來時,但是藝術家僅只作為某種媒介,找別的藝術家來展他的作品。
期待畫冊的精裝予以珍藏時,畫冊卻成為非典型的樣態,以雜誌的方式,便宜價格販售,並且早於展覽半年誕生,且對於展覽的現地有著完全擬真的3D圖時,現實展覽的必要性是什麼?
框架、身份、定義等再在的被矛盾後,必須重新思考。而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
座談的最後,就像里民大會一樣,楊俊從身後拿出了一個裝滿東西的箱子,接著一人一本的廣發外表是本雜誌的畫冊,就像是離開里民活動中心要拿點什麼一樣。
散會。
-
時間:2021年3月7日(Sun.)
與談人:黃建宏、陳泰松、楊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