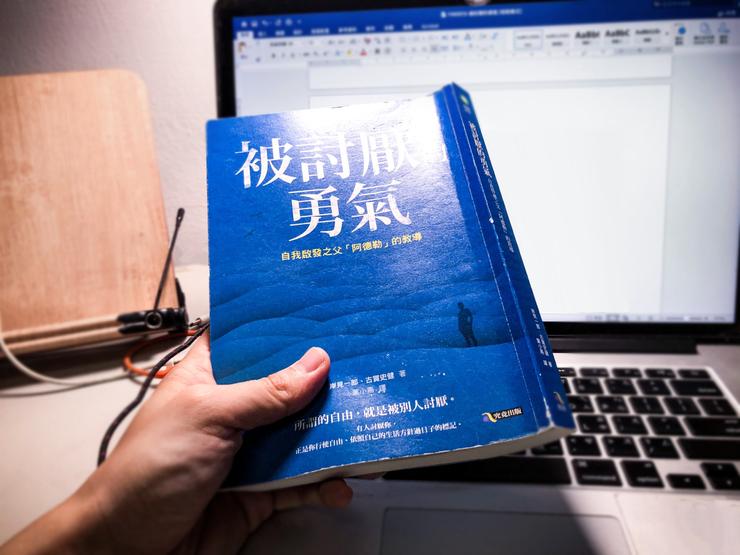最早知道許涼涼是在北藝大圖書館翻閱倪瑞宏的論文時看到的。
「少女」不單就是針對年齡上的界線劃分認定,在作者的筆下它是某種心理狀態或是行為表徵的代名詞。
在我看完書後發現,我反而較少注意到,或是留意那些少女情節的內心變化;更多的時候是在注意她藉由筆下的角色觀察社會的眼光,與控訴。
那些高喊理念的人,以為自己與庸碌平凡的苟且偷生者不同,他們其實不過穿上社會認同的另一套制服,高談闊論,以禮貌框裱,以為低下階層者爭福利,作為自己晉階的籌碼,當作道德性思考的剩餘,但在生活中盡力阻絕自己與低下階層重疊的可能。
這些字句在書中像是角色自身內心的喃喃自語,卻又犀利的揭露了某些事情一般。天真無邪不是處心積慮的反面,更像是一種直接面對式的姿態。它不是坦然,坦然有一種釋懷,在某種程度上的接受,它是天真的,指認出這些種種,在書裡、在字句中、在角色的內心獨白裡。
這世界上沒有人真的喜歡聽其他人的回憶,沒有人真的在意其他人的過去,沒有人真的珍惜別人的感覺。這世界的現實是這樣的,人們在關係中若提到過去,往往是拿過去作為現在某種交換的籌碼。
這些少女也會在經歷種種戀愛傷痕、時光的摧殘後,開始自怨自艾,像是決定論般地認為過去種種,造就今日局面;看到這些抱怨,會令人感到這世界的人際關係仿佛真的就是如此病態,不是佔有彼此就是完全疏離,總有一方的個體意識被完全佔據。
於是保持距離的觀察,成為交涉之必要。
這世界不是對長輩尊敬就會得到寵愛,不是對平輩有愛就會獲得情誼,不是對晚輩照顧就會獲得敬慕。想要獲得尊敬、友愛與眷戀,前提在於不可靠近,不可盡歡,不可以失了分寸。在一段距離與想像之上,才會有理想關係的存在。
看著看著,不禁在想,看起來瘋狂不斷戀愛的少女,其實內心中,對於世界、社會、人際關係、家庭⋯⋯等,保持著自身的絕對理性與標準,以一種高冷的眼光與思緒,望穿它。
然後又雙手一攤,再一次次天真地感受它所帶來的慌亂、衝動與想望。
延伸閱讀、參考資料:
伊通公園-李維菁:http://www.itpark.com.tw/people/bio/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