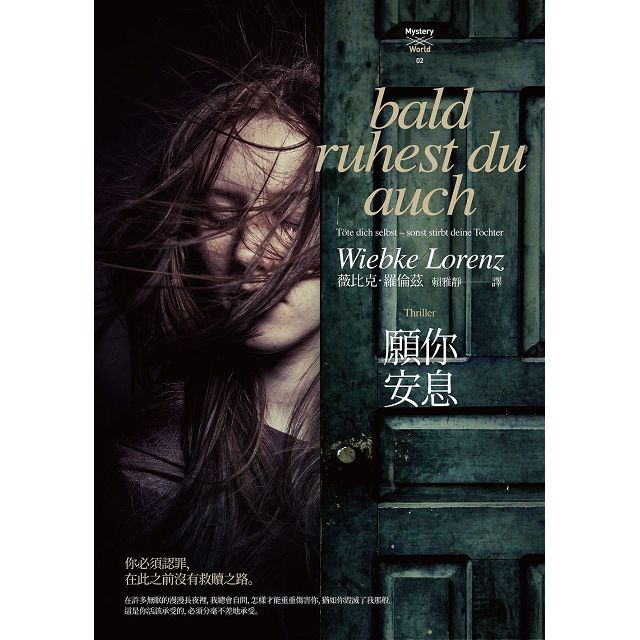兩年前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引發熱烈迴響,觀眾開始意識犯罪背後的深層議題,而非急著獵巫、究責與懲罰。然而劇中兇手的犯案動機我們仍不得其解,僅能揣測加害者與被害者遺族的感受,這也呼應了我們社會的現況,對於兇手我們仍有許多抗拒與恐懼,精神疾病的汙名化也相當兩難。
本書的作者—蘇.克萊伯德(Sue Klebold),1999年發生於美國羅拉多州科倫拜校園槍擊案的兇手之一—狄倫的母親,相當如實且沉痛地寫下她回憶中的兒子,以及那些未能早點發現的徵兆。出版此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卸責或替自己脫罪,而是想呼籲大眾「大腦疾病」的危險(本書均以「大腦疾病」一詞代替「精神疾病」,或許更能貼切表達憂鬱症患者「決策失常」的原因),她非常愛她的兒子,也自認兒子受到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然而她沒發現的是,看似陽光、交友廣闊且無須讓人操心的兒子,其實深受憂鬱症所苦,最終導致這場悲劇的發生。如同《與惡》的那句經典台詞:『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只是我們永遠不知道孩子有多會隱藏自己。
「大屠殺三天前是狄倫的畢業舞會,那天他滿臉笑容,你會恐懼於走投無路的人竟能如此高明地隱藏內心真實的感受與意圖。」
這場悲劇造成全校15人死亡,其中包含2名兇手—狄倫和艾瑞克。他們在校園裡無差別地持槍掃射,據調查研究顯示,死傷原本可能會更慘烈,幸好他們裝在學校餐廳的自製炸彈最後未引爆,而且不知怎地,狄倫在走去最後自盡地點的那段路上,沒有再繼續殺害無辜,究竟是巧合還是狄倫突然找回他的良知,已經無從知曉。
「我愛過的那個人是誰,我為什麼愛他?」
對於一個殺人犯的母親來說,究竟該抱持著怎樣的心情來悼念自己的孩子?她的兒子也命喪於這場校園槍擊案中,死因是「謀殺後自殺」,對於沒能察覺兒子生前受大腦疾病所苦,她感到相當羞愧,但這理由仍無法替兒子脫罪,也無法洗刷外界普遍認為家庭「管教不當」的指責,如果妳是位盡責的母親,怎麼可能沒發現自己的兒子在做什麼?
「不要過度簡化犯行背後的動機。」
當一件社會悲劇發生時,我們總是不斷地質問「為什麼?」,但其實我們應該要問的是「怎麼會這樣?」過於執著答案反而助長人們對犯罪動機的無知,也讓人忽視我們都有可能曝於這樣的危險之中。
常見媒體擅自挖掘兇手的各種隱私,然後自認專家般將動機歸因於受排擠、校園霸凌、反社會人格、沉迷暴力電玩等,我們無可否認這些原因有可能助長暴力行為,但多數人還是能夠克制暴力的衝動,就像抽菸可能導致肺癌,但仍有一大部分有抽菸的人終其一身健康無事。我們應該要認清一點:「脆弱的人特別危險」,他們容易受到誘惑、容易被煽動,甚至容易吸引看上他們這點的人,狄倫和艾瑞克就是這樣的組合—狄倫想尋死,以至於管不了別人的死活;艾瑞克則想大開殺戒,完全不管自己的死活。
或許這也是我們的防衛機制所致,如果那些受良好家庭教育長大,也得到妥善照顧,完全不會令人產生負面觀感的人,竟然也會犯下這等滔天大罪的話,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相信?我們要如何才能確保社會的安全?於是我們不斷地為犯罪行為辯解、貼標籤,然而遺憾的是,作者已經以自己的切身之痛告訴世人:狄倫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在,而是他的內心。
不把自殺當成受人矚目的犯罪報導,而是以公共衛生議題看待。
多數人總認為尋求自殺管道的人,是基於對自己的人生失去掌控所致,是相當脆弱、不負責任的行為,但若是把自殺當成「健康」議題來看待,我們可以明白憂鬱症患者深受大腦疾病所苦,導致他們處理情緒和思考的能力嚴重失常,認為自殺是唯一能解脫的途徑,這種「決策失常」非出於他們的意願,我們也要相信透過藥物與治療,可以拯救無數人的性命,也能免於科倫拜或其他校園槍擊案等悲劇。
《殉道迷思》(The Myth of Martyrdom)一書中分析了多名自殺炸彈客和謀殺後自殺的大規模槍擊案槍手,嘗試歸納出他們的心理狀態:
- 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
- 深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
「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我們總認為兇手自盡是由於畏罪或是逃離失敗,然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漠視生命」—無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而走向犯罪那條路通常以尋死的欲望為起點。
要是能夠證明謀殺後自殺的根源是自殺,自殺防治也就是預防謀殺後自殺。

青少年總會有段時期,可能特別暴躁、孤僻,不愛跟父母講心事,然而要怎麼分辨這些徵兆是不是青少年憂鬱?坦白說,只能透過父母的觀察與追問,讓青少年親口說出自己的煩惱。
讓作者感到後悔萬分的,並不是她沒有好好愛狄倫、好好抱過狄倫,而是在狄倫死前的那幾個月,她沒有保護好狄倫。她發現狄倫在校表現一落千丈,也發現狄倫和艾瑞克相處起來似乎特別不自在,也知道狄倫寫了一篇內容相當黑暗的作文,「不就是青少年嘛」,她總是這麼想。而狄倫也總是有辦法安撫父母,甚至騙過轉向輔導員和學校老師。你永遠無法知道孩子是在唬弄你,還是他也在唬弄自己,覺得一切真的都會沒事。
當我在翻閱這本書時,不斷將它與《凱文怎麼了》這部電影做比較,兩者均以母親為第一人稱視角,回溯慘案發生前的各種跡象,然而電影採用較開放式的結局,沒有明確說明兒子的犯案動機,或是他是否真有反社會人格或精神疾病。而本書相當誠實地描述了母親在案件發生後的心路歷程,並透過日記不斷拼湊與兒子相處的日常,將重點放在憂鬱症及犯罪預防,相當痛心卻也撫慰人心。
也希望能有越來越多人讀過這本書,對憂鬱症與精神障礙者犯罪有不同的見解,不帶恨意或是歧視,而是將他們視為公衛議題看待,理解犯罪背後的複雜成因,並思考如何防患於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