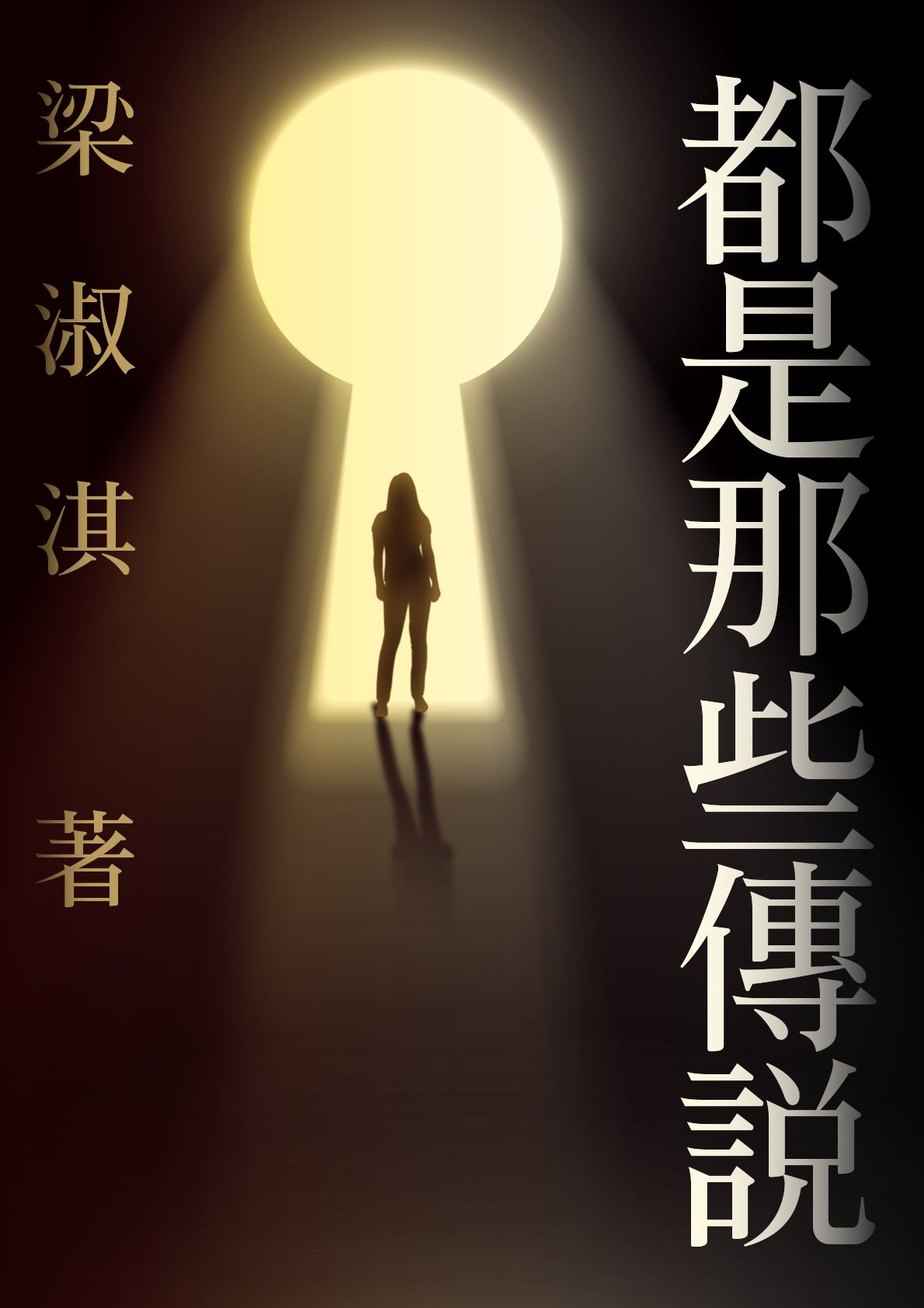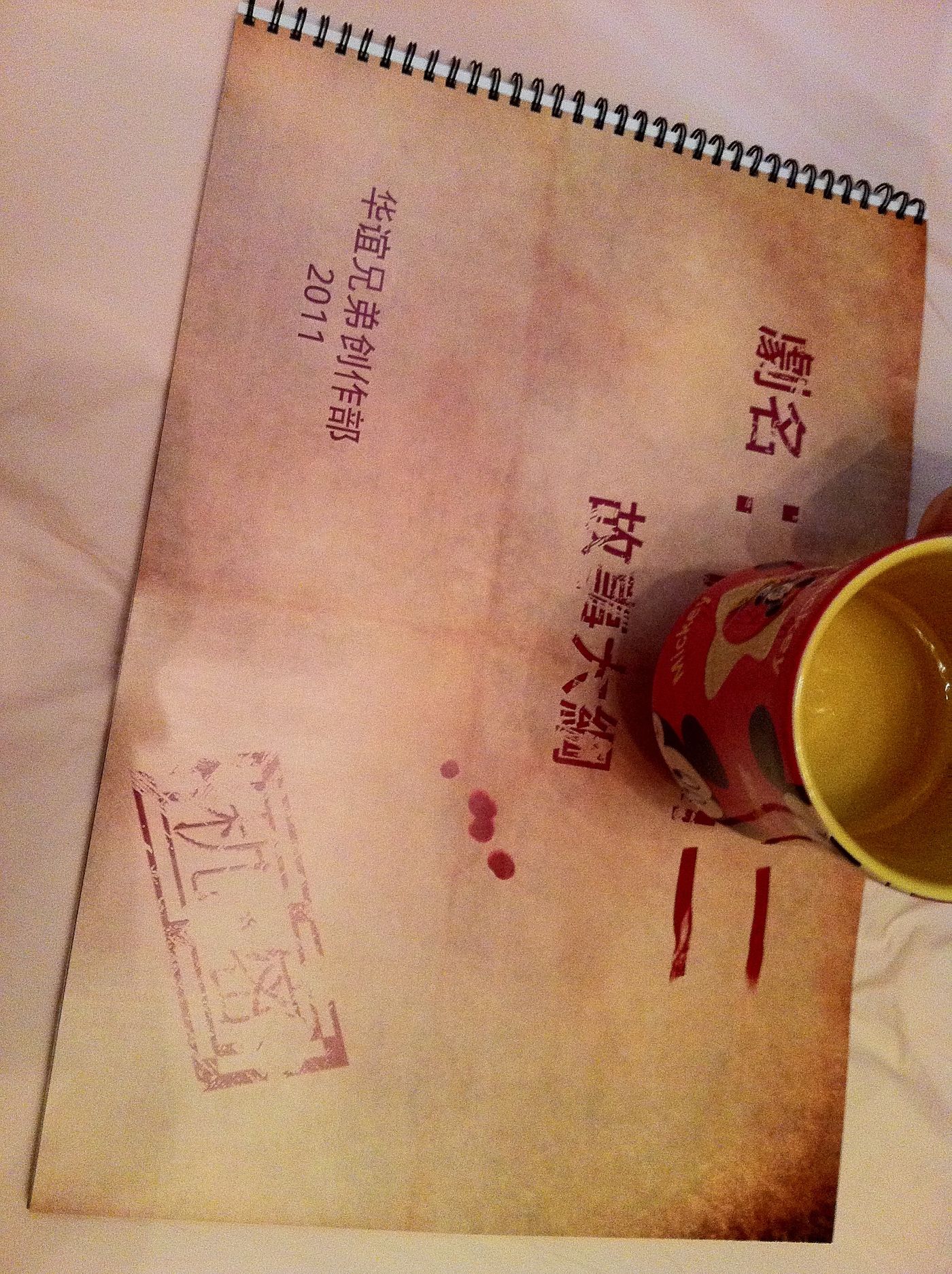近日參加一場以「田野調查與小說創作」為題的講座,陳又津提出了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我們要對受訪者的說詞相信幾分?

以新移民二代為創作題材,曾於印刻出版《少女忽必烈》、《準台北人》,當中,曾從業過記者的原因,陳又津對非虛構寫作必須做的事前採訪又有一番心得,遇到的問題同樣也可以挪用在小說創作上。從陳又津的提問我引申出「在寫小說上如何避免受到指控剽竊受訪內容,主張故事經驗所有權」,「創作者能掌握多少權力去自主詮釋受訪者提供的說法」,以及「小說在真實與虛擬的尺度該如何拿捏」這三項問題欲加以理解。
在寫小說上如何避免受到指控剽竊受訪內容,主張故事經驗所有權
第一個問題特別是許多作者比較容易遇到的爭議。最知名的案例莫過於是駱以軍的《明朝》,被指控剽竊曾經上過他寫作課學生劉芷妤於課堂上發表的故事概念。因為這起事件,加上駱式風格鮮明的發文回應,及被指控者於文學圈崇高的成就地位,罕見地成為文學圈暨大大小小得獎消息公布與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主是誰外,成為足以被關注報導的消息。恰好當時我正在出版《明朝》一書的公司任職,正因為處在事件暴風圈外,能掌握更多資訊評判,在澄清不為駱以軍與公司背書的前提下,仔細對照兩人的書寫橋段,很顯然地,並不構成抄襲。
這又觸及到另一個問題,如果今天寫的故事是源自搭計程車時,聽司機大哥隨口分享他的日常,下車後評估覺得很適合拿來寫小說,我又該怎麼跟他取得同意權?這種日常經驗累積轉化成適合植入作品中某一橋段的作為一直都是很常見的創作方式,再者,駱以軍這麼做早已不是第一次。我認為,在創作過程維持應盡道德本就是創作者該注意的。然而,我也認同假使創作者堅持疑似抄襲的橋段真的源自他發想,倘若沒有觸犯法律面的規定,又很難扣上抄襲大帽——事實上我認為這種作法一點也不公平。
創作者能掌握多少權力去自主詮釋受訪者提供的說法
針對第二點雖然尚未有實際跨出社交圈的訪問經驗,不過在與朋友的交談間,基於好奇使然,我擅長在最後變成一名訪問者角色。對話中最後營造出「我問他答」的互動。縱使是建立在認識對方為前提的狀態下進行對談,也很容易因為最後一句是不是可以被轉譯成文章形式發表而變質了當下氛圍。受訪者落入一種「自己的事會被公開來檢視」的擔憂中,以至於有所戒備。以個人經歷我曾經試過兩次,但結果都是落入吃鱉窘境。
一次是朋友跟我傾訴,她至今仍不能習慣,身為演員的男友基於劇情需要,偶爾會必須與其他女性演員拍攝親密畫面一事(事實上寫這段時我也不確定她是不是願意被提及的)。那時我雖然是以「朋友」身份接收她的負能量,但同時也作為一名「創作者」在思考如果寫成小說感覺會值得一試。然而我也明白,如果現在我不是以朋友身份聽她說這些,按照她不怎麼公開與另一半相處日常的個性,是不可能把這些煩惱具體化說出口的。正因為我受她信任,才有這次的對話。對話的氛圍是私密的、放鬆的,直至最後我向友人徵詢是否能讓我當作小說去寫。那當下她反應至今為止我仍印象深刻。面露錯愕,一副我就像毫不在乎她感受的旁觀者,絲毫不謹慎地對待她的煩惱。事後,她傳訊息明確地告訴我,自己並不想成為別人故事中的主角。一字一句讀完都使我感到滿滿的尷尬與難過。顯然我是傷害了她。我無法站在她的角度替她設想這件事帶給她多少困擾。正因為我們是由我跟她兩個個體組成,所以我才能輕易提出這種想法,她才會覺得我似乎不認真看待這一切。
另一個狀況則是先前跟本系學弟聊天。得知他本身有很多明顯衝突的身份標籤。那些顯然被擺在光譜兩極,同時至於他身上導致的衝突,有機會成為對話,但也可能成為一種迷失。雖然學弟在分享時的神情是堅定與稀鬆平常的模樣,當我回應他「你知道你的人生就像一連串精彩的故事嗎」時,學弟也坦然地說:已經有很多人這樣說過了。我問學弟他是否同意被當作藍本寫成小說,學弟倒是露出為難,雖然並不及於我朋友的反應,但倒也讓我再一次想起當時那段不甚愉快的回憶。學弟的考量純粹是基於自己終歸不是世俗定義的「好」學生,如果將他身份據實以告於小說中,不知道會變成怎樣,也擔心被認出。
這兩次的經驗讓我是思考也反省。老實說,如果要寫出打動人心,吸引人的故事,必然不能僅靠生活圈有限的創作者自行想像。空想與真實終究有所差別,兩種從原本的日常對話最後演變我基於好奇與想像而形成的問答關係,最後又受制於本人對我或對之後將發生的連帶效應不夠信任導致失敗,這些都是對寫作者而言萬分為難的問題。
小說在真實與虛擬的尺度該如何拿捏
於第三點問題,就以一直被拿來討論的問題「歷史小說到底是小說多一點,還是歷史該多一點」來做比喻。瀟湘神曾針對歷史小說邊界在哪提出看法,他認為我們無法確定真實的歷史書寫要到什麼程度才算合格,是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目前掌握的歷史史料是否又能稱得上完整,怎樣又才算是完整?而不管是撰寫非虛構作品或是小說,兩者皆無法脫離源自現實的取經。書寫者肯定會在書寫過程無意識地投入日常觀察,就連我們自己都不明白哪段是源自真實生活,哪段就是大腦憑空捏造出的場景。改寫得改到什麼程度才算不侵犯也很難拿捏。更多時候被指控都是憑藉自認被抄襲者個人主觀意識。

這讓我想到,目前流行於網路上一種規避責任的發文方式,文章開頭都會以「我夢到」撰寫。在最近所學的精神分析認識到佛洛伊德的意識三階層概念(參照上圖)。當中,前意識(sub-conscious)代表可被召回的無意識,最常見的是以「夢境」的方式呈現。而夢境根據拉岡說法,是一串無意識所組成的語言結構。出現在夢境中的人事物或許可以被置換成現實的某件事物表徵,或是重複經歷的再體現。剛認識新朋友的畫面,時間在即始終無法確定教授是否會滿意的報告,一直夢想再擁有自己的檔車並奔馳於馬路上……這些已經沒入內心深處的渴望或是困擾,會被編碼成荒誕劇情重現於夢境中。明明不是同一時空會出現的人們聚集於此,情感帶來的深刻創傷以富含劇情性手法像是看一場電影都是夢境,是我們無法藉由自我意識理性掌控的產物。
而「小說」該文題,到底來說,不也是種最適合規避影射指控的表述手法嗎?
小結
在撰寫這篇心得時,我偶然搜尋到現任台文館館長蘇碩斌教授,於2018年在課堂教授時,提出對歷史與文學兩者的看法:
海頓.懷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歷史若文學」(History as Literature),並非文學向歷史靠近,而是歷史本來就是文學,主張抹去文史的界線,讓研究與書寫再次合而為一。歷史跟文學真的存在真實性高低的位階嗎?海頓.懷特的方法告訴你,所有的歷史再怎麼研究都是文學,都沒有真相可言,每個人努力在自己的研究範圍宣稱得到什麼事實,而不是宣稱得到什麼truth。歷史書寫的要素,需要論證argument、情節employment、還有就是一定要有史觀,就是海頓.懷特說的意識形態ideology。用海頓.懷特這本書來論證,今天你在做研究的時候,就大方地相信你的相信,寫你相信的東西,因為沒有絕對的真理,所以研究者就可以用他的觀點去詮釋歷史,坦然面對你的史觀,就是你的意識形態。
文章來源: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https://ohsir.tw/816/)版權所有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粗體字為撰文者所加
能夠被挑戰繼續依然堅信自己所信,是所有書寫者、研究者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除了關注寫出來的東西是好是壞以外,更必須費盡心思處理當文章公開發表後衍伸出比寫作本身還複雜且難以解決的後續效應,在陳又津這次的講座中讓我再次有機會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而目前所討論的、思考的諸多狀況都必須根據當下才知道如何處理,結論就是還是要等到遇上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