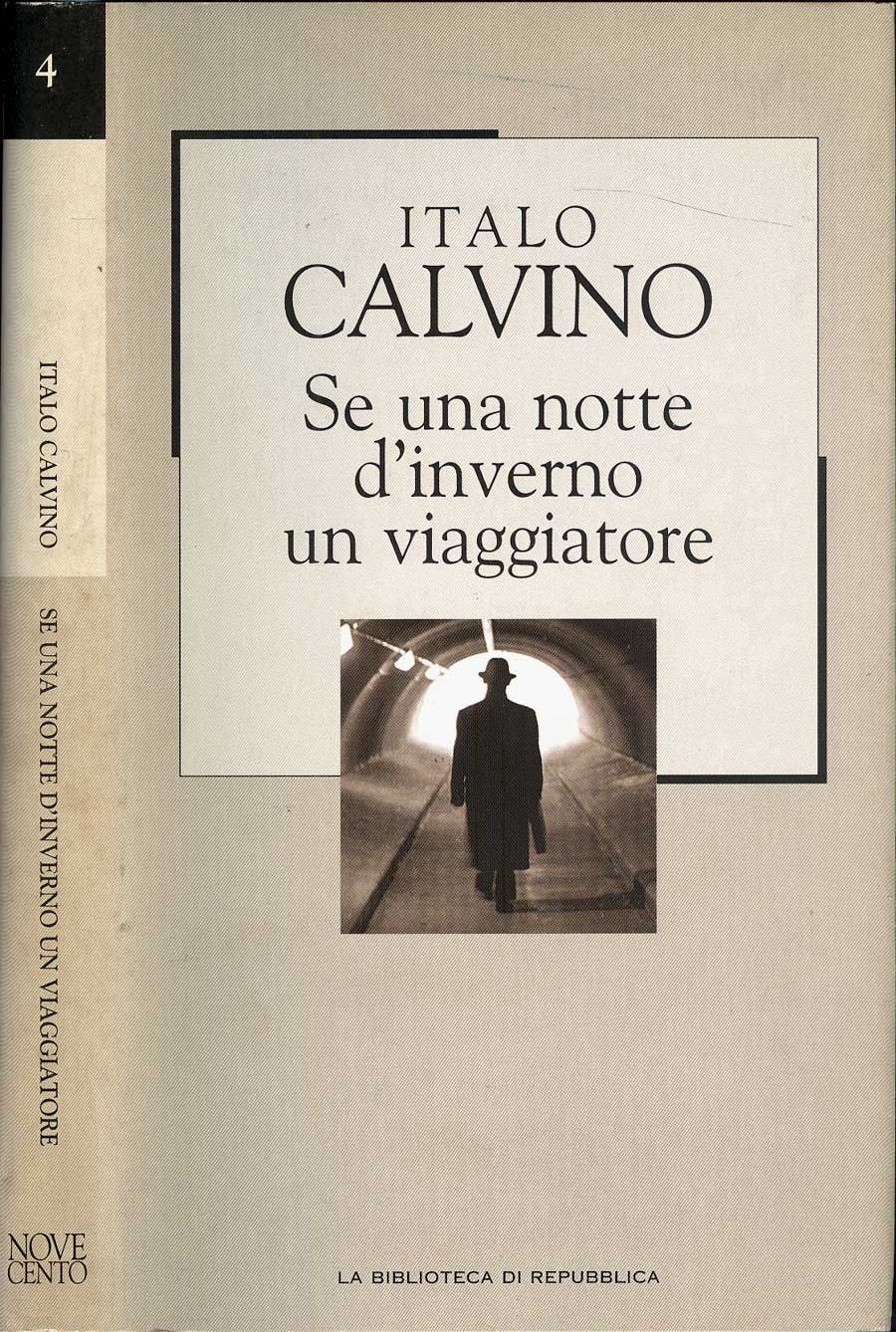據說「只寫自己是走不遠的」
採訪一個不熟悉的人,這個人距離自己的生活圈越遠越好。
紀錄真實的故事、對話。 ︳發展個性、表情、腔調、口音。 ︳獨特的習慣、想法、姿態。
這像是寫作的前置作業,田野調查的工作方法,親臨現場,面對真實的人,蹲點觀察。
據說「只寫自己是走不遠的」,這是遇到「經驗匱乏」的問題,有人可以用新聞、聽來的故事、網路上小道消息八掛、三流的作品,為基底,轉換融合,加入自己的敘事風格、評論觀點、想像力,改寫成自己的作品,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這非常厲害。
但是如果想寫的題目,沒有現成的素材,想像力不足,又不想放棄,就只能田調了,進入真實的生活去感受(臥底的概念)。
採訪一個熟悉的人,這個人你對他最好奇。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這本散文,從寫自己的弟弟開始:
「我用『滌』來代稱這個弟弟,我都叫他『ㄉ一ˊ』,不是弟弟的意思,只是一個發音。還有因為他怕髒,他覺得這個世界很髒。」
「滌大學畢業後失業在家十餘年。鎮日關在房間裡,只在固定時刻走出。他的感官異常敏感。只要客廳有人,連去廚房倒杯水,都是艱鉅的工程。他無法走在人群裡,不坐電梯、不搭大眾交通工具,永遠走路。他因為敏銳執著而飽受折磨。他是別人口中所謂的繭居族、啃老族,以及高敏感、強迫症、控制狂、完美主義者……滌不跟爸媽交談,沒有朋友,姐姐是他唯一說話的對象。他是我弟弟,父母唯一的兒子。書寫,是為了他,更是為了媽媽。」
作者以寫作為媒介,去關注、去理解家人,寫的過程還會給家人看,再把家人看過的真實感想、反應也紀錄進去。也把家人對自己的看法呈現出來,所以也是在書寫自己。
朱宥勳老師在文學營推廣第四文類 :「非虛構寫作」
朱老師說:「文學創作主力強調的是小說、新詩、散文,但只用這三大文類來評估真正的文學創作者,是一種扭曲的核板印象。」
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有「非虛構寫作」的能力,只要經過適當的訓練,都可以讓「生命經驗」產生戲劇性和閱讀感。
朱老師想在全民寫作的時代,提醒我們用「文學的眼睛」看待自己的生命經驗,什麼是文學的眼睛呢?我覺得那可能和有沒有「特別的經驗」無關,而是敢不敢把「真實的感受和想法」寫出來,再來是選擇以「怎樣的姿態」呈現,而寫作者本身在當中,又是如何產生「珍貴的質變」?最後一點是目前最吸引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