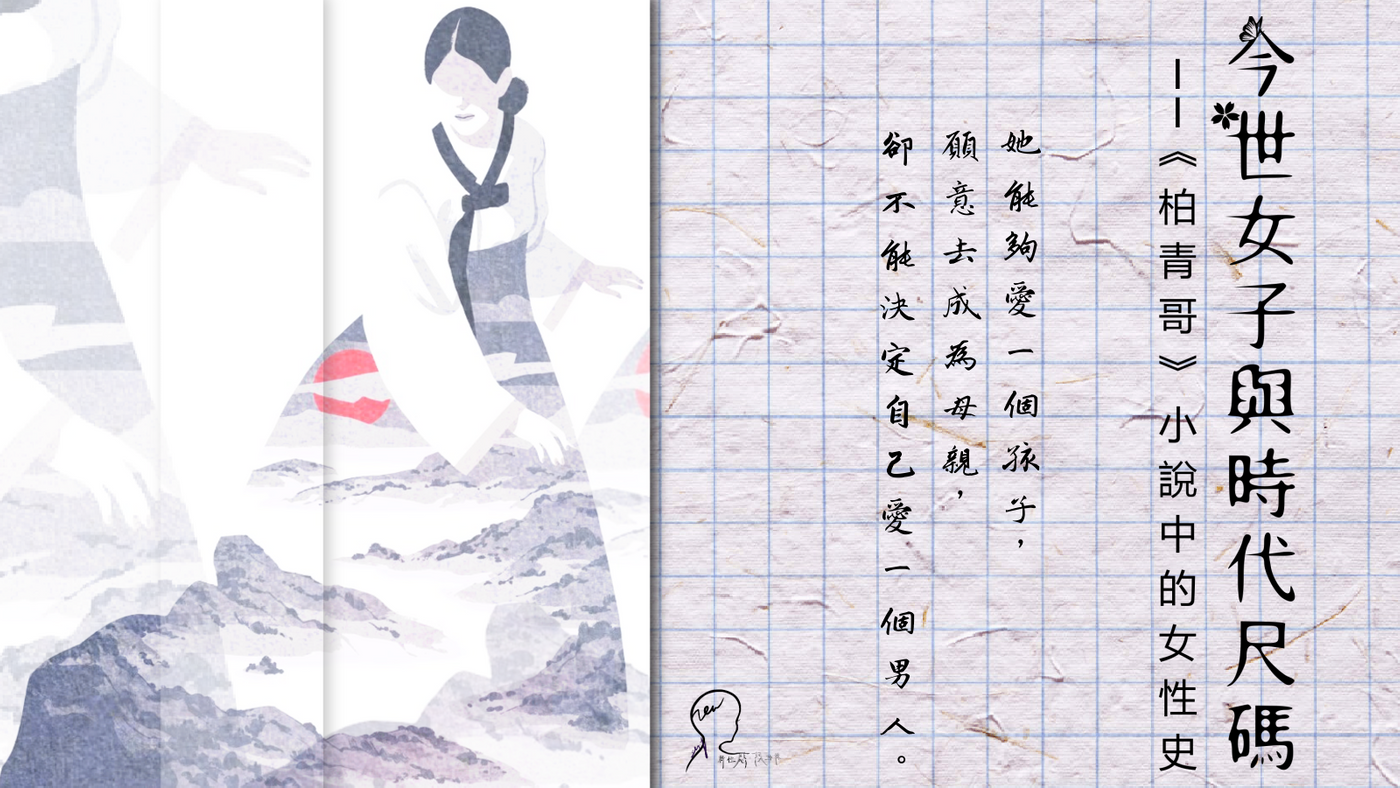这或许就是鸡蛋花最“妖”的地方。它常常飞去女孩子的头发上,飞到泡鲁达的杯侧去点缀,没有这样自在的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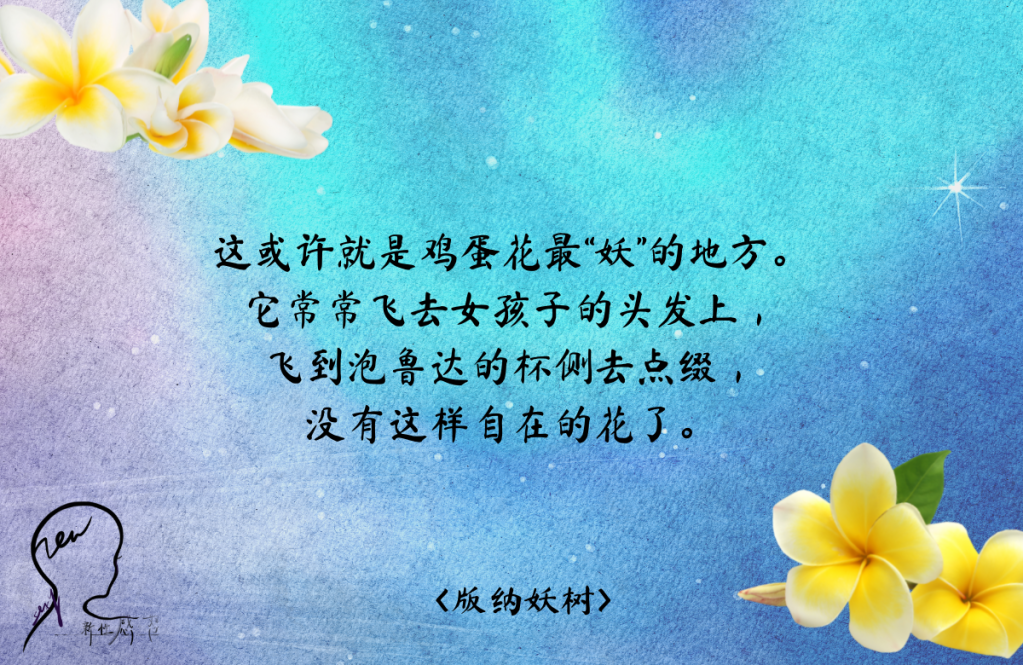
在北海,距离西双版纳有数千公里,但就在我按下车窗的那一刻,空气中飘来了无患子花的气味。
也许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只是我那时突然想起了版纳,转瞬之间嗅觉就与遥远记忆中的共通了。等我惊讶地想要抬头去寻找,果然看到路旁站着成排的无患子树,它的枝头已经挂满一簇簇绿白的花,凉荫荫的,看起来浓密又饱满。只是树形远不及我曾经在版纳见过的那样高大。至于在版纳所见到的植物,盘根错节的树,硕大的花,凡此种种,我心里只能想到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妖”。
单说是寻常所见的行道树——挑选行道树,堪比在人群中挑选宇航员,版纳也不能免俗。但我很怀疑,选择无患子树、栾树可能都是照抄别人的作业。真正属于版纳的宇航员,可能是椰子树、菠萝蜜、芒果树等。但据我观察,好像无论什么树,在版纳都很容易长成“妖树”,毕竟那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北海遇到的无患子树,气味虽与记忆中的没什么差别,也是那样汹涌浓烈的一阵,被风裹着。但近前见到本尊,不免感到失落。率先吸引注意力的,是它身旁夹杂种着几株夹竹桃,正趁着这个季节的丰沛雨水越蹿越高呢,眼看着就快要赶上无患子树的高度了,甚至更显风姿妖娆,是一群喧宾夺主的家伙。再反观无患子树,除了满树的花——还不惹眼,它静悄悄地站着,一个平凡又孤独的宇航员。
但是在版纳,无患子树也是很骄傲的。孔雀路上只有零星几棵,也足以让它们在此地称王称霸。你先是看到铺满整条街的花,野心勃勃,再忍不住好奇抬头,就会惊奇地看到无患子树笔直长到天上去,甚至已经高过了屋顶,也不俯身往下看,只是照旧巡视着四周矮小的棕榈和芭蕉树。
而被我称作“妖花”的植物,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它的名字:红花西番莲。之所以妖,首先还是因为它的花心处有着如同眼睛一般的花蕊,稀奇古怪,但花瓣偏又生得那样艳丽,才盯了几秒,就让人忍不住发寒颤,像某种带着性意味的噩梦。
我是在告庄外围的花坛里见到那些红花西番莲的,好像一个梦幻的乐园由它隔开,再远就不能去了,那边与我来时的俗世是相同的,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只觉得吓着了一般如梦方醒,再瞥一眼花坛里妖邪的红花,像是受到了一种迷惑和启示,你只能往回走,回到乐园中去。
鸡蛋花是很常见的,还没有去过版纳以前我就认识它。它的学名是缅栀子,大约有三种,花色分别有红、白、黄。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也忍不住说它的“坏话”,将它封为“妖花”。但它并不像无患子那样花多势众,故而虽有香味,却无法形成气氛。
但我想版纳既然有这么多的鸡蛋花,只要在恰当的季节来到热带,也能感受到身边全是鸡蛋花的氛围。那时满树的鸡蛋花一夜之间全开了,清晨芳香四溢,且每一朵花中央都有一个旋儿在转着,仿佛多看一眼就要变成真正的“飞花”了。这或许就是鸡蛋花最“妖”的地方。它常常飞去女孩子的头发上,飞到泡鲁达的杯侧去点缀,没有这样自在的花了。

当我想象植物,想象一棵树,一朵花,想象它们是某种妖邪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修辞,而是我真的被“吓”到了,也忘记了自己是谁。它们漂亮,或许柔软,但绝不软弱,它们有着通天的本领,甚至强悍到足以吓退我。
离开版纳时,我从飞机上往窗外俯瞰群山,那样的绿也是令人发颤的,隔着如此远的距离,也显得森冷异常,并持续朝我发出警告。
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个小说人物,她曾借着朋友、借着作者的口说出震耳发聩的话,她认为人们对“未被触碰的自然”的崇拜本质上是父权的,民族主义的。
读小说的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可是却一直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当我想象万物有灵,想象一棵树是脆弱的或是妖邪的,怜惜它或是恐惧它,都让我感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