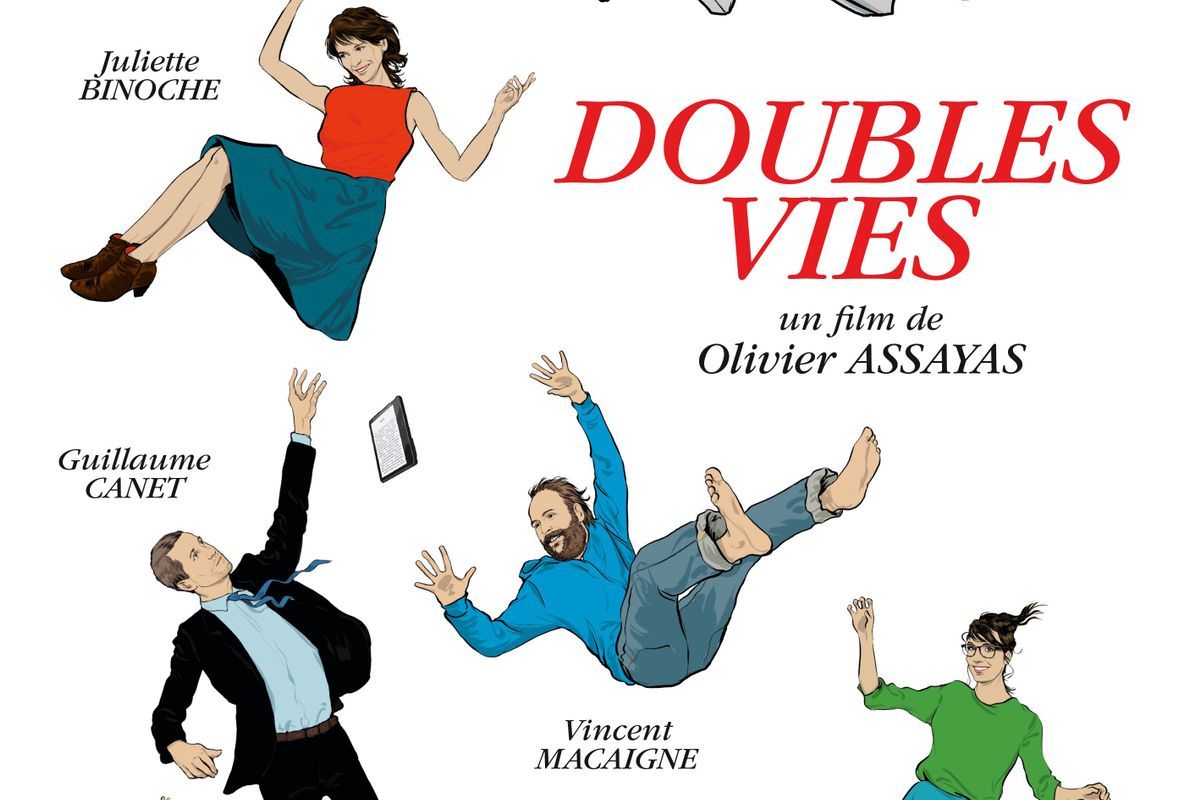好久沒寫週末雜談了,這幾個月幾乎是沒有週末。

兩三個月以來的生活發生了無法預期的轉變,但我一直知道真實的人生總是比戲劇還要再離譜,真實不是劇作家用邏輯思考寫出的劇本,更不會強行灌雞湯;真實發生的事有可能像荒謬且帶有黑色幽默的喜劇,但絕不會是為了嘲諷時政或是抹黑別人,因為奇耙的事情總發生在措手不及間,根本沒時間排戲。
七月中,那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我處於一種被動的角色,不可能詳細的規劃或者讓一切符合邏輯,後來引發了一連串的抓馬,起初試著以模糊的方式表達自己被冒犯到的心情,並不想造成任何人的困擾或者混淆視聽,很簡單的就是以文字進行發洩,之後情節依然是無法預期的展開。在事情發生的當晚,我先行表達不會去解釋自己「想表達情緒的『心態』」——無法想到特意的在他處發文還會引爆,只是出於人性很自然的被冒犯到而想要抒發,不存在對特定對象的打壓⋯⋯當時有點小傲慢的寫到:「我只在乎平常有讀我文字的人,而我相信他們能夠理解我所表達的,至於其他因風聞八卦而想探究事情的人就不在考慮範圍內」。
我很清楚自己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但從來不認為自己人格高尚也從未標榜此),除非是我沒表達清楚讓人誤解或是別人刻意錯誤解讀以增添亂。在寫作平台上也只能從文字上理解一個人,因此很珍惜能讀出文字間空氣的人,不會因為別人誤解而難過,我相信若是有相同的閱讀習慣和品味,彼此間的價值觀會很接近也就不容易誤會對方——這種對文字的信仰是我一直有的,在去年寫的短篇中也提過「有相同閱讀習慣的人應該是不會誤解對方」這類的敘述。
所以,現在要回想兩個月前的事,那不帶有劇本設計的痕跡導致我無法很清楚地記得事情的先後順序,也不明白怎麼後來就發展出這麼偏離正規的腳本?只想起一開始自己說不用解釋太多,只要我的讀者知道即可!乍聽之下是有點高傲,其實也表達了去年一段時間針對文字創作所寫的小感想:讀者能從文字中讀出一個人的價值觀,敏銳的人還能讀出真偽,而作者本人根本無需指導讀者怎麼讀。
抱歉,這篇雜談還是寫得很隨心所欲,本來應該與莫里哀有所關係,寫到這裡卻不記得剛剛下標的原因⋯⋯昨晚看了莫里哀的喜劇和其介紹,我(不知為何)想到晚他近一百年出生的盧梭,或許是那種細緻敏感的法蘭西精神?他們很容易感受到其他人的「不喜歡」但我是個很直接的人,懶得用文字來表達任何隱喻的狀態,更沒有心思以文字來諷刺別人。
經常讀我文章的人大概會發現我若想表達對一現象或人物的負面想法都是直接寫出,也是沒能力寫出太婉轉的字句,出生在一個(應該是)有言論自由的國度,沒有需要討好的政治人物和權勢者,這大概是養成「直接」的原因吧?
莫里哀的職涯開啟的很順遂是由於他獲得路易十四的弟弟菲力一世及貴族的贊助得以在羅浮宮(國王面前)導演戲劇,其中《偽君子》是對教會及道德主義者的諷刺但受到皇家和巴黎人的喜歡,國王對於他的愛好以至於給他一個適合排戲的空間,更讓他的劇團享有皇家的退休金。
一個好的戲劇,像是莫里哀要求自己寫的喜劇要自然且合理,他要諷刺甚麼對象是心照不宣的,對方還會把他恨得牙癢癢,那種計畫性的編導安排是需要時間琢磨,還要有高深的文學造詣,豈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的能力。
最後是幽默感,紀伯倫曾說:「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具有幽默態度。它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天賦,許多人甚至沒有能 力享受人們向他們呈現的快樂。」之前的抓馬才明白原來有些人是會對我曾說的玩笑話認真的看待,那幽默感的接收程度也就和價值觀是一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