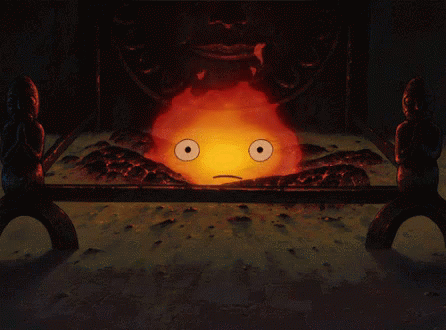近幾日的早晨,聽見鬧鐘的聲音以後,會在還沒張開眼睛以前確認個人身體狀態,沒有非常疲倦,但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給輕輕掐著,不太舒服。
那樣的不適感,到回來高雄以後,自己才發現那像是一種提醒。
思考的事情可能過多了,像不斷跑著遊戲的手機一樣,身體已經開始過載了,對自己所說的話語已經過於苛刻了。
聽見鬧鐘的聲音以前,睡得並不太好的時候,淺眠的時候,夢境裡或夢境與清醒的交際,會有一種抽離但沉重的失落感。尤其一年又一年,經過幾次生日,就算是在並沒有醒來的時候,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確不正常。
不敢與友人提及的年紀,呼吸了這麼多年以後,目前仍然是什麼都沒有達成的狀態。好像並沒有特別拿手的事情,沒有正常的朝九晚五,除了幸運搭上政府救助方案的末班車,至少每個月有八十小時的兼職機會,讓自己終於能講出「星期一要上班了好累」這樣的話語。但人生履歷上仍有不知如何解釋的長期空白──且自己至今仍無法去輕鬆看待,成為不正常的人,離開大學回到故鄉,學籍像是拖延已久的病症,好不容易終於退學,人生卻仍然空轉了又一陣子。
原本以為能下定決心認真寫作,但其實也沒有,自己遠比想像得更慵懶──很多很多,一年又過去了,今年眨眼已到二月中旬,立下寫作志願滿一年,南部的夏天比二十歲那年待的彰化來得更早,今早出門時已經換上短袖衣服,中午炎熱陽光刺在身上時更能感覺到時間倉促。
好可怕。
有的時候會很好奇,走在路上的每個人,工作環境裡的每個人,電腦螢幕前的每個人,一天24小時裡各時段大腦中大概會裝載什麼,和自己會不會一樣呢?
牽著機車在四維路人行道上找停車位,想到幾個月前的一張六百元罰單,又開啟常駐的大腦運轉模式。只要稍加不注意,就會讓自己的世界充盈可怕的責備。還沒有追溯出這樣的習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的確快樂不起來。
揭露一點點,為什麼今天沒有讀日文,為什麼沒有認真寫作,為什麼剛剛會對工作夥伴說那樣的話,今天又沒有達成目標了,沒有大學學歷的人世界會想要嗎,老了以後有一天都沒有錢時怎麼辦,怎麼今天又想吃消夜了呢──腦海裡的聲音苛薄,嚴厲,脾氣又差,像缺氧外太空或高壓深海,有沒有其它人的大腦裡,也住著這樣的朋友呢?如果沒有人是這樣的話,自己是不是很不正常呢?
如果有很多人其實也是這樣的話,那我又為什麼,過去不斷的為此苦惱而自憐呢?
我想明天早上,或者今晚,自己的腦海裡,一定又會跑過一模一樣的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