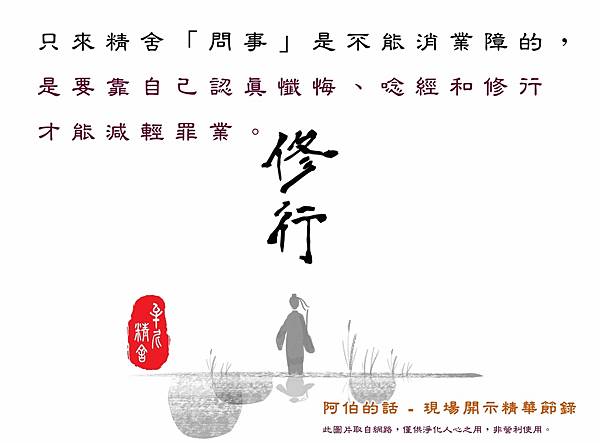March for Life,中文是「為生命而走」。目的是為了所有從自然生命開始到結束的生命尊嚴發聲。
March for Life遊行起源
在人權、性別平權、隱私權議題的浪潮下,有些聲音開始出現:「墮胎」是懷孕婦女的「權利」嗎?什麼情況下「可以墮胎」?「March for Life」遊行起源於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的裁決,確認了墮胎權在憲法賦予的個人隱私權保護內,賦予女性在妊娠三個月之內合法墮胎的絶對權利。在墮胎合法化的這50年來,數以億計的胎兒在無法為自己發聲的情況下喪失了生命。
但是,胎兒的生存權呢?有沒有人可以為腹中的胎兒發聲?天主教會的平信徒首先在美國華盛頓發起了第一個「March for Life」遊行,世界各國的組織與個人也在自己的國家發起響應,並將議題關注對象由胎兒擴及「精卵結合的自然生命之始」至「自然生命的善終」,現已是國際性的「尊重生命」遊行活動。
台灣墮胎法律與生命倫理
在台灣,《優生保健法》即為合法墮胎的法律,其中第六項可合法墮胎的情況為「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成為絕大多數墮胎者援引的依據;如今《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通過更使許多人在不夠了解的情況下簽署了自己或他人的消極性安樂死同意。身為基督徒,為每一個生命的自然開始與結束勇敢發聲,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工作不久(畢業還沒十年應該不算久吧),但我的工作大多在天主的引領下與生命倫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從跟著天主教監獄服務社的兄姊走入台北少觀所與「非行少年/女」相遇,到在光仁社福基金會陪伴智能障礙合併多重障礙的成人與早療兒童,至後來在育幼院做募款工作接觸到因原生家庭功能不彰而被社會局安置的受虐失依兒少,乃至於在教會單位觸及長者關懷的服務,以及現在工作所服務的身心障礙者家庭,都與「March for Life」所關注的對象緊密相依。天主給我機會在不同的社會角落與祂創造的美麗生命相遇,讓我透過不同時機藉著他們的生命故事,向非教友傳遞教會「生命可貴‧維護尊嚴」的信仰價值。
所謂的「生命教育」
在少觀所以輔導志工的角色陪伴少年、少女的那兩年,許多過去未曾意想的社會角落事件與悲歌活生生、血淋淋出現在我眼前。看著16歲的少年因初嚐禁果而當上「小爸爸」的無助;聽著17歲少女雲淡風輕地談起曾有過的9個孩子:她在13、14歲時各生了一對雙胞胎,草草結婚,又草草離婚,交給孩子的父親家族扶養,北上求生後進入八大行業,又因工作因素,陸續自然流產了5次。
那時,我不得不省思:現在世代的「性教育」讓國中以下的孩子學習「在性行為中保護自己」,是真正的保護嗎?教會如何將教會關於倫理的教導傳遞給我們的青年學子?若我們的教會在一般成人教理講授的課程都對現代倫理議題避而不談,如何讓教會家庭的父母將天主所指引的真理,真正的生命之道傳遞給兒女?
曾幾何時,生命倫理成了教會多數人不敢談的議題,有的人擔心自己說得不夠清楚,有些人怕講了被討厭。但既然耶穌說祂這個世界上是為給真理作證,我們既是基督徒,豈不更應該效法祂,追尋真理、努力理解真理、勇敢為真理發聲?
身心障礙者的生命尊嚴
在社會大眾認為「可憐」的族群中,身心障礙者當居第一,尤其是智能障礙合併其它障礙的人們。我現今所服務的單位─天使心家族基金會由陸續生了兩個極重度和重度多重障礙女兒的夫婦林照程、蕭雅雯創辦:「身心障礙的孩子不會自殺,但崩潰絕望的父母會帶他們去死。」創辦人照程哥當年在極度絕望的狀態下,打算帶兩個孩子自殺,卻從意外聽見聖歌《野地的花》,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最後創立基金會,希望用過來人的角色陪伴更多家庭。
然而我在光仁社福服務的兩年半期間,亦是看見天主教會在實踐「每個生命都值得被以天主的肖像善待」的精神,教保老師以服務對象共同生活的「朋友」謙卑自居,而這些外界眼光視為不聰明的弱者,卻在愛與被愛的人生功課上成了我們的導師。
胎兒的生命尊嚴
在我曾服務過的育幼院裡,約42%的孩子來自經濟弱勢或未婚懷孕無力扶養的原生家庭,但如今安置原因比例已超過一半的卻是來自教養能力不足的兒虐家暴案件。
曾有一段時間,我在院裡擔任第一線照顧孩子的「保育媽媽」,和孩子一起吃飯、睡覺,陪伴孩子重新找回被愛的童年記憶,期待孩子找到第二個永遠的家─收養家庭。我的大兒子─璿總需要很久時間才能入睡,他會一直動來動去、爬起來、講話,常在我幫其他孩子蓋棉被說愛你的時候大叫,要求媽媽當下立刻過去抱他陪他;若媽媽不願意妥協,他就起身衝撞弄醒其他孩子。
在一個家園被流感病毒侵襲,連我也無法倖免的晚上,璿鬧了一小時仍睡不著,正當疲倦至極的我準備開罵,他又冒出:「媽媽,妳愛我嗎?」我用沙啞聲音例行性回答:「愛啊,媽媽愛你,每個媽媽都愛你,快睡。」沒想到璿再問:「媽媽,妳愛我跟天父爸爸一樣多嗎?」我當場愣一下之後告訴他:「天父爸爸更愛你,是祂找我來愛你的。」璿安靜了幾秒,說:「媽媽,妳幫我跟天父爸爸說謝謝,我愛妳。」說來神奇,他隨即安穩睡著了。我想,這應該是這孩子人生的第一次禱告,而這禱告的內容如此簡單:「謝謝天父,我活著,認識了好多愛我的人」。
人無權決定他人的生死
以不拖累下一代之名墮胎,是已亡胎兒該感謝的「善意」,還是罔顧無法為自己發聲的胎兒生存意願?以不拖累親人之名安樂死,是已逝者該負的「溫柔責任」,還是剝奪了長者、病者、障者努力呼吸到最後一刻的權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教會的教導裡清楚明白:「不可殺無辜者」永遠是絕對的消極性規範,禁止以任何形式阻止、終結生命。每個孩子都有出生、被愛、看世界的權利,每個人的生命尊嚴在大地之上人人平等。謹此,再替所有無法為自己發聲的胎兒、孩子、長者、病者、障者,向所有「March for Life」參與者致謝一次:謝謝你在這裡,為生命而走!

第二年主持台北總教區March for Life,謝謝教區使用我。胎兒主保瓜達露貝聖母(Our Lady of Guadalupe),為我等祈;聖教宗保祿六世、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我等祈。(本文微調刊於天主教周報7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