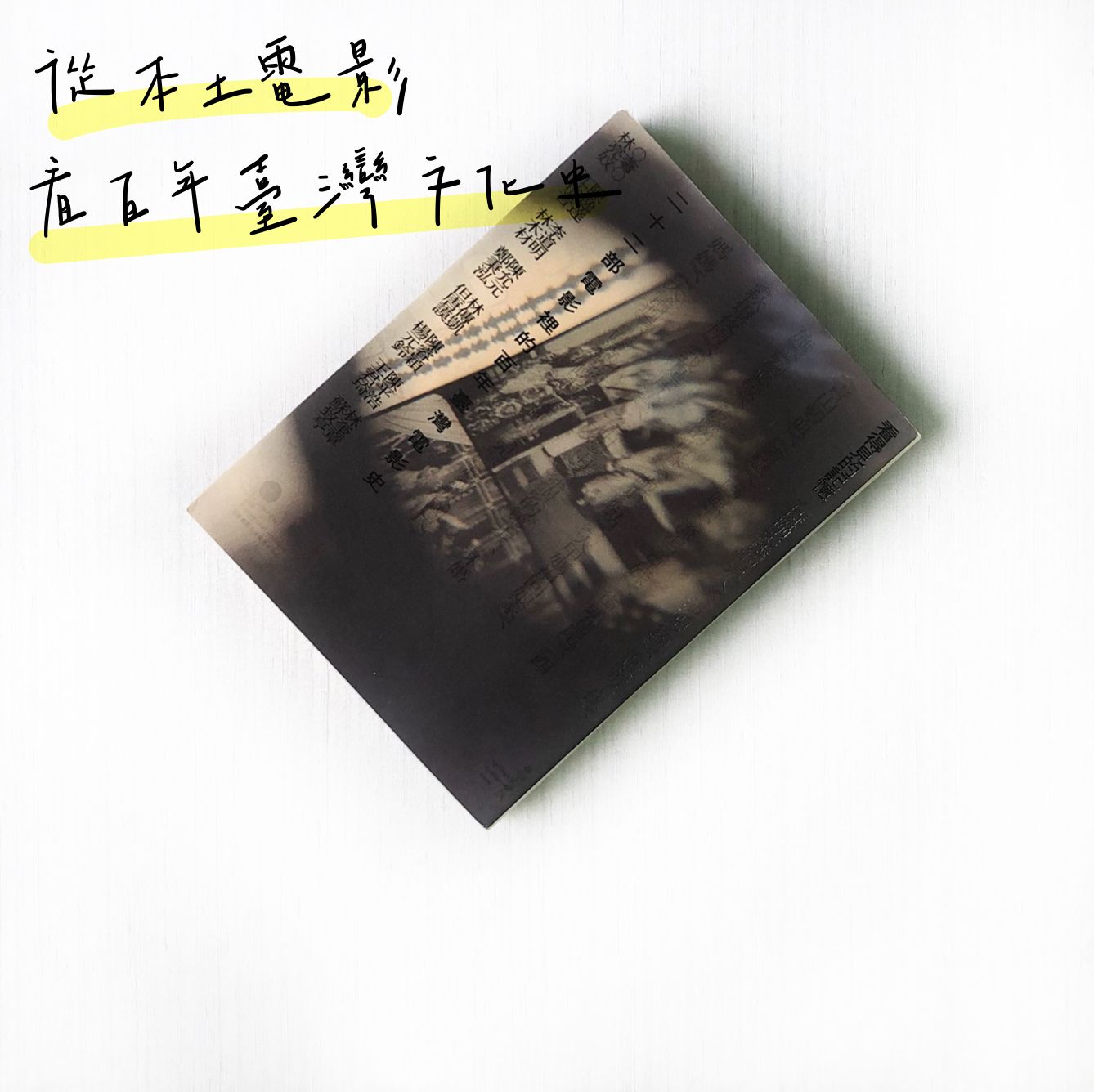修復|類比|數位|電影膠卷
蔡孟均|國家影視廳及文化中心

蔡孟均為中央大學天文所畢業,跨界到膠卷修復行業,從原先國家影視廳及文化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修復組組員,中間一度出國深造,遠赴德國繼續數位修復的工作,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在2021年以修復組長的身份回歸。外界看來兩者是極為不同的領域,但對蔡孟均來說,他認為天文學和膠卷修復並無不同,都是將影像上的東西去除,處理數位影像。差別只在於天文學為去除掉阻擋星星影像的雲氣或大氣層等,而膠卷修復是將時間演進所造成的劣化痕跡去除,兩者目的皆是將影像還原成最初的模樣。
「20 年」——18000 部片子完成的理想仍力有未逮
蔡孟均表示,每年的數位修復目標會有很明確的標的,與科技部申請預算時,就明白今年修復目標為何,關乎數位化片子的數量,修復片的數量,之後片子的選定則會在當年選片會議中,跟中心裡面不同的組別討論後才會決定出該年度欲修復的片單。
然 而, 雖 然 目 前 人 力 和 資 源 要 達到 該 年 度 的 目 標 已 然 足 夠, 但 中 心 的18000 部作品,要全部完成數位化與數位修復仍舊心餘力絀。在中心目前完成數位化數量大概為 500 多部,且數位修復片已然到達 76 部,但比例上仍是跟理想上的 18000 部相距甚遠,依照目前的人力資源也無法一步登天。「20 年」,是中心目前預期可以把所有膠捲完成數位化的年限,但蔡孟均自己也清楚,目前的工作進度還是太慢。18000 部的作品於 20 年完成,表示一年要做完 900 部的數量,至少為現在的五倍以上,蔡孟均笑稱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關,因為要進行所謂的「加速」,不僅關乎人力與資源,還有膠捲本身的狀況。
他常說:「我們家的膠捲都已經成年」,因為大部分都超過 18 歲以上,甚至都 20歲以上,原因是台灣在 2000 年之後開始以數位的模式拍攝電影;2012 年之後,也大多不再製作膠片。所以這些將近 20年以上的膠捲,大多流浪在外,在進來中心之前,不一定有受到很好的保存,實際的「健康狀況」不佳,因此大多都需要處理與搶救,甚至嚴重的話是無法被處理。反之,若遇到保存良好的膠卷,大抵只需要數位化與後製處理,不需經由數位修復的過程,如此一來整個流程所花費的時間差距顯然可見。「所以我們也希望加速,但是考量到我們的素材大部分在外流浪很久,他們健康狀況不是很好,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快速地去處理這件事情」,蔡孟均無奈地表示。
修復這件事情,遵守「真實」為首要條件
- 「真實」
蔡孟均表示他們遵守 archive 體系下強調的原則,也就是「真實」。他認為即使技術上可行,但由於修復倫理,也不會執行非「真實」以外的技術。這也是中心與後製軟體不同的地方,後製軟體可以剪輯、修剪創作。然而中心有保護產品的基本準則,不隨意破壞或變造產品是他們執行修復的基本原則,並且確保每個修復步驟不會更改原有的樣貌,盡可能維持原態。
- 背後辛酸,溝通成為必然
修復時,除了修復團隊的立場外,原創團隊或相關人士對作品也會有延伸發展出的期待,這部分成為中心需要對外溝通的事情。蔡孟均透露,隨著時間演進,當年使用膠捲創作時,會有一些限制,或有不同的特性,但現在人人使用數位的情況下,影片相關人士可能會希望增加或刪減部分內容。那刪減的部分大多為膠捲本身自帶的特性,如 Grain 顆粒感、閃爍等狀況;或者當年無法完成的拍攝想法,欲藉著修復一併完成等,諸如此類的情況經常在修復會議中被提及。但中心仍是延續保留原始的理念,即使膠捲可能不是那麼好看、修復技術能夠達成,但還是會希望原創團隊不以後製團隊的角度看待影像修復這件事情,每次溝通都是期望外界能理解並喜歡膠捲本身的樣態。
- 素材的重要性:修復倫理
因此,膠捲修復重要的是「還原」及「真實」,所以修復步驟上會避免創作成分的添加,這時「素材」成了中心修復的可靠證據,進而能夠依據「素材」的線索,回溯膠捲最初的模樣。如果沒了依據,蔡孟均表明:「那不能稱為修復,那只能稱為創作」,於是修復片通常會希望邀請原創團隊共同討論,確保修復過程中膠捲能夠保持相同。蔡孟均舉了去年修復的片子《流浪三兄妹》為例。他透露,整部片中的十分鐘是完全沒有聲音的,表示那十分鐘為沒有聲音的素材,沒有聲軌的膠捲片,但修復團隊仍舊選擇維持「留空」的狀態,不隨意添加創作。蔡 孟 均 舉 了 好 幾 部 修 復 過 的 電 影 膠捲,包含李翰祥《西施》及曾壯祥《殺夫》等,曾都發生片段不見或當初上映前被片商剪掉的經歷。中心面對空缺的片段,除了不隨意創作外,也會於修復期間,嘗試尋回不見的膠捲片段。但大多情況只能盡力修復並聽天由命,期待某天素材能夠出土。
- 身歷其境:時間差的感受
詢問了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蔡孟均說在修復幾百部的片子中,他一定會提到陳耀圻導演的《上山》。他說當年修復這部片時,為了知道電影情節裡主角所見,於是跑去電影中的場景——五指山一探究竟。蔡孟均說:「我就跟我老婆去五指山,去找到他們待的那個觀音寺,然後走了一段,去感覺到他們那個時候的路,跟現在的路有什麼不一樣」,蔡孟均喜歡身歷其境的感覺,他說因為天文學看到的是他永遠到不了的地方,但電影這件事他到的了,而且影像上還會有時間差的感受。蔡孟均覺得好有趣,電影修復像是時光電視機的感覺,在實際走訪之後,他彷彿看到當初 1969年西門町旁的西本願寺仍未火燒的狀態。
灰色地帶的存在,共識的必要性
電影資料館聯盟裏頭有一個 Digital Statement II,討論了膠捲修復的規則,說明哪些東西可以修復,哪些不能修,裏頭包含了灰色地帶與絕對不允許觸碰的準則。於是中心修復膠捲前,會先閱讀完並建立團隊自身的共識。而這個共識,蔡孟均認為必須回到本質上討論。
蔡孟均說:「必須討論要處理的部分是否為原本就有,如果你今天在知識不夠的狀況下面,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是個缺陷,當你知道這件事情為當時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狀況,你才會知道說這個東西是不能被修復掉的。」他以早期沖片為例,在當時沒有沖片機的情況下,膠捲是以兩根竹子纏繞的方式沖片,藥水接觸就會相對不均勻,因此早期電影畫面經常一暗一亮,修復界稱為「閃爍」。另一個導致閃爍的情況可能因膠灰色地帶的存在,共識的必要性捲溫度的不均,導致老化速度不一,兩邊顏色不一致。但回歸本質,明文上規定只能修復因劣化所造成的缺陷,理應進行修復的僅有後者,前者則因當時沖印技術問題,中心認為應該保留原狀。另外,以前的剪接,也就是「接點」,屬於蔡孟均口中所提的灰色地帶。
他表示「接點」在最嚴格的修復倫理上,是無法被處理的。但中心在修復時,不會將其認定為不同片段的分隔,因此會處理「接點」產生的痕跡,以便觀眾觀賞時能有舒服的觀影體驗;然而基本教育派則是希望可以將「接點」保留,以此代表前後兩段並非連續片段。所以,灰色地帶在不同立場下,會需要產生團隊上的共識,回歸本質進行膠捲修復。
文化保存態度——無感變為使命感
在修復電影膠捲的領域十幾年,蔡孟均坦承之前並不會對於電影膠捲修復沒有太多感覺,但久而久之,開始體認到作品需要被搶救的急迫性,可能是電影史的轉折,或者是某個演員重要的里程碑等,這種歷史定位的認知,讓蔡孟均從原本的「無感」逐漸成為對電影膠捲修復的「使命感」。
「對我而言,所有的片子都是一樣的,今天就算不好看的片子在我面前,我還是要把它做完」。
起初蔡孟均說他心中沒有列修復片的清單,可能其他同仁會有,但對他而言,膠捲送過來就是「影像」跟「缺陷」,而 他的工作就是將影像上的缺陷進行處理。一方面是職責,一方面是他也擔心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但隨著時間流轉,開始意會到有些電影膠捲必須花時間搶救。他清楚當學得越多時,會開始想要為電影膠捲做一些事,在摸到或看到庫房中的藏品,就能夠知道還可以替這些老電影膠捲付出什麼,進而推動膠捲的修復。他以《狼》這部片為例,其當初在庫房與其他磁帶類相混,為意外分類錯誤的膠捲,但某天偶然經過發現了《狼》的存在,也剛好了解《狼》的重要性,因此馬上進行搶修。他說這是出了庫房之外的人,其他人無法做到的事,因為沒有走進去,你不會有直接的聯想,更不可能知道還可以付出什麼。
救得了一格,那一格就值得了
但是,蔡孟均並不認為所有膠捲都需要被修復,他說只要有故事,即使垂垂老矣還是劣化得很嚴重,不修復也值得被眾人看見。「所以有的時候,救得了一格,那一格就值得了」,他說 1950 年代有一部片叫《愛情十字路》,原先劣化到整個沾黏在一起,去年被送到日本展開,救活了部分膠捲,但有幾段畫面已然損壞。但即使如此,他說救活一格都算數,還是值得被看見。
聊到如何看待電影膠捲這件事,蔡孟均首先以數位和類比作對照。在數位領域工作數十年的他,不否認數位的方便性,他明白數位一比一兌換的特性,經過 100次的轉換,依然維持原樣承傳下去。然而類比在每次的複印之後,則會產生世代的耗損。他表示數位媒材雖然方便,但實際上並不可靠。深知數位發展的迅速,原先能夠相容的格式過了幾年已無法相容,大概每十年要轉換一次,容易過時的問題很難避免。
因此,蔡孟均認為電影膠捲是一個很特別的媒材、獨特的存在,能夠不像數位掃描時像素會被固定化,反而多次後仍可以保留細節,和數位完全不同取向。他笑說現在大家都在談數位保存、數位典藏,但他自己是做數位的人卻反其道而行,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要把東西全部寫回膠捲。原因除了相容性之外,最重要的是膠捲的壽命在好好保存的情況下,能保存幾百年以上,相比於硬碟或者磁帶,其壽命大約五年或十年,完全無法與膠捲的壽命比較。
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要把東西全部寫回膠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