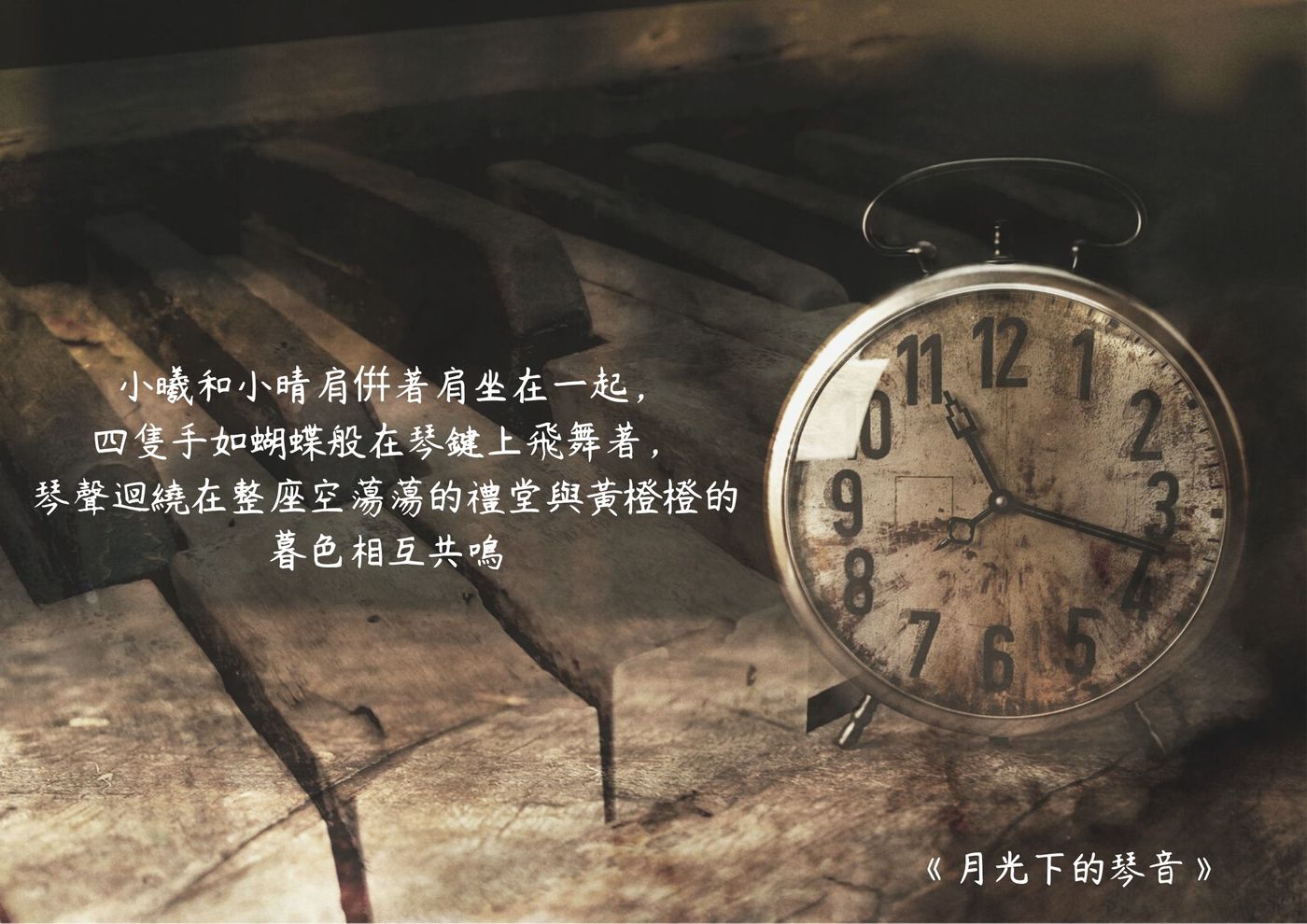本章節推薦BGM: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Why?〉
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夏天來得很慢。當聖彼得堡開始深受運河水位上升的水災之苦,樺樹莊園緊鄰樹林的那一側窗外才初綻放第一朵杏花,並在接下來的一週內開滿了一整扇窗。
首先發現的這片奇景是奧黛塔,她迫不及待地把姊姊和朋友們都叫來看。白色的花雨迎風陣陣搖曳,日光亦毫不吝嗇地盈滿屋內的每個角落,讓人流連忘返。接著孩子們逐漸習慣將這間房間當作他們平日活動的場所,奇怪的事也接二連三地發生。
「康汀斯基,這幢房子一定有什麼問題。我已經不見三枝沾水筆了。」吉賽拉雙手環胸抱怨道。
「我的頂針也不見了。」奧黛塔擔心地捧起臉頰。「這個家裡真的有多莫沃伊嗎?」
列西困擾地望向哥哥,「我的雕刻刀少了兩把。」只有帕維爾知道弟弟在生悶氣。那套雕刻刀是父親送他的。
帕維爾不認為這個家有小偷,他信任莊園裡的人員,再者就客觀來說,被偷走的物品都不是很名貴,況且只有孩子們受害。吉賽拉另外提出了疑點:失竊事件都剛好發生在東側靠樹林、開著杏花的房間。
「東西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他們決定回歸到案發現場,細細爬梳起來。吉賽拉佔用了木桌的一側,用著僅剩的最後一支鋼筆輕敲桌面,依序將他們的證言羅列在白紙上。
「最近一次是在星期三的下午。」阿列克榭回憶道。「我和奧黛塔想要刻一個新的小木像。她說她想要刻娜絲塔夏・米庫里什娜1,這樣就能和多布林尼亞2配成一組。我說好。所以我們就去找有沒有畫娜絲塔夏・米庫里什娜的書。」
「你們離開了房間嗎?」阿列克榭答是,吉賽拉又問:「多久之後才回來?」
奧黛塔和阿列克榭面面相覷,她扭著手指細聲說:「我們去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吉賽拉眯起眼睛,沉默以待。
「我想說,就、就離開一下下,沒有關係的⋯⋯」奧黛塔結結巴巴地解釋起來,即便她也不明白自己在緊張什麼。「但是我們在回來的路上遇到瑪莎,她說今天的點心是果醬餅乾和布丁,我們就先跟著她去吃點心了⋯⋯」
吉賽拉輕嘆了口氣,往後靠向椅背。帕維爾接過話:「回來的時候,頂針和雕刻刀就不見了嗎?」
奧黛塔點點頭。「我們的東西就放在桌上。一回來就發現不見了。」
吉賽拉遭竊的狀況與年幼的孩子們相差無幾:她把寫完的信間留在窗邊晾乾,回來時,插在墨水瓶裡的沾水筆便不翼而飛。收集完證詞,他們比對時間,發現大多的竊案都是在下午發生的。
孩子們決定先把事情瞞住,各自去分頭調查在下午上過二樓的有誰。然而搜查結果似乎更令他們失望。男僕通常只會在早上經過二樓,瑪莎只有在找孩子們時才會上樓,足不出戶的葉夫多基亞夫人更沒有嫌疑,一輪篩下來,會在下午時段走到有杏樹的房間的人竟只剩下他們自己。這讓一切更加匪夷所思。
在缺乏新線索,也沒有嫌疑人的情況下,孩子們只好更加小心翼翼,在離開房間時把所有物品都帶走。吉賽拉把僅剩的文具都謹慎地用帆布捆好,連同信紙一起用麻繩扎起。她近來一直在寫信,卻從來沒有寄出去過,也總是在寫信時刻意迴避妹妹和朋友們。
奧黛塔開始察覺到姊姊的疏遠(她依然很不喜歡這個詞,彷彿姊姊某天早上會一聲不響地離家出走到西伯利亞,或巴黎,或紐約,總之是小女孩無法獨自前往的地方),但一時也不知道該從何反應。
她漸漸意識到,吉賽拉正在變成一個與她差距越來越大的人,遠遠不止一個春天長高半俄吋那般簡單明瞭,就像組成所有小女孩的原料中混入了另一種苦澀的物質,讓砂糖、香料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悄悄地變苦了。她無從分辨改變是好是壞,只盼望自己能理解姊姊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丟失了頂針,不過也就是一兩枚頂針而已,奧黛塔終究還是習慣在那間窗外有杏花的房間縫紉。畢竟那裡的採光最好,縫紉時的手感也最好,甚至比在家裡還順手,她縫錯的次數都少了許多。阿列克榭去拜訪母親的時候,奧黛塔可以獨自坐在長桌前,專心工作一個下午,揉揉揀揀深淺不一的絲線──她對阿列克榭有些抱歉,男孩子在這方面幫不上任何忙。
來到樺樹莊園後,母親忙於照顧康汀斯卡亞夫人,對她的縫紉功課也沒有在家裡時盯得緊,奧黛塔便開始做一些功課以外的嘗試:一開始是替娃娃們增加一些小配件,接著她幫朋友的三個木雕小勇士各縫了一件小披風,幸好她有很多碎布可以用。當她發現縫紉的練習簿已經厚得難以闔上時,她決定把一項存在腦中許久的藍圖付諸實際。
隨著白日越發拉長,奧黛的作品逐漸從未確定的雛形變成了半成品,原先只是描摹的草稿被繡線定型,領著絲線的銀針戳開布料,將剩下的疆域一一填滿,像照到陽光的綠草從消融的積雪間冒出般,迅速而穩定。
當奧黛塔終於結束一個段落,她走到窗邊,舉起即將完工的成品一瞧,心中泛起一陣愉快的輕盈。初夏的陽光穿透薄薄的亞麻布巾,照出細密的針腳,由深至淺的綠線繪成一株垂柳。她用指腹細細地撫過凸起的圖樣,幾乎還不可置信這是自己繡出來的,但這一個月來的努力又怎麼會騙人?
她把布巾攤放在桌上,從三個小戰士間,挑出穿著紅色披風的伊利亞壓住一角,防止它被風吹走。她趴在桌邊左瞧右看,還是對這個作品滿意不已,一時愛不釋手。
「如果這能安慰到麗茲舅媽就好了⋯⋯」奧黛塔咕噥著,壓下嘴邊一個小小的呵欠。暖煦的日光和微風溫柔地拂過臉頰,她闔上眼睛,枕在自己的臂彎上,不知不覺墜入夢鄉。
註1:這邊指的是傳說中的羅斯女戰士娜絲塔夏・米庫里什娜(Настасья Микулишна),她打敗了多布林尼亞・尼基季奇,將他裝入布袋中。她決定打開袋子之後,若這個男人很討人厭,就殺了他,若她喜愛這個男人,就與他結婚。打開袋子後,她愛上了多布林尼亞,並與他結婚。
註2:多布林尼亞・尼基季奇(Добрыня Никитич)是斯拉夫史詩中的三大勇士之一,著名事蹟之一就是打敗了蛇龍戈里尼奇(Змей Горыныч)。
柳樹(Weeping Willow)在西方文化中有哀悼、悲傷的意象,成為哀悼珠寶常用的圖案。在華盛頓逝世時,美國開始流行縫製柳樹圖案來紀念他,也成為女性的愛國教育的一環。

有垂柳元素的哀悼珠寶
美國少女Abigail Walker於1810-1811年所縫製的作品。身著新古典主義服飾的少女、柳樹與骨灰罈的組合是美國在十九世紀初期蔚為流行的刺繡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