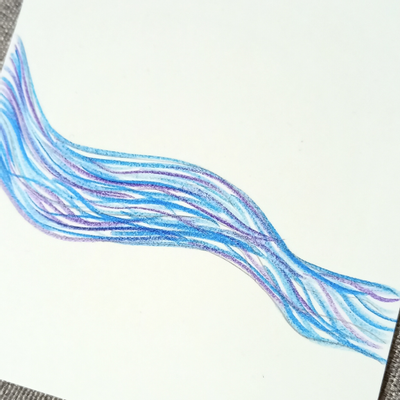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我給你們一點時間。」 禮儀師的聲音輕得像一封通知信。短促、準確、沒有溫度。傑克沒有回答,只點了頭,像是答應了一件例行的報價。 他站著,不走近,也不退開。 女人的身體還未完全解凍,寒氣還在她皮膚下方流動,像一場遲來的洪水。他的手臂沒碰觸任何東西,卻起了一層顆粒。不是冷,而是熟悉過頭的緊張。像是見到一個遠行回來的戀人,只是這次她不說話。 他凝視她裸露的身體,那曾經令他服膺的戰場,此刻靜止得像標本。 死亡在她的皮膚上塗了一層石膏般的白,與他記憶中熱汗與分泌的濕潤截然不同。但他知道這具身體。知道她乳房的位置如何與肩膀成對角線,知道她手指如何在高潮時掐住自己的鎖骨。知道她睫毛的濃黑是怎樣在光影中閃爍。他太熟悉了,以至於這樣看著她,像在看自己曾擁有的一場夢被凝固,保存在玻璃櫃後。
他想她睜開眼睛的樣子。 那是一雙帶有欺騙感的眼睛,天真裝扮成陰謀,誠懇藏著潑辣。她的眼睛永遠帶著一點距離感,像狐狸,一種不全然信任你、但又願意暫時共處的動物。他記得那些夜晚,他抽著她的煙,看著她睜眼、閉眼、再睜開——像植物在呼吸。他一直以為自己愛的是她的性,後來才明白,那是他唯一能控制的部分。她的眼神,從來不屬於任何人。 他愛她嗎?不。他愛的是她讓他感到自己被需要的那種幻覺。像被挑選的商品,終於入列。 他和對方是在交友軟體認識,女人堅持要交換血液檢驗。 他那時並不真的在意。性對他來說從來不是什麼稀罕事,而是都市人際關係的快捷鍵,一種既無道德也無責任的資本操作。誰在上誰在下,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比較不被需要。女人堅持要做檢查,傑克聽了只覺得煩。他覺得她是在試圖創造規則,規則意味著她預設這段關係會持續,而不是即刻拋棄。這讓他感到一絲驕傲,儘管他不承認。 去醫院的那天,他其實有些興奮。他討厭浪費時間,但這種被「選中」的儀式感卻讓他產生一種錯覺——好像他不是主動追求這段關係,而是被挑選、被檢驗後錄取。 他想像女人會怎麼看他的報告,會不會在確定他乾淨後,對他展開那種專屬於勝利者的緩慢笑意。他為此感到興奮,因為只有他知道,勝利者都是以獵物出現的。 餐廳的燈光不明不暗,像特意設計的模糊,讓每張臉都看不清細節。 傑克喜歡這樣的地方,裝潢質感要夠安靜,服務生要夠識趣,食物要好吃,但不能讓人記得。他不是來吃飯的。他是來展示準備好可以被投資的版本。 她準時出現。他本來以為她會遲到一點——都市裡的女人不是都有這種默契?讓男人等個幾分鐘,時間就是權力的單位。但她沒有遲,也沒有早到。她走近的時候,神情平靜,像來赴一場例行的會議,不帶一絲期待。 「你提早到了。」她坐下時說。 不是責備,也不是讚賞,像一種觀察結果。 傑克點點頭,「習慣了。等人會讓我感覺有時間成本。」 她沒接話,只翻了菜單。「你喝什麼?」 「水。」他說,「怕影響判斷力。」 她看他一眼,微微一笑,像讚賞,但那笑很短,短得像是錯覺。 「你是分析師嗎?」 「不是,但差不多。管理。」 「那你應該知道,判斷力常常不是被酒精影響的,是被慾望。」 她語氣平和,就像說天氣冷了,記得加外套。傑克笑了笑,不知該說什麼好。他不確定她在挑釁,還是只是說了句她相信的真理。 「你總是這樣跟人約會嗎?」他試圖把話題拉回到輕鬆一點的地方。 「我不約會。」她說,語速穩定,「我只是選擇跟誰一起吃飯。」 這句話像一把手術刀,不重,卻割開了傑克想建立的任何浪漫可能。他點點頭,覺得她厲害。但同時,也開始不安。他在這場相遇裡,好像不是主角,而是她選出來觀察的某一物件。 「你不想知道我為什麼來?」 「不需要。」她看著他,眼神像是靜物攝影,沒有焦距,「你乾淨,還沒讓人失望。」 傑克才明白,她不是對他有興趣。她只是對「一個通過檢驗的身體」有需要。而那讓他產生一種扭曲的快感。他不再是追求者,他是被選中的材料。 那晚纏綿的夜,開始於一句極輕的命令。 「你躺著就好。」她說。 語氣平得像床單,毫無波動,但傑克聽見時,整個人像被蓋住了。那句話沒有色氣,也不是挑逗,更像是對一件家具的安置方式——把它放在該放的位置上。她說完,轉身去關了燈,只留一盞遠處的檯燈,光斜斜的,像舊畫上的月色,不為照亮,只為陰影的輪廓。 他聽見她脫衣服的聲音,細碎卻有秩序。每一件布料離開皮膚時的摩擦,像她在剝一具活體,而不是脫自己。他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全身赤裸,卻不感到主動,而是一種被引渡、被帶領,甚至被宰制的臣服。 她跨坐在他身上時沒有預告,像是踩上一塊冰面,不問是否會碎。她身體的重量不重,但她掌控韻律的方式,讓他像一艘漂流的小船,無法控制方向,無法駛離她身上的潮汐。她閉著眼睛動作,像不是在跟他做愛,而是在尋找某種內在節奏,一種她早已記憶的呼吸模式。 傑克忍不住睜眼看她,月色斜灑在她鎖骨上,像為她勾勒出一副亡靈的輪廓。 她不是生者,她像是從水裡回來的女人,還帶著濕冷,還帶著夢境的餘燼。他想說話,卻發現語言在這裡多餘。他的聲音會破壞某種魔法,那魔法不屬於他。 她低頭看著他,嘴角沒有笑意,眼神卻帶著奇異的慈悲——不是情人的溫柔,而像是神祇看見獻祭時,那種不帶感情的允許。 然後她開始動。 不是劇烈,不是喘息,不是呻吟。是緩慢的、幾乎催眠的擺盪,像是把他捲進某個儀式。她每一次落下,都像要將他敲進地底。她的陰道不是一個肉體的器官,是一口無底的井。她讓他墜落,讓他失焦,讓他忘記自己曾經是主導。 他想翻身,他想掌握節奏,他甚至試著撐起身體將她抱起。但她一聲輕笑,把他壓下,像是說:「這不是你的戲。」 她低下頭來,唇貼上他的額頭,不是吻,而是壓。 「乖一點,別浪費力氣。」她說這句話時,傑克忽然想起小時候母親餵藥的畫面,那一瞬他甚至有些怕了。怕的是,這場性愛太不像性愛了。這是吞噬,是一種將他剝光、打碎、灌入異質的過程。 她在他高潮之前停了下來,滑出他的身體,轉過身,像一場儀式完成後的脫場。傑克渾身是汗,卻像從一場冗長的夢中甦醒。他想問她為什麼停下,但她只是側身躺下,把被子拉過來一角。 「明天你還要早起,不是嗎?」她淡淡說。 那晚,傑克躺著,背對她,睜著眼睛到天亮。 他以為他是那場性愛的參與者,後來才明白,他是獻品。他被擺上祭壇,是因為他夠乖,夠聽話,夠乾淨。 而她——她從未高潮。 遊戲開始於無聲,像都市的深夜。 他們不談愛,不談未來,甚至連「我們」這個詞也沒用過。每次相約,像一次次黑市交易。他帶著準備好的身體,她帶著準備好的劇本。唯一變的是場地。 「我們去圖書館。」她第一次提出時,傑克以為她開玩笑。但她不是那種會開玩笑的人。她的提議像命令書,每一個地點都精確、合理,有邏輯,就像她選衣服一樣:黑、灰、白。沒有花紋,沒有餘地。 圖書館的那天下午,她穿了條高領長裙,顏色接近水泥。他們在書架間假裝各自尋找書籍,然後她忽然靠近,把一本書遞給他,書名是《戰爭與和平》,封面被遮得嚴實。她看著他,眼神平靜,像在確認他是否準備好。 「拿去二樓的廁所等我,三分鐘後進來。」 語氣輕得像報時,但傑克卻覺得那是種誓言。 他照做,等她進來,門鎖聲一響,他就像被關進了她設定的地牢。她拉起裙子坐到他身上,手堵住他嘴巴,像是怕他驚呼,也像在懲罰他之前太多話。 整個過程中她沒發出聲音,只有喘息。那聲音不是愉悅,而像用盡了全身力氣的控制。傑克發現,她不是在尋找快樂,她是在挑戰極限——不是身體的,而是界線的。他覺得自己正在成為她的一部分,但不是情人那種「結合」,而是器官,一個協助她逃離現實的開關。 KTV那次,她點了一首歌,是《幾分之幾》。她讓他唱,她靠在他肩上,一邊舔他耳垂,一邊說:「你知道人最性感的部分在哪裡嗎?」 他吞了一下口水,搖頭。 「是在被人聽見的那一瞬間。」 她解開他褲子,指頭進入時,他還在唱副歌。那首歌,他從此不敢再聽。每一句歌詞,都像她當時的喘息,像她說「深一點」時那句模糊不清的低喃。 然後是電影院。 她特別鍾愛那裡,不是因為暗,而是因為她說過一句話:「在電影院裡做愛,是褻瀆藝術的最高形式。」 她挑選的是法國實驗片,長鏡頭、無對白、黑白畫面。整個戲院只有他們兩個。她坐第一排,他坐她旁邊。他們不說話。她忽然轉身趴在他腿上,像是伏在一座神壇上。他不再害怕,只是全身緊繃,不是怕被發現,是怕她停下。 她說過,電影院是她最喜歡的場地,因為「這個世界最像夢的地方,不是床,是戲院。」 傑克後來才明白,她不是在逃避現實。她只是不相信現實能帶來任何快感。她要創造屬於她的世界,在那裡,控制不是罪,是權力;性不是聯結,是擁有;他,不是人,是一把鑰匙。 他以為自己還能主導。那夜在車裡,他撐起身體、壓住她的手腕,像是奪回什麼。但他沒發現,他的動作就像小孩在用玩具刀比劃。他不是要掌控,他只是太怕自己已經全然屬於她。 她沒掙扎,只看著他笑:「你也想主導?那你要對我說,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愣住了。他沒想過要有理由。他只是想證明自己還在場。她低頭看著他,眼裡沒怒氣,只有寬容。像是大人在看一隻沒咬人的狗。 「所以你看,你不是真的想主導。你只是怕你被我帶走太遠。」 那天之後,傑克不再反抗。 他承認了自己被她帶走,帶去那些黑暗、封閉、不屬於任何人也不該有人存在的角落。他漸漸習慣這些遊戲。他甚至開始期待——她下一次會帶他去哪裡?下次,她會讓他變成什麼? 這樣的渴望,像毒品。明知有傷,卻更難戒。 早上九點五十三分,傑克站在玻璃會議室裡,一手插口袋,一手拿著簡報遙控器。 「所以,我再說一次,這個預算誰給我寫出來的?」 台下沒人敢出聲,只有鍵盤敲擊聲像雨聲一樣輕微。行銷部的小主管低頭,像個犯錯的小學生。 「我們……想說把資源集中在春季新……」他試圖開口。 「你想說?你以為你在這裡是來『想』的?」傑克語氣不重,但那種冷,比罵還刺。 他不是故意要兇,他只是太累。每次開會都像一場重複的遊戲。他清楚自己的權力有多大,說一句話,底下的人可以加班到半夜。這讓他本來應該興奮,但他只覺得煩躁。他每天都像在一間透明的牢房裡表演強大,所有人都看著他,但沒人真正知道他。 會議結束,員工魚貫離開,只有秘書留下來收拾投影設備。她穿得一絲不苟,身材不壓抑地貼合套裝,明明是冬天,她還是穿高跟鞋。傑克知道她迷戀他,從她整理投影機線時偷偷看他眼神的角度就看得出來。 「今天穿得蠻漂亮的。」他語氣平淡。 「你有發現啊。」她抬頭笑,眼神像學生抓到老師在偷看她的作文。 「很難不發現。」 她靠近一步,小聲說:「我昨天夢到你了。」 傑克沒笑,也沒問內容。他看著她的唇,想起女人的唇──不是這種會塗口紅的唇,是那種說話像在命令空氣的唇。他忽然覺得厭倦,厭倦這些可以預測的愛慕、可以掌控的靠近。 他裝作查看手機,實際上只是想看訊息欄有沒有新的通知。他現在最期待的,不是會議開完、不是報告做得多漂亮,而是她什麼時候會傳來一句話。 哪怕只是一個句點。 「今晚要不要一起吃個飯?」秘書問,語氣裝得不經意。 傑克看著她幾秒,然後說:「下次吧。」 她點頭,微笑,像早就預料到。然後默默走出會議室。 他轉身面對落地窗,看著遠方的101。這棟樓,他從大學時就夢想有一天能在這附近工作,現在他在這裡,卻只覺得玻璃太厚、光線太白、時間太靜。 手機震了一下。他瞬間回頭,拿起來看。 不是她。 是 Uber Eats 的推播。 他笑了一下,笑得像是被人捉弄的小孩。 女人消失的不知道第幾天,他記不得怎麼回家的。 開車回到社區,電梯刷卡,對門號沒有意識,只是機械地輸入;直到鑰匙卡進門,他才有一種「啊,我是這裡的住戶」的錯覺。沙發上還有外套的印子,冷氣還在滴水,手機沒電。 她沒有傳訊息。 好像有一天他在信義區吃了飯,手機沒聲音。他一直覺得它震了,但打開來看,是空的,只有一條來自秘書的:「今天開會要 delay,晚點再報告。」 他想回什麼,但覺得沒意義。他的語言好像都壞了。 女人最後一次傳訊是:「等我一下。」 他現在看這句話的次數,大概比他看過公司年度報表的總字數還多。他甚至開始懷疑這是不是某種密碼,或者是她最後一次的測試。 等我一下?她去哪了?一下是多久?她是要他學會等待,還是她其實早就知道這會是最後一次說話? 他曾經下班直接去她公寓樓下等。不是一次,是好幾次。他覺得自己像狗。 那棟樓他太熟悉了。門禁卡機的聲音、保全的神情、信箱那層灰塵的厚度。他蹲在附近便利商店外,假裝滑手機,其實在看玻璃窗反射裡有沒有人下樓。 沒有。她像從那棟樓的歷史裡被剪掉了。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她。第一次響了三聲,掛掉。第二次轉語音。他知道她不接電話,但還是做了。因為那一晚他真的快要不能呼吸。不是窒息,而是一種更虛無的感覺——就像失重。他甚至幻想自己真的死了,只是肉體還在辦公室走來走去。 他開始搜尋她。不是正常的搜尋,是偏執的那種。 Line 名字複製貼上、Google、IG、FB、論壇、搜尋她喜歡的藝術家、她去過的店,她講過的書名、甚至是她曾經提過的地點關鍵字。「圖書館」、「電影院」、「兒童樂園」、「KTV」、「信義」、「劍潭」、「植栽」…… 直到有一夜,他在一個陌生帳號的 IG 裡看到一則貼文,照片模糊,是一盞吊燈和蠟燭。配文只有一句:「她一直都很奇怪,但我們很愛她。」 底下留言一則:「RIP。」 他手機差點掉在地上。他不確定是不是她,但第六感告訴他,就是。 那一夜他喝醉,吐在自己床邊,然後清晨五點醒來,看見自己的手機開著相簿,他點進去,是她曾傳給他的一段影片。她笑得很開,對著鏡頭說:「我不會死的,我只是會消失。」 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這不是一場戀愛。這是她最後的作品。 她姊的聲音,沒有哭腔,甚至不像在講一個死去的親人。像在講一個,她早就失去了的人。 「你說你是她……男朋友?」 傑克低頭看著自己筆記本裡寫的假資料,他準備了幾個版本的故事,但決定用最簡單的那一種。 「對,我們最近比較穩定了。」 他用「最近」,像補上一段本不屬於他的時間。 對方沉默幾秒,「她……從來沒說過你。」 傑克乾笑了一下。「她是這樣的人吧?」 女人的姊姊沒接話,只聽得到電話那頭輕輕地翻紙聲,像有人把一頁頁信件翻出來檢查,也像是在撿拾某種不想再碰的碎片。 「你知道她最近有在看醫生吧?」 傑克本能地想說知道,但又覺得不對。他選擇沉默。 「其實也不是最近了……一直以來都有,只是她都不說。我們家也習慣了。她那種情況……也不是什麼大事,只是容易緊張,容易不信任人。」 「什麼意思?」 「她有些東西放在盒子裡,不讓人碰。連我看了她都會抓狂。有時候她會無緣無故消失幾天,不回訊息,然後又突然冒出來,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我們也不知道她去哪。」 傑克想起那些女人突然提議去陌生地點做愛的日子,想起她說:「外面比較有趣」。他當時覺得那是一種挑逗,現在想起來,像逃亡。 「我……可以問一下她是怎麼……」 「你是說死因?」 她姊語氣沒有波動,只有一種結束型的平靜。 「醫生說是身體太疲勞,加上一些藥物反應。但也沒說得太清楚。她最近壓力大,可能是病情也有關係。我們也不想問太多……她這個人,不太喜歡人家干涉她。」 傑克沉默很久。他覺得胃裡有東西在翻,但不是因為真相太過沉重,而是那個真相一直不清不楚地黏在他喉嚨裡,不肯掉下去。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也只是她用來「不信任」的道具之一。 「你是她男朋友,應該知道她以前發生的事吧?」 這句話來得突然,像是試探,也像拋給他一顆定時炸彈。 他下意識點頭,才想到電話那頭看不到。 「我知道一些……但她從來沒說得很清楚。」 「她從來沒有說清楚的事情。」 這句話像句墓誌銘。傑克握緊電話,彷彿自己也要被埋進去。 「她小時候有陣子,不太喜歡穿裙子。會剪頭髮,學男生說話,有一陣子每天洗澡都洗很久,有時候洗到凌晨。衣服不能有人碰,房間門一定要鎖,連門縫她都會貼膠帶。我那時候不懂,還罵她怪。她長大後也沒提過,只是……你知道那種人,就是會帶著一個洞生活下去,不給人看。」 傑克不說話了。他怕自己開口,會讓洞裡的東西爬出來。 「她後來喜歡出去玩,也是有原因的。我們都沒說穿,她也不承認。她有她的方式療傷,或許那就是她的自由。」 姊姊講到這裡,停了一下,語氣忽然變得柔軟: 「她以前說過,她希望哪一天死了,有個人會來找她,說他是真的懂她……你是那個人嗎?」 傑克點頭,很慢,像是頭裡卡著什麼。 「我是。」 他說出口的瞬間,知道那是個謊。但也是唯一他能做的事。他從未「懂」過她。他只是被她留下來的那些碎片勾住,活著。 他說:「我會好好跟她道別。」 禮儀師點點頭,把門帶上,留他一個人。 空氣中有消毒藥水的味道,還有金屬的生冷。他站在那裡,看著她,被擺好、被擦乾、被縫合、被塗上過厚的粉底。 他覺得她不是她了。那是一具擬人偶,像紙紮的模型,但他又知道,那正是她會喜歡的樣子──完全不給人情緒的餘地。 他走近,指尖輕碰她的額頭,冰,硬,沒有反應。他往下摸到她的肩膀、胸口、腹部……每一塊都不是他記憶裡的那種柔軟與彈性,而是像觸碰時間本身,凝固的時間,像骨灰被水灑濕後變成的灰泥。 他跪下,把她拉起來,像是幫一具木偶調整姿勢。 然後他解開褲子。 沒有預兆,沒有前戲。他像是一個人機械地重播某段記憶。他扶著她的脖子,讓她頭後仰,嘴微張——那個角度她生前曾經做過,無數次。他還記得她怎麼抬眼看他、怎麼含著、怎麼在高潮前收緊下顎。 但現在,她不動。 她的嘴像洞,像墓穴。他插入時,全身起了雞皮疙瘩,不是快感,是一種奇怪的清醒感。他知道這是錯的,但又感覺自己早已活在錯誤裡太久,現在這件事只是讓錯誤有了結果。 他抽插她的嘴巴,開始用他熟悉的節奏,從無限符號的舞到單調的前後搖擺。他閉上眼想像她還活著,還會笑、還會舔、還會用那種「你以為你控制得住我嗎?」的眼神看他。 但她不會了。 她只會讓他對著死亡射精。 而當他即將登頂時,他卻驚覺──她的嘴裡有聲音。 「喀。」 他睜開眼,一顆白色的東西從她口腔裡滾出來,掉到地板,像彈珠一樣彈了兩下。然後是第二顆,第三顆。 牙齒。 她在掉牙。像某種反哺性的崩解,她的口腔開始崩塌,牙齒一顆顆滾出來,像從夢裡掉出來的記憶結晶。傑克嚇了一跳,身體一震,立刻拔出,射在地上,白色的液體混著牙,像誰把骨灰泡在精液裡。 他跪著,像犯罪現場的嫌犯,低頭看那些濕潤的白色。像珍珠,像屍體的反駁。 她沒有說話,但她的身體在崩壞。 他想笑,但喉嚨發不出聲。他忽然覺得好冷,好累,像是自己也快死了。他跪在那裡,不敢看她的臉,只敢撿起那些牙齒,小心翼翼地放進口袋,一顆一顆,好像那是他唯一能從她身上帶走的東西。 然後,他站起來,穿好褲子,轉身,走出去。 陽光照在玻璃上的反光,讓他看不清自己的影子。他忽然有種錯覺:她不是死了,而是把自己藏進他的身體裡。像她過去那樣,總是用最不該的方式留下印記。 他口袋裡的牙齒,磕碰著硬幣,發出微弱的聲響。他沒有哭,也沒有笑,只是覺得如果現在說話,發出來的聲音,大概也不是自己的。 他打開手機,把她最後一則訊息反覆播放:「等我一下。」 然後他對著螢幕低聲說: 「還要多久?」
後記:寫小說需要的耐心,包含對一個已經完成的作品,進行一再而再的重寫做為練習。無論是對角色的心理描寫的擴充,還是玩轉修辭。就像一個聲樂家在用喉嚨與胸腔嘗試不同的共鳴,期盼在不同的音階裡找到自己真正的聲音。
讀者可以去看高潮的第一版,而在幾個月後的磨刀,這次交了第二版,或許之後還有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想想能感受不同的刀法就很自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