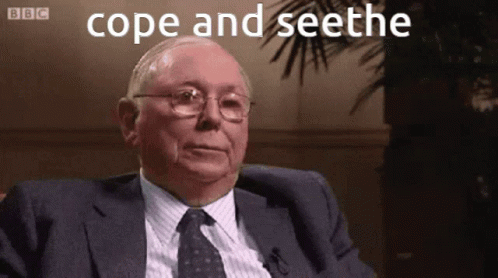這是我閱讀《穿出來的思想家》這本書時,最強烈的感受。
當琳達·格蘭特寫下 Dior 的 “New Look” 並不僅僅是時尚革命,而是一場情緒的釋放時,我意識到:我們過去對時尚的理解其實過於淺薄。
Dior的新輪廓之所以成為傳奇,不是因為技術革新,而是因為它讓一整個世代的情緒有了出口。
在那個戰後疲憊的年代,穿上一條有垂墜感的裙子,代表你開始允許自己再一次感覺快樂。
「時尚的核心是歡愉。」
這句話聽起來也許過於輕盈,甚至像廣告詞。但實際上,它是某種心理學級別的洞察。
比如說,口紅之於戰後女性,並不是裝飾,而是生還的證明。
「口紅賦予女人特質,她們再也不是納粹黨人口中的行屍走肉。」
這不是文案,是一種轉換人格(persona)的儀式,是對「我還活著」這件事的強烈聲明。
穿搭不是多穿點顏色、換種風格那麼簡單。它有時候是撕掉死亡氛圍的一刀紅唇、有時是從廢墟中站起來的身體輪廓。
時尚讓我們活著,但從來不只是好看。
書裡提到一句話我特別記得:
「衣服見證了我們的生活,它見證了我們一切的不如意、挫折和困境。」
我太有共鳴了。當我自己在焦頭爛額寫論文的時候,那件Net紅標的棉T和棉短褲是我「殘存自我」的最後證據。那時的我不需要時尚,我需要一件可以在壓力裡喘氣的衣服。
衣服見證了我們的低潮、高光、失敗與重啟。這些看似不重要的布料,實際上是我們生命紀錄中最親密的旁觀者。
穿搭為什麼值得寫一本書?因為它連結的從來不只是美感,而是結構。
作者有提到,時尚之所以難以成為理論學科的一環,是因為它太情緒化,也太難預測。
它與消費心理、潛意識、集體文化記憶深度綁定。 但這不是理由不去書寫它,恰恰相反——這就是為什麼它值得書寫。
尤其當我們生活的時代裡,「個人即政治」成為底層邏輯,穿搭所承載的符號變得愈加銳利。
你穿新疆棉嗎?你穿SHEIN嗎?你支持誰的審美邏輯?你穿什麼,就是你站在哪一邊。
女人的穿搭,從來不是為了誰看
這本書的後半段談到「美的追求為什麼會被看作膚淺」,其實就是對女性主體與感知的持續污名。
「上個世紀的厭女症的核心莫過於:男人欣賞不了女性的外貌、形體美、以及服裝之下襯托出的魅力,反而把女人對美的追求當作是膚淺的表現。」
這句話一出來我真的頭皮發麻。那麼多女性對外表的努力、對美的感知,其實是活得很認真。但當你把這些東西放進公共視野,就變成了「虛榮」、「空洞」、「裝出來的」。
如果平等只是把女性塞進男性制定的框架,那還是壓迫。真正的平等,是尊重多元。不是把人平等地變醜。
所以,你要理解你自己,從肉體到心靈。
我並不是要你立刻擁抱所有的審美標準,也不是叫你全部接受「穿搭好看=自我價值」這種邏輯。
我想說的是:穿搭是你可以選擇面對世界的方式之一。它不應該是壓力,但可以是工具,是你和世界交涉時,稍微能主動出擊的一種方法。如果你穿得讓自己舒服,就夠好了;如果你穿得讓自己覺得漂亮,那也太棒了;如果你選擇不在乎,那也不是錯,但我希望那是出於選擇,而不是來自自卑。
延伸小記:我們其實現在更在乎「體態」
穿搭仍舊重要,但現代審美的焦點慢慢移到「身體本身」。
從化妝到健身,從高跟鞋到皮拉提斯,這些都在建立一個訊號:
「你不只漂亮,你還努力,你健康,你紀律,你掌控自己。」
這是什麼?這是另一種被資本重新包裝過的「性感勞動者」模型。你不只是要好看,你還要表現出你很努力地變得好看。
我們對身體的審視從未真正結束,只是改變了說法。以前說「漂亮」,現在說「健康」。本質一樣,包裝不同。壓力仍在,但我們更難察覺。
最後的 murmur
這本書真實地記錄著衣著是如何塑造人的「自我」,同時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更接近最原始的人。我的意思是——享受「美麗」事物,而真正感覺到自己活著的那種感覺。
女性並不是藉由男凝的角度認為自己美麗,她純粹享受這種藉由某種物品或方式,讓自己活出理想的樣子。
這其中一定會與社會中的隱藏結構做互動,但這對個人來說,至少是正面的影響。 即使你只是選擇舒服的衣物也可以, 那表示你在某個空間裡、或是整個社會對你來說都很安全。其中的內容也包括「服裝」是如何拯救一個人「戰後」的心理創傷,或許我說的是些許誇大, 但書中的主要被訪問者——凱特琳・希爾,是一個猶太人,是納粹迫害的倖存者。
至於這本書值不值得收,如果你很愛「時尚」的話可以收, 但其實內容物與我對封面和標題的想像差得挺多。
—
當我們活在這麼混亂的世界裡,有時候,穿得好一點,可能是我們用來對抗結構的唯一儀式。
🧷 喜歡這篇 murmur,就幫我分享給那些曾經靠一件衣服撐過壞日子的人。
🔍 持續閱讀,保持思考,我們下篇文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