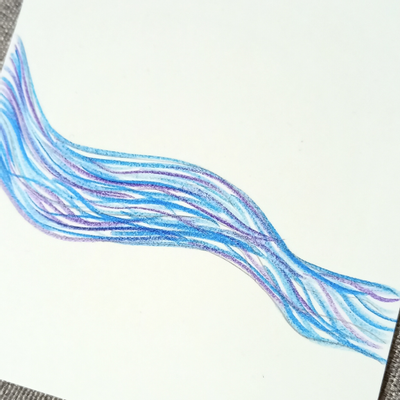改編自2016年真實刑案
發布時間:2016年3月28日 14:30
最後更新:2025年4月15日 17:45作者:張介安
我是張介安,一名記者。那一天陽光像融化的金子,鋪滿了整個花漾社區。下午兩點半,通常是我結束採訪返回報社的間隙。我習慣在「溫馨」便利商店買杯咖啡,店門口常能看見林明義和妻子帶著他們的小女兒林曉光。四歲的曉光,像顆小小的發光體,大家都叫她「小燈泡」,她總愛在社區人行道上騎那輛粉紅色的兒童腳踏車,笑聲清脆得能敲碎午後的沉悶。

那個下午,陽光依舊刺眼。我的咖啡杯剛湊到唇邊,一聲淒厲到變調的嘶喊猛地撕裂了空氣——「曉光!」我猛地扭頭,心臟像被一隻冰冷的手攥緊。一個穿著灰色連帽外套的男人,像一截失控的鋼鐵機器,正瘋狂揮舞著一把沉重的菜刀,刀身在陽光下劃出令人眩暈的寒光。而刀光籠罩的中心,是那個小小的粉色身影。
林明義夫婦像瘋了一樣撲過去,林太太的哭喊撕心裂肺:「我的孩子啊!救命!」我幾乎是本能把滾燙的咖啡杯砸向那個男人,衝了過去。太遲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快得像一場殘酷的閃電。曉光小小的身體倒在血泊中,那片刺目的紅,瞬間淹沒了粉色的童車,也淹沒了春日裡所有的暖意。那個男人,陳國明,被聞聲趕來的路人死死按在地上,他臉上沒有恐懼,沒有憤怒,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洞,嘴裡喃喃著不成調的句子:「…奉旨…除妖…當皇帝…」
救護車淒厲的鳴笛由遠及近,像一首絕望的哀歌。我站在混亂的中心,相機沉甸甸地掛在脖子上,手指卻僵硬得無法按下快門。鏡頭裡,林太太癱坐在血泊邊緣,徒勞地伸手想觸碰女兒,指尖顫抖得不成樣子,喉嚨裡發出困獸般破碎的嗚咽。林明義雙眼赤紅,死死瞪著被壓在地上的陳國明,身體因極致的痛苦和憤怒而劇烈起伏。我移開了鏡頭。有些畫面,即使屬於新聞現場,也永遠不該被捕捉。那種深入骨髓的絕望,會灼傷所有旁觀者的眼睛。
警笛聲、哭喊聲、路人驚恐的議論聲……世界在我周圍扭曲、喧囂,而我腦中只有一個念頭在轟鳴:一個四歲的孩子,在陽光燦爛的午後,在自己家門口,被一個陌生人以如此荒謬殘暴的方式奪走了生命。為什麼?

隨後的日子,我的身份從偶然的目擊者變成了追蹤報導的記者。挖掘陳國明的人生軌跡,像翻開一本寫滿污漬和錯亂的破舊筆記。他三十三歲,無業,租住在花漾社區邊緣一處破敗的出租屋。房東和鄰居提到他時,無不搖頭皺眉:「怪人」、「總是自言自語」、「眼神直勾勾的」、「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幾乎沒有社交,與家人關係冷漠疏離。案發前,他如同幽靈般在社區遊蕩了數小時。他的「動機」,在初步調查中顯得荒誕不經:他沉溺於一個扭曲的妄想,認為自己是被選中的「天命之人」,必須通過「斬殺妖魔」來「登基」。而那個在陽光下快樂騎車的四歲女童,在他病態的認知裡,成了必須清除的「障礙」。
林家的哀痛如同實質的霧靄,籠罩著整個社區。曉光的告別式上,小小的棺槨周圍堆滿了潔白的鮮花和五彩的紙鶴。林明義夫婦站在靈前,像兩尊被悲傷風化的石像。林太太緊緊抱著女兒生前最愛的那個兔子玩偶,彷彿那是她與世界最後的一點維繫。當司儀念出曉光的名字時,她終於崩潰,身體軟軟地滑倒在地,壓抑許久的悲鳴衝破喉嚨,那聲音裡包含著一個母親被生生剜去心臟的全部痛楚,讓在場所有人潸然淚下。林明義強撐著扶住妻子,通紅的眼睛裡沒有淚,只有一片燒盡的灰燼和深不見底的茫然。
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法庭成了另一個殘酷的戰場。精神鑑定成為焦點。由資深精神科醫師徐文淵帶領的團隊經過反覆評估,給出了明確結論:陳國明在行為時,因罹患嚴重思覺失調症,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均顯著降低。辯護律師沈志維以此為據,強調陳國明是「嚴重精神病患」,主張國家和社會對這類邊緣人群的照護系統存在巨大疏漏,並以此請求免除死刑。
每一次開庭,陳國明都像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被帶上被告席。他眼神呆滯,對法官的詢問、檢察官的指控、甚至被害者家屬錐心刺骨的陳述,都毫無反應。他沉浸在自己的喃喃低語中,彷彿周遭的一切紛擾都與他無關。這種徹底的「抽離」,比他任何激烈的反應都更令人不寒而慄。他像一面冰冷的鏡子,映照出精神疾病深淵的可怕面貌。
林家聘請的檢察官言辭如刀,直指陳國明行兇手段極其兇殘,目標選擇完全隨機,對毫無反抗能力的幼童下手,社會危害性極大。他駁斥精神鑑定報告,認為陳國明在案發前能獨自購買兇器、長時間在社區遊蕩尋找目標,顯示其具備相當的現實認知和計劃能力,絕非完全喪失辨識力。他請求法庭判處極刑,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告慰無辜逝去的生命,才能撫平家屬的創傷,才能回應社會大眾對安全的強烈恐慌。

法庭辯論的硝煙瀰漫到整個社會。「司法人權促進會」(原廢死聯盟)成員在法院外舉著「反對死刑」、「精神病患不是惡魔,需要治療而非處決」的標語。另一邊,以「正義之聲」為代表的團體則高呼「殺人償命」、「還小燈泡公道」、「支持死刑」。網路上的爭論更是鋪天蓋地,勢同水火。支持廢除死刑者痛陳國家精神衛生體系的潰敗,認為殺死一個精神病患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只會讓社會逃避責任;主張死刑者則悲憤質問:「誰替那個被當街砍死的小女孩負責?誰又能保證這樣的慘劇不會再次發生?」憤怒、恐懼、悲傷、對正義的渴求、對安全的焦慮、對未來的迷茫……所有情緒在「小燈泡」這個名字下激烈碰撞、撕裂。
作為深度跟進此案的記者,我目睹了太多撕裂的瞬間。在法院外的台階上,我曾看到一位情緒激動的「正義之聲」支持者,對著一位手持「反對死刑」標語的「司法人權促進會」年輕成員怒吼:「死的不是你家孩子!你說得輕鬆!」那位年輕成員臉色蒼白,嘴唇顫抖,卻固執地沒有後退一步,眼中含著淚:「我…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更多悲劇…根源不解決,還會有下一個受害者…」那一刻,口號背後的個體痛苦和無措,清晰得讓人窒息。
漫長的司法程序如同鈍刀割肉。一審,台北地方法院認定陳國明因精神障礙減刑,判處無期徒刑。檢方和林家上訴。二審,高等法院同樣判處無期徒刑。案件最終上訴至最高法院。每一次宣判,對林家都是新一輪的凌遲。林明義夫婦在鏡頭前,面容一次比一次憔悴,眼神裡的光一點點黯淡下去。他們不再激烈控訴,只剩下一種沉重的、幾乎要將人壓垮的疲憊和堅持。林太太曾低聲對我說:「張記者,痛是永遠不會過去的。我們只是…想知道一個答案,一個能讓我們女兒的死…稍微有那麼一點點意義、能阻止下一個悲劇發生的答案。死刑?無期?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答案』了…」她的話語裡沒有仇恨,只有無邊無際的悲傷和對未來的深深憂慮。
最終,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落下了沉重的帷幕:維持無期徒刑。判決理由的核心,依舊是那份精神鑑定報告。法庭認為,陳國明在行為時辨識和控制能力顯著受損,依刑法規定不得判處死刑。判決書中也沉重地指出,此案暴露出社會安全網對高風險精神病患的干預存在嚴重缺失,要求行政及立法部門深刻檢討並改進相關機制。

終審定讞的消息傳來,如同在滾沸的油鍋裡又澆進一瓢冷水。社會輿論瞬間爆炸。支持廢除死刑的群體將此視為司法對精神障礙者人權保障的進步;而主張死刑的一方則悲憤難平,認為司法未能實現實質正義,讓無辜幼童的生命未能得到等值的尊重,更憂慮無期徒刑在假釋制度下可能並非真正的「終身監禁」,無法有效阻遏潛在的模仿犯罪。花漾社區裡,一種無聲的恐懼在鄰里間蔓延。家長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警惕的目光掃視著周圍。陽光依舊明媚,卻再也驅不散那日午後留下的冰冷陰影。
案發多年後,我再次拜訪了林家。那輛小小的粉色腳踏車,靜靜地靠在客廳角落,被擦拭得一塵不染,像一個沉默的紀念碑。客廳的牆上,掛著曉光大大的笑臉照片。林明義顯得平靜了許多,鬢角已染上霜白。他告訴我,他們夫妻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基金會,叫「曉光角落」,主要致力於推動兒童安全教育和社區鄰里守望計劃。
「死刑,無期…爭論好像永遠沒有盡頭。」林明義望著女兒的照片,聲音很輕,「我們改變不了判決,也帶不回曉光。但看著她笑,我們就想,能不能讓別的孩子,少一點危險?哪怕只是一點點。」他頓了頓,目光裡有深沉的痛楚,卻也有一絲微弱但執拗的光,「每次在社區看到孩子們玩,安全地、開心地玩…我們就覺得,曉光好像…還在那裡看著,還在笑。」
林太太拿出一個舊鉛筆盒,是曉光上幼兒園時用的,上面印著可愛的卡通圖案。「這是曉光的東西,」她輕輕撫摸著,指尖帶著無盡的溫柔,「我們把它放在基金會辦公室。提醒我們,也提醒每一個來做義工的人,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那些活著的、還會笑、還會跑、還會問『為什麼』的小小的光。」她的眼淚無聲滑落,滴在鉛筆盒上,「原諒那個生病的人?我不知道…也許有一天吧。但求一個公道,一個不讓這種事再發生的改變,這是我們能替曉光做的,也是我們必須做的。」
離開林家時,暮色四合。華燈初上,社區裡傳來孩子們追逐嬉戲的笑鬧聲,清脆悅耳。我站在街角,回頭望向林家那扇透出溫暖燈光的窗戶。那個裝著「小燈泡」曉光鉛筆盒的辦公室,彷彿也散發出一種微弱卻堅韌的光芒。它無法驅散世間所有的黑暗,也無法彌合那些深刻的傷痕與分歧,但它固執地亮著,像一粒不肯熄滅的火種。
在這個關於生命、瘋狂、司法與人性的複雜漩渦中,在死刑存廢這個注定充滿爭議的永恆命題前,或許,正是無數個像這樣微弱的光點,無數份像林明義夫婦這樣在破碎後仍試圖守護他人的努力,才是我們穿越黑暗、避免墜入深淵時,所能緊緊抓住的、最真實的東西。那輛粉色的腳踏車永遠停下了,但總有人在努力修補那條讓它傾覆的道路,為了其他還在前行的車輪,為了那些尚未被黑暗吞噬的光亮。我拿出筆記本,藉著路燈的光,記下這一刻的感受。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是此刻唯一能回應那些笑聲與淚水的儀式。我知道,這個故事遠未結束,而我的記錄,也仍將繼續。
後記:筆尖的重量與微光的溫度
這篇報導,或者說這個故事的重量,遠超我寫過的任何一篇特稿。十年過去了,鍵盤敲下最後一個句點時,指尖傳來的依舊是那股熟悉的、沉甸甸的冰涼,彷彿還能觸摸到那年春日午後,灑在血泊上那過於刺眼的陽光。

作為第一現場的目擊者,這個身份像一道烙印,永遠改變了我觀看世界的方式。從按下快門記錄苦難,到選擇移開鏡頭保護絕望,這中間的掙扎,是身為記者最撕裂的功課。我記錄了陳國明空洞的眼神,記錄了林明義夫婦一寸寸被悲傷風蝕的容顏,記錄了法庭上冰冷的法條與沸騰的民意如何激烈碰撞。每一個字,都像在搬運一塊沉重的石頭,壘砌著這個名為「小燈泡」事件的紀念碑。它不僅是關於一個孩子的消逝,更是關於我們這個社會集體的創傷、困惑與艱難的尋路過程。
死刑存廢的爭議,在曉光事件後,如同被投入巨石的深潭,激起千層浪,迴盪至今。每一次類似的悲劇發生,這爭論必將再起,尖銳而痛苦。支持與反對的聲浪,我都曾近距離傾聽。在法院台階上目睹的對峙,那年輕成員含淚的「根源不解決,還會有下一個受害者…」,以及對方悲憤的「死的不是你家孩子!」,這兩句話,像兩把鋒利的刀,精準地剖開了這個難題的核心:對正義極致而不同的渴求,對安全無法消弭的恐懼,以及對社會責任歸屬的深刻分歧。誰的痛更重?誰的訴求更「正義」?作為記者,我無權評判,只能忠實呈現這片荊棘叢生的人性與制度困境。
陳國明最終因思覺失調症獲判無期徒刑。這個判決,將巨大的問號拋向了社會:我們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與照護網絡,是否足夠堅韌,能兜住那些滑向深淵的靈魂?陳國明不是第一個,也絕非最後一個。他的「奉旨除妖」聽來荒誕,卻像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系統中未被填補的巨大黑洞。判決書中要求行政立法部門「深刻檢討」的字句,是司法系統沉重的嘆息,也是對整個社會的嚴肅叩問:我們是否願意投入資源、建立機制,在悲劇發生前,接住下一個「陳國明」?這不僅是法律的問題,更是社會成本與集體良知的考驗。
而林家,則以另一種方式,教會我關於「活著」的重量。成立「曉光角落」基金會,推動兒童安全與社區守望,這不是一個復仇的故事,而是一個在廢墟上試圖點燈的歷程。當林明義望著社區裡安全玩耍的孩子,說出「曉光好像…還在那裡看著,還在笑」時;當林太太撫摸著那個舊鉛筆盒,低語著「為了那些活著的、還會笑、還會跑、還會問『為什麼』的小小的光」時,我感受到一種超越個人悲劇的巨大力量。他們沒有被仇恨吞噬,而是將無法承受的喪女之痛,轉化為守護他人微光的具體行動。這種轉化,並非遺忘,而是另一種更為艱難的銘記——用行動抵抗虛無,讓逝去的生命,成為保護生者的一磚一瓦。
那個放在「曉光角落」基金會裡的舊鉛筆盒,上面的卡通圖案或許會隨著時間褪色,但林太太滴落其上的淚痕,以及它所承載的溫柔與決心,卻比任何激昂的標語或冰冷的判決書都更為有力。它提醒著每一個靠近的人:在龐大的社會議題、無解的司法爭論、複雜的精神醫學課題之下,是一個曾經鮮活、如今只存於記憶與照片中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林曉光。她喜歡騎粉紅色的腳踏車。她的笑聲,曾經清脆地敲碎過午後的沉悶。
這篇報導,是我作為一個記者,在巨大悲劇與複雜爭議面前,所能獻上的最誠摯的記錄與思考。它無法提供終極答案,也無力彌合所有的傷口與分歧。但我祈願,它能像「曉光角落」散發出的那點微弱光芒一樣,固執地存在著,提醒我們:在追問「為什麼」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具體的「誰」;在爭論宏大命題的喧囂中,依然看得見個體的痛楚與微小的努力;在面對深淵時,總還有人,願意俯身,去修補腳下那條讓光明得以延續的道路。
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應當擁有在陽光下安全騎車、放聲大笑的權利。保護這點點微光,是我們所有人,無可推卸的責任。
張介安 謹誌
於「曉光角落」基金會成立十週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