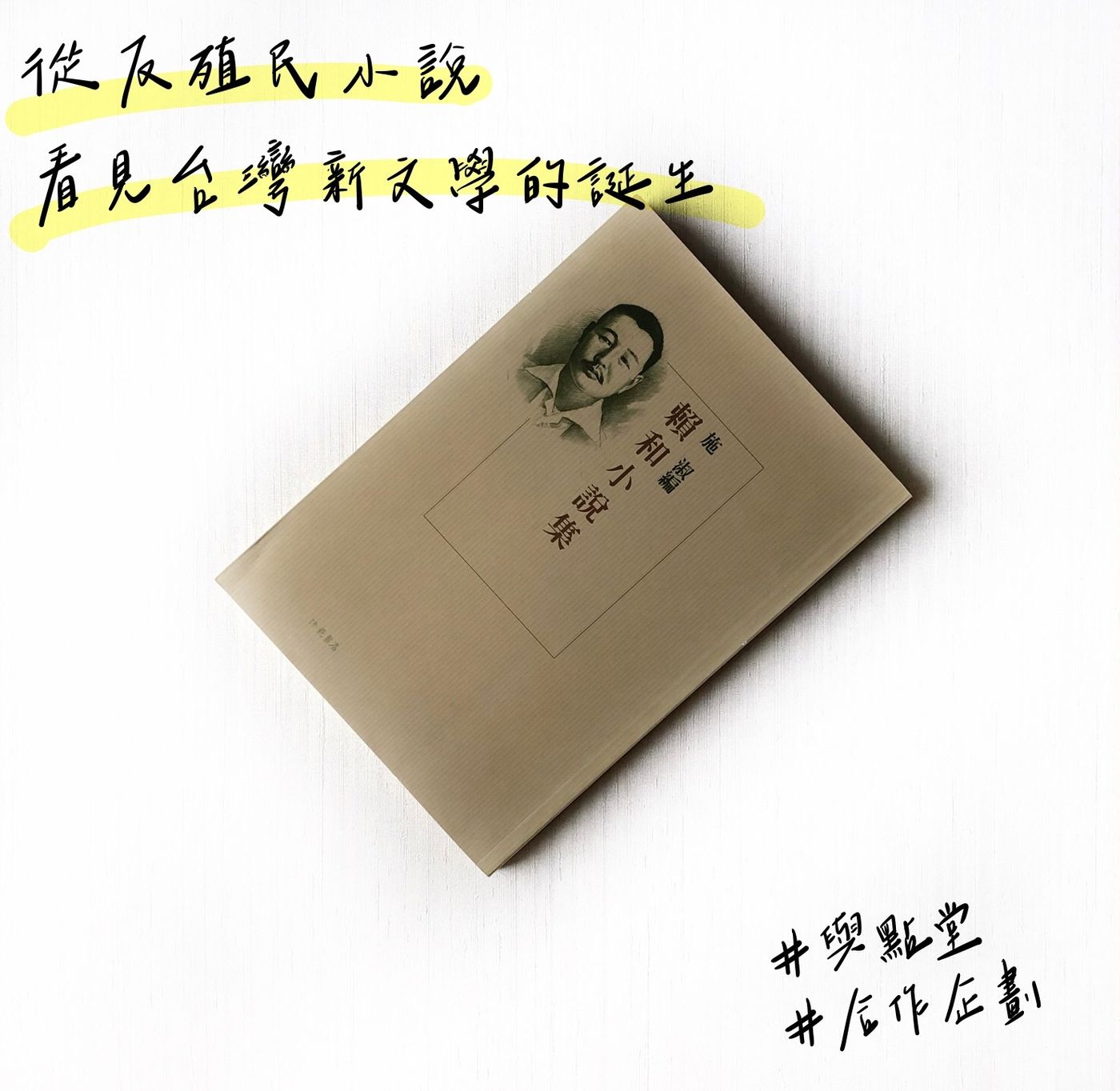【專題序】
人是群居動物,天生就能捕捉表情的資訊,才能夠理解同伴的心情,進而協作。
當人們看到賴和、周定山的表情,會有什麼想法呢?這兩張表情距離我們好幾十年了,我們還能理解這兩位作家的心情嗎?周定山的表情代表什麼?賴和的表情又說什麼?
同樣的表情,在不同人眼裡有各式各樣的解讀,他們是在生氣、暗喜還是憤怒?把這些作家的表情當成鏡子,不只可以知道一個人的經歷,也可以嗅到整個時代的變動。利用拾藏作者的文字,重新帶領讀者進入賴和、周定山所處的時代氛圍,這座島嶼隨著時代躁動,直到現在,跳動的脈搏依然清晰可見。

挑選這件藏品,是一個誤會。
使用臺灣文學館「文物典藏查詢系統」偶然看到它,心裡一驚,以為是賴和(1894-1943)的死亡面具。因為不久前閱讀某篇文章,才看到臺北圓山的臨濟護國禪寺內,藏有日治時期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臨終時採模的石膏面部遺像。死亡面具盛行於17~19世紀,但在20世紀已逐漸為攝影技術所取代,一般只有少數身分顯赫者的家族會製作。為何賴和遺族要製作死亡面具?又為何臺文館庫房會藏有這種東西?那面具的白、及面具背後的空無,偶然的一瞥,讓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衝擊,並快速點選下一頁。但幾分鐘後,冷靜一想,若真是死亡面具,那麼它也精確紀錄了賴和臨終時的最後表情肌理。
賴和逝世,是在1943年1月31日。兩個月後,楊雲萍(1906-2000)回憶他到帝大附設醫院探病時,原本躺臥的賴和突然起身,按著疼痛的心臟激動地說:「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楊急忙安慰道:「不會的,三、五十年後,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不數日,賴和即因心臟僧帽瓣閉鎖不全逝世於自宅,享年50歲。一生為新文學運動努力的賴和,為何會在生命將盡之際說出這樣一句消沉的話?對他而言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而在其臨終之時,眼中究竟看到了什麼?我懷抱著這些疑問,重新回到方才的頁面。不知何故,那副面具似乎不再那麼讓人感到不安了。望著白色面具上那直挺的鼻樑、微蹙的眉,以及挖空以致不知望向何方的眼廓,我覺得它像賴和,卻又有些微妙的不相似(臨濟護國禪寺內的後藤新平面具,也不太像後藤新平。是採模技術的限制嗎?還是臨終之際的病容所致?)究竟哪裡不相似,我也不太能說得具體。我認識的賴和,又是什麼樣的呢?

後來我向臺文館申請入庫房看藏品,方知其實那並不是賴和的死亡面具,而是二十年前文資中心籌備處某員依照片製作,並於退休後捐贈臺文館。雖不是死亡面具,但在必須維持恆溫保護藏品,以至於在盛夏的七月依舊有些寒涼的庫房,仍給我一種死亡的寧靜肅穆之感。白色的面具,平擺在攝影用發光的白色平台上。我彎腰、俯視。挖空的眼廓沒有回應。我歪著脖子看他的側臉。我緩步繞著平台,從各種角度看他。庫房很安靜,沒有人說話。忽然間,我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個我遲到許久的歷史現場──那彷彿親人臨終之際,隨侍在側,也像是蓋棺之前,最後的遺容瞻仰。賴和在自宅離開的那天,臺北寒冷,下著細雨。呂赫若(1914-1950)在日記中記下了天氣,但賴和逝世的消息應該還沒傳到他耳中,否則應該會記下才是。幾天前才探病的楊雲萍,也是在賴和走了一段時間後才得知消息。喪家並沒有給每個人發訃聞。但公祭時,據說參加喪禮者有五百人,且沿路有許多彰化民眾路祭,供奉青果、焚香祭拜。賴和臨終之時,想必是帶著極大的遺憾與寂寥的吧。否則他怎會說出他們曾努力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洩氣話。但曾受過賴和幫助的臺灣文學家們,又是怎麼看待這位前輩、以及在其呵護下茁壯的新文學運動的呢?賴和離開後的那個夏天,以張文環(1909-1978)為核心的《臺灣文學》第3卷第2號刊出「賴和先生追悼特輯」,楊逵(1906-1985)、朱點人(1903-1951)、楊守愚(1905-1959)都給他寫了文章,編輯部也請張冬芳(1917-1968)將他的〈我的祖父〉及〈高木友枝先生〉翻譯成日文一同刊登。編輯同人在後記寫道:
臺灣文學者的大前輩賴和在二月急逝,祈求冥福,刊出追悼特輯。賴和是醫師。舊來臺灣將醫師定義為金錢的亡靈,但也身為醫生一員的賴和,終其一生,獻身於文化極大。同人全體對其急逝惋惜不已。
賴和有一顆仁心,不求名利,行醫常不跟窮人收錢,並將一生貢獻給新文學運動,作品以強烈的寫實及抵抗精神聞名。但他昂揚的意志,其實在中年後已顯消沉之跡。新詩〈低氣壓的山頂〉(1931)與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1935),可以看到他歷經1931年大逮捕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全面挫敗、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的結成及其後的分裂,心境上的黯淡沉鬱。然而賴和從來都不曾像〈獄中日記〉(1941-1942)那樣赤裸地袒露自己的徬徨、焦躁、軟弱,那樣自覺於死亡的逼近。1941年12月8日,賴和在未被告知事由的狀況下到署拘留。入獄第八日,賴和用鉛筆在粗紙寫下:
我尚想今日是禮拜,早上風冷,窗到近午試為放下上扇,日光射入,神為一爽,午飯後,兩足冷,使受日光照射,且計日影之移過床板的時間,一片約十二分,共有九,在東邊日影西斜,若由上計算,要到三點,竟於二時四十分過,日影移上墻腰,想把時刻記錄起來,由放物箱拿出手帳,看有便箋一枚,初想寫下詳細家務金錢的整理事件,有似遺囑,不禁傷心,乃轉念頭,試為記錄心經一篇,不知有無差錯,不知何日得有對證的機會,心又淒然。
陽光穿越氣窗、射進牢房,失去自由的人,得以暫時享受平等的溫暖;也能藉由日影的移動,重新確認時間流動的實感。然而隨著關押日長、出獄無期,賴和的日記不時瀰漫著死亡的陰影。無論記下什麼,都像遺囑。既是一生的回顧,也是身後事的分配。

這是賴和第二次入獄了。第一次入獄時他方三十,因為參與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控違反「治安警察法」,三週後獲不起訴處分出獄。第二次入獄,賴和已近遲暮了。原本只是一個極為平常的傍晚(但在遠方──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於焉爆發),警官前來謂有話要問,請之到署一趟。賴和匆匆將手上事務結束,便乘自轉車(腳踏車)出門。豈知到署後,只要他等,也許三、五日亦未可知。賴和只得求人通知家裡來牽他的自轉車回去。未被告知事由、也不知州高等課何時要來取調(審訊),不安與焦躁,反覆打磨他原本就纖細多感的神經線。他在夜裡搔癢難耐、頻尿,輾轉難眠;而在天明後「起來頭似帶箇蓋,意昏昏然,想前想後,使我悲觀。」每日,他將穿過牢房鐵柵抵達的破碎訊息轉換為某種徵兆,判斷自己的處境:「午飯後,水野樣來監房存問,要代買雜誌,對其好意,真為感謝,因此又知事屬匪輕,不易有到社會之日。」有時則是在無期拘禁的悲觀之中,強迫自己樂觀:「午後司法主任到監來,我問他許可剪髮,他說許可,我說當寒,他亦說此去寒,待出去纔剪較佳,這句話,又幾分使我安心。在我想像裡,當檢束不會過久。」他讀醫書,卻總思及剛過世的三弟,心中懊悔沒給他更好的醫治;讀心經,則多少能給他一些慰安。當讀心經也無法鎮定其心緒時便寫漢詩,但寫詩有時也只是徒增愁悶:「平仄乃失檢不葉,今日思改正,久思不能成。」入獄第十七日,是官廳封印日(12月24日)。若此日未能出獄,就要等到明年一月五日官廳恢復辦公才有機會了。這是今年出獄的最後一線期待,但賴和終究還是失望了:
我的心真是暗了。幾次眼淚總要奪眶而出,想起二十年前的治警法當時,沒有怎樣萎靡悲觀,是不是年歲的關係,也是因為家事擔負的關係。
不再年輕的賴和,已不若往昔的意氣風發;擔負著家計卻不得出獄行醫,又讓他焦急難耐。但賴和更深層的恐懼,恐怕是被世界遺忘在監獄之中,一個人孤獨死去吧。他既等不到人來給他問罪,也時常等候不到請求家裡差入的書籍或是襯衣,在日記抱怨家人難道以為他已死去。他夢見龍舌蘭開花,疑為惡兆,並發現自己的心臟似有異常。他託池田公醫與李慶牛診斷。但身為醫生,他也給自己聽診。已是1943年元月了。但上一個冬天仍未完全過去。當他以冰冷的聽頭,緊貼胸口乾澀而逐漸失去彈性的肌膚,在不可透視的肉體內部,他聽見了自己的心尖第二音不純,以及隱隱作痛的感慨遺憾:
我的心臟的病,李慶牛先生謂是榮養不給的原因,我自己恐是心實有病變,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但若得早些釋出,當要檢查詳細纔好,原因只在一兩夜的(初五、初六)完全不眠,到十日第二心尖音只少不純,至十三日已是雜音,進行可謂速,已注了二回射,今晚睡眠看看如何?
這是賴和入獄後第三十九日的日記,也是最後一篇了。因病之故,他必須停筆。但諷刺的是,也托病之福,數日後終於得以出獄。賴和的判斷很準。李慶牛想安慰他,但他知道是心臟問題。出獄一年後,賴和病逝,死因是心臟僧帽瓣閉鎖不全。這份連續記載三十九日的獄中日記,終成賴和生命潦草的絕筆。

賴和在獄中自覺時日無多,感嘆來不及見到大時代的完成。而新文學運動,也成了他的未竟之夢。其實,在寫下〈一個同志的批信〉的1935年後,他已經悄悄脫離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線了。雖然李獻章(1914-1999)出版《臺灣民間文學集》(1936)時他也寫序、楊逵脫退臺灣文藝聯盟另創《臺灣新文學》時,他也擔任漢文編輯,但賴和自己的作品畢竟是少了。〈一個同志的批信〉後只斷斷續續寫著漢詩,抒情言志,直到生命的終點。以漢文寫小說的無政府主義者王詩琅(1908-1984)即時發現了賴和的頹喪。他在〈賴懶雲論──臺灣文壇人物論(四)〉(1936)寫道,賴和的近作缺乏以往的強韌,創作的火花也顯得抑弱了。「如果筆者的這個觀察沒有錯誤,這是做為一個作家的危機」。王詩琅也發現,整個臺灣文學生態似乎也漸漸改變:
近年來,本島人在文學方面,日文方興未艾,佳作多如潮湧;相反的,漢文與其說不興盛,還不如說日漸衰微。他的作品不但沒有像過去那麼多產,在前述的近作〈一個同志的批信〉中,還看得出萎靡散漫的樣貌。
依照年代閱讀他的所有作品,見到每一篇作品的發展軌跡,我反而對今後的他有比較多期待。某人說:「三十歲以後開始寫小說,到四十歲才寫得出真正的小說」,我就想對他有這樣的期許。
三○年代中期,年輕的日語世代作家正式崛起。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翁鬧(1910-1940),以及後來的龍瑛宗(1911-1999)陸續在東京中央文壇獲獎;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風車詩社、鹽分地帶等,也高舉各自的文學主張,活躍於島內外。但日語世代的崛起,或漢文的日漸衰微,與賴和的心態上的消沉應是兩回事。他仍守護著新文學,自己卻不太寫了,作品也顯露了倦意。
王詩琅的〈賴懶雲論〉,對賴和的思想、文學特質與地位有極精準的評析。他感念賴和,卻也疼惜著他,想給消沉的他一點激勵。王詩琅是第一位將賴和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母」的人:「臺灣的新文學能有今日之隆盛,賴懶雲的貢獻很大。說他是培育了臺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恐怕更為恰當。」無論在新文化或新文學運動中,賴和並不是革命型、運動型的人物。與其以激烈的言論發起文學論戰、或涉足政治社會運動,他始終默默地進行新文學的實踐,並在擔任《臺灣民報》文藝欄編輯時,給予同輩後進許多的提攜幫助。他自己的文學也是這樣的:不以立場之基進、或故事之曲折精采取勝,而是擅於方方面面的分析思考辯證,內斂紮實,且多所內省。他有著宛若手術刀般銳利的科學之眼,卻同時擁有一顆柔軟、溫厚的詩人之心。他知道社會必須改變,卻從不以知識精英自居,將庶民大眾視為有待啟蒙的愚昧落後者。他的文學自漢詩始,卻也願意摸索不被看好的新文學的道路,進行白話文及臺灣話文的實驗。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他無疑是懂日文的,卻終生以漢文創作。因為他清楚知道,他的文學是要寫給誰看的。他穿臺灣衫,說是為了便利。他樂於助人,但不會強迫他人接受好意、或給人精神負擔。他不喜歡虛矯浮誇的派頭,拍照時經常站在後排左二或是右三的位置。在人群中他並不特別顯眼。但他也不需要顯眼。他是開拓者,但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悲劇英雄。他心有不甘。但他幫助過的晚輩,如今也接下了他的棒子,繼續為臺灣的文學文化、乃至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儘管隨著戰爭迫近,自由的空間是越來越小了。賴和漸漸淡出新文學運動,卻沒有真正離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一直都在。

楊逵說,1920年代末在彰化待了一陣子,常去賴和家玩。賴和的客廳有一張長方形大桌子,總擺著好幾種報紙。「不管先生在不在,我們都是自己進去,自己看報,自行討論,自行離去。」賴和有時出診不在。在的時候,總是在幫人看病:
當時先生不招呼我們,而我們也很高興他不招呼我們。
不過,有空時,先生還是會進來這個客廳加入我們。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我們不怎麼理會他,而他好像也不怎麼理會我們。
就像一家人在家裡碰面時沒什麼感覺那樣。
但是楊逵說,身體不舒服時,一解開衣服,賴和的聽診器就來了。開了藥也不收錢。
賴和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在與不在都沒關係。反正客廳已擺了書報,大家當自己的家,別太在意。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守護臺灣新文學的。這是賴和的溫柔,也是浪漫。當然他也心急,因為無法親眼見證大時代的完成;不能夠肯定,此生投入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否真有意義、抑或只能是徒然的夢。於是他憂慮、不安,在獄中與病榻上說了洩氣的話。但沒關係。我們都記得。我們都在。
臺灣文學還要繼續寫下去。
★作家小傳
賴和(1894-1943),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出生彰化,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賴和在「新舊文學論戰」中,是主張新文學的健將,並積極投入臺灣新文學創作,其作品洋溢著民族情感與人道主義,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一生橫跨日本殖民臺灣50年。
賴和幼年習漢文,舊文學根柢深厚,16歲考進總督府醫學校,1917年六月在彰化建立「賴和醫院」。1918年二月前往廈門,在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中任職時,感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化、社會的影響力,而積極投入臺灣文化、臺灣新文學的推動及關注。
因積極參與社會團體並擔任要職,賴和二次入獄,1941年12月8月,珍珠港事變當天,第2次被捕入獄,約50日,在獄中以草紙撰述〈獄中日記〉,反映了殖民地下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沉重心情,後因病重出獄。1943年1月31日逝世,享年50。
★延伸閱讀
★觀測員簡介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2018,合著)。合編有《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2020)、《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2020)。
視覺設計/瞿繼維
攝影/鄭宏斌
上稿/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