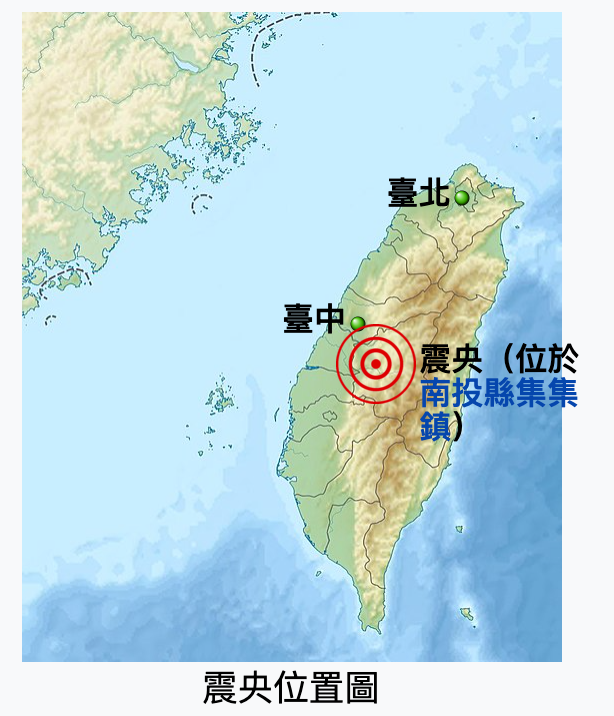2014年1月,在海燕風災的兩個月以後,跟隨救援組織前往菲律賓重災區進行採訪的我,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首先,對救援組織是否應該花錢讓記者出國採訪這件事感到不安。尤其我們居住的地方往往是陰暗災區中的唯一還亮燈的舒適酒店,有豐盛的餐點。可是,每天深入災區見到的又是連取得基本資源都有困難的民眾,這種衝突感讓我還有其他記者們難以消化。
某天晚餐,終於逮到機會向一位資深救援組織領袖表示我的困擾。他卻認真地說,安排記者深入災區採訪,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外傳遞災區的情報,一來可為災區爭取更多的資源,二來也便於贊助者了解救援組織的運作情況。再者,對救援團隊來說,面對記者的問題也是一次梳理與檢討的機會。



這番回應讓我重新找到使力的方向。回國後開始在整理與書寫災區故事時,滿腦子都在想著如何不辜負願意接受我訪問的人,如何靠著文字的力量為他們爭取更多的資源。只是這時候報社高層卻認為,不需要為一個僅有一星期的行程佔有太多的版位。
雖然最後我還是爭取到了兩期的連載,硬是把能寫得都寫了,但心裡卻也偏執地在想,這趟免費的旅程或許被高層當作了員工福利,他們才不是想要關心世界重大的自然災害,抑或同情災情嚴重的菲律賓呢。沒人知道我當時的心境轉折,那些文字到底有沒有發揮影響力我也不清楚,總之我獨自默默地在消化這件事。之後與主管在幾個課題上的意見相左,他們沒有公然地反駁我,我也沒有強烈地爭辯,就只是沒辦法好好地溝通,對工作也就不敢再有太大的期望,渾渾噩噩起來。到了5月左右剛好有了其他機會,我就順勢離了職。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自己還真的是意氣用事。我最擅長的始終是觀察與書寫,之後轉換的工作都太靠近政治核心——我以為我可以發揮所長,但在只求結果不問過程的緊湊工作中,我也失去了花時間去思考與探索的機會。
繼續默默地在報社工作,會不會現在就已經累積了什麼,心裡比較踏實點呢?
只是當時的我也沒力氣糾結這麼多。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為無法控制的事,我花再大的力氣去堆砌的安全感,說崩塌還是會崩塌的。海燕飛過捲走了數不清的人與事,只留下遍地瓦礫。我想起五十歲便罹癌逝世的母親,在照護她一個學期以後,我並沒有留下來。我以為我勇敢地找尋人生方向的決定,會帶給她力量,但最終她還是走了。
之後的我一直用忙碌填補生活:到新加坡進修兩個月半、完成論文口試、繼續出國留學唸博士。庸庸碌碌一年後又對博士的就業市場感到惶恐,匆匆回國找工作,找到工作後也不住在家裡。
想來弟弟對我的怨恨從那時候就已經埋藏。我根本沒有時間看他一眼。他一定以為我不用負什麼責任,卻過得自在逍遙。
我們都很愛意氣用事就是了,卻忘了彼此展現了生活不同的可能,都可以很安逸和自由。但我們卻消耗很多的力氣在羨慕彼此,然後討厭彼此。


烈陽下海燕風災的災後現場異常地平靜。我聽了許多痛哭流涕的故事,看到遍地的十字架,然後回到有蔥綠草地、徐徐海風的地方,靜靜地聆聽著遠處斷斷續續、敲敲打打的聲音,我自顧地覺這就是“活著”的感覺,因為大難已去,新的生命已經開始在醞釀,生活還是要過下去。
我當時的文字就是這麼描述的。還特別強調了那張在奧爾莫克鎮(Ormoc)拍的“沒了屋頂,沒了家園,但我們沒有失去希望”的照片。
現在想想,當時的我只不過是從一場更霧殘雲愁的災難中,對自己的另一場傷痛感到釋懷。可是傷痛一直都在,還會在我最脆弱的時候,反手一擊。


最後一天,和同行的記者朋友約好要早起看晨陽。他們是電視台的記者,畫面比講故事還要關鍵。最後一晚我們留宿的地方靠海,晨陽剛好是可以一掃愁雲,讓觀眾感覺到希望的象徵。
要不是留下了照片,我差點都忘了當時的場景。早晨非常地冷,冷得我們直抖索,海邊的石塊多,攝影機架了好一陣子才架起來。然後微小的亮光,好不容易才地推開雲層,慢慢地讓大地暖和起來。
彷彿整個世界都會瞬間好起來,菲律賓會好起來,我也會好起來。只是再看一次又是一次的哆嗦。
我還不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