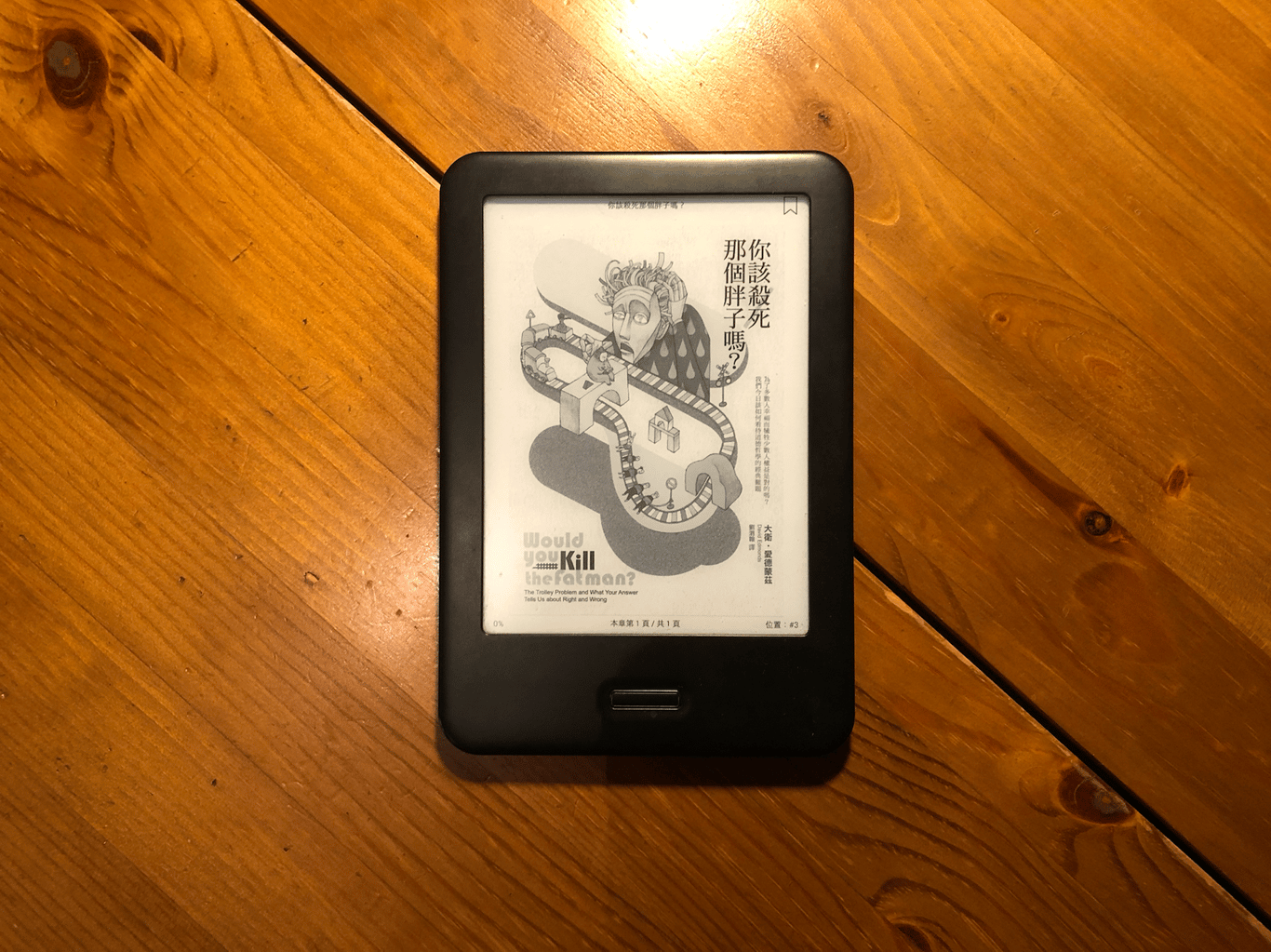所謂的四維解,就是用禮義廉恥的模型來分析問題。同時,經過分析之後,都覺得這並不真是個「難題」。
題目是:一輛失控的列車在鐵軌上行駛。在列車正行進的軌道上,有五個人被綁起來,無法動彈。列車將要碾壓過他們。你站在改變列車軌道的操縱杆旁。如果拉動此杆,則列車將切換到另一條軌道上。但是,另一條軌道上也有一個人被綁著。你有兩種選擇:
- 什麼也不做,讓列車按照正常路線碾壓過這五個人。
- 拉下操縱杆,改變為另一條軌道,使列車壓過另一條軌道上的那個人。

一台電車一根桿,等當英雄或狗熊
這個難題常被引用做為哲學上功利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間的矛盾。選項一是做為自由意志主義的選項:我們無權選擇任何人的性命;而選項二是做為功利主義的選項:反正都有人要死,只死一個人總比死了五個人好。但這兩個看似是僅有的選項剛好都抵觸了另一個主義的宗旨,因此襯托出一種道德無法兩全的「假像」。
但這兩個選項真的是僅有的嗎?看似如此,其實不然。隨著我的分析,這個難題很多沒有釐清的問題會一一顯現。道德的選項在於人選擇如何融入他所處的團體,而不是如何去操縱眼前那根操縱杆。
分析的方法乃是找出團體的範圍邊界在哪?同時群體內有沒有分化?我們從題目可以看出來,團體應該就是這六個無辜被綁在鐵軌上的人與你一共七個人。然而題目裡並沒有線索提到能分析出團體內部有無分化,因為他並沒有說被綁的人的職業身份。網路上該題的有些版本會強調你與受難者並不認識,如果認識,則必須明確說出身份與關係,否則今天你在這裡做決定(也就是另五個人受難或一個人受難)後的結果會因為被綁的人各式各樣的身份或關係而不同,使得問題變得相當複雜。也許也應該另外獨立探討。
一個角色不能轉化的經典問題,就是你女友問你「我和你媽一起掉水裡你會先救誰」?所以想想電車難題可能還比較簡單。因此在這裡採用你與六位受難人並不認識的說法。
但,團體範圍真的是這六個人嗎?這裡面是不是有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如果這世界就只有這七個人,那火車是誰造的?鐵軌是誰造的?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六個人莫名地被綁在鐵軌上,而且我就剛好站在一個可以操縱列車的操縱槓前?這些問題都不是在抬槓,而是這個問題之所有看起來很棘手,其實是問題裡的族群團體範圍其實有隱藏角色。因此當故事角色一登場的時候,他就立即陷入了一個設定好的情境(Context)當中而被預設好了一定要做某些事。他不能像假裝什麼都沒看到的路人一樣無視災難而走過去,同時又不得犧牲某些人等著遭受到社會的非難。
這就像忽然掉到異世界裡的勇者一樣,已經有著大魔王綁走了王國的公主的劇情等著勇者來發揮。那麼,如果公主沒救成,被魔王先O後X,是要怪勇者囉?頭腦正常的人當然知道是要怪魔王吧?!那為什麼電車難題就變成難題?
以該題目的陳述,在現實社會中如果真的發生了類似的場景,用常識來理解,無論你操不操縱那個桿,你都不會有任何法律責任。因為事故責任都不在你。你可以是目擊者,你只要上警局好好地將你所見做好筆錄,就算盡了你最大的社會責任。就算這不是一場謀殺案,剛好真的就有六個人身陷鐵軌,那麼鐵道系統本身是加害者,所有鐵道系統的關係人都既可能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這會是一場國賠案。說不定你碰了那根桿,無故闖入鐵軌,還要接受罰則(筆者非法律專長)。
重新出題
因此,題目所提供的情境其實是不足的,也就是出題有瑕疵,送分!不過我不是來這裡敷衍了事的。可以想像大家對於這種難題的困境,也就是那功利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間的矛盾在感情上是真的存在的。它只是題目設計的不好。我們必須把太多預設的情境拿掉,而且是人為的情境。人為的預設情境會使得團體內部的參與角色直接分化,而且隱藏在背後的角色還無法判知。因此,我想調整過後的情境大概會是如此:
想像山上有顆大石頭掉下來,你剛好在高處看到若石頭直直掉下去會砸死五個人,但若你來的及用肉身去阻擋它,但它會倒向另一邊砸死另一個人,請問此時你應該如何選擇。
就不再抬槓別說什麼石頭也許滾下來後不會壓死任何人;或是你可以用大喊的叫大家趕快跑。我想我們需要塑造出來的問題就是:「當一個團體面臨外部災難的時候,內部的某個個體是否有選擇其他個體來承受災難的權利」?當這個題旨相當清楚之後,接下來的討論才有意義。
同時,這個話語已經相當接近四維模型描述問題的方法。若把角色分化和角色不分化的問題分開來看,題目可以衍生成以下兩個問題:
- 「當一個角色未分化的團體面臨外部災難的時候,內部的某個個體是否有選擇其他個體來承受災難的權利」?
- 「當一個角色分化的團體面臨外部災難的時候,內部的某個角色是否有選擇其他角色來承受災難的權利」?
這裡先直接講答案:兩個衍生題的答案都是「是」,但第一題有附帶條件。
藤原拓海的電車難題
而我們先解釋第二題,因為它比較沒有爭議。第二題之所以某個角色可以有權利選擇其他的角色來承受,正是有選擇權的角色是因為被視為外部壓力的解決者。角色在團體裡的天生義務就是增加團體在外在環境中的生存率。角色乃是先承受了該外部壓力而懂得,或取得有利位置,而能夠為團體解決問題而躍升成獨立角色;這是屬於「廉」的範疇-擁有解決外部能力的角色,他們在團體中不但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同時也為其他人的生命負責。
現實的例子,其實一大堆喔。或說,我們的生活就已經是默許這樣的規則了。只是太日常了,我們都忘了。將軍送士兵上前線是屬於這個模型;政府送醫護人員上疫情前線也是屬於這個模型,這個角色就是:
「陳時中 」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在疫情記者會上,無論記者是向陳時中,甚至是柯 P,問到:「既然打疫苗會造成一定程度的風險,為什麼還要鼓勵大眾去打疫苗」?他們以身為公衛專業為領導者的身份都會這樣回答:「必竟打了疫苗,死亡率還是會比較低」。
那麼打了疫苗死亡率比較低,就和選擇操縱操縱桿使得鐵軌上少死四個人是一樣的意思。陳時中並沒有因為講完這句話,馬上就被警察帶走。這符合人情現實,也符合四維模型。
也許很多人在這次病毒戰爭中失去了親人,身陷痛苦與悲傷。這些人恨透了陳時中,認為陳時中就是殺人兇手。這裡再補充強調,只有面對外部壓力他們有這樣的權利。以打疫苗為例,其實陳時中他們除了說明打疫苗死亡率比較低之外,其實他們更應該說,疫情領導者也都和我們一樣面臨病毒的威脅,和大家一樣面臨打疫苗副作用的風險;只是他們比別人更有能力而提出建議—這也是為什麼大家一直把「同島一命」掛嘴邊。若是純粹的內部壓力當然不行;或特定角色才會面臨的局部壓力轉稼給另一角色也不行(轉稼局部壓力即是屬於蔽惡)。
若看了我的答案,再跑回去看原來的電車難題,也許你會說:「既然電車災難的責任不在我,那麼我經過那裡,我的『位置』旁人無法取代,當我『操縱』完那根桿後的那一刻,我也躍升成問題的解決角色了。那麼我去動操縱桿讓人少死一點不應該也可以」?
問題其實就在:「你確定操縱完那操縱桿,真的有角色會躍升而出嗎」?
在電車問題裡,你有沒想過如果你動了操縱桿結果反而更糟怎麼辦?像這樣:

藤原拓海的雙軌甩尾
我想表達的是,縱操桿的結果若要是穩定的,它將會是團體共識下的結果才行。也就是,假若全世界只有你懂得如何操縱,那麼你會無罪,你會是英雄,你會躍升成為問題解決者(或是你本來也就是問題解決者跟本無需躍升)。這個在現實生活中一樣四處都充滿了案例:
這裡舉出了一個用自己身體做寄生蟲實驗的醫生—謝獻臣醫師。這樣偉大的醫生其實不算少數。他們之所以會選擇自身做實驗,就是要能夠先承受災難而獲得受難者的角色認同,才能進一步做決策。(文章來源)
但電車難題之所以會使用一個簡單的操作來表現問題,出題者更想表達的是說這個操縱是普遍的認知,誰都可以。因此,你無法躍升。
聞氫哥的電車難題
若解決問題的手段是普遍共識,也就直接將問題指向第二個衍生問題,當團體內部角色無分化時,內部的某個個體是否有選擇其他個體來承受災難的權利?
由於角色不分化,有外部壓力,我們採取「義」的準則。即能夠不自進。同時,動了操縱桿、減少人員死亡並不會躍升成獨立角色,所以一切都皆大歡喜。答完收工。
「等等,先生你別走,你還沒自殺呢」?!
這裡我還未提到的附帶條件,就是操桿者必須事後自殺。你說無理取鬧?團體範圍裡一共有七人,他們角色既無分化,也無角色躍升。那麼電車壓死一人後,再加上操桿者自殺後團體一共死亡兩人,團體死亡率從 5/7 下降到了 2/7,完全地策略正確。
還是不懂?你不是說角色無分化嗎?你也不想當英雄,那為什麼不能自殺?
既然這個事件中沒有人想當英雄,那麼你再反思我提出的勇者救公主的異世界轉生案例。你想像現身在這樣一個寫好的劇本中,與其說是討論道德,不如說你其實只想演上一段災難電影裡的主角,來突顯自己與眾不同,有著能思考道德的高尚人格。
如果故事是這樣的,災難發生了,你發現災難臨頭將要取走別人的性命,而你挺身而出犧牲了性命,擋下了災難,使得災難取走了較少的人命。那麼這個故事你無疑是英雄。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在於你自己承受了災難。我們想像外部災難是個連續的隨機事件,因此你隨時都有可能是選擇別人生命的人,或是被別人來選擇生命的人。當每個人都承受了相當的災難風險後,你才能落實真正的角色不分化。
或許在這樣的情境下,完全的功利主義是派得上用場的,只是這些哲學家公式列錯了。當你有權選擇別的個體承擔災難時,代表你自己也相同地承受了災難;這個情境無涉角色躍升,其實是屬於禮的範疇-「不踰節」:任何人都不能置身團體規則之外。這並非是說功利主義是對的,而是該情境必須遵守「比例」原則。今天如果全人類都覺得不去操縱操縱桿比較好,那麼當全體人類遇到同樣情境時都應當比照辦理。與較多或是較少的死亡率跟本毫無關係。
今天假設每個相同的電車難題情境,我們都選擇了讓較少的人犧牲。那麼每當情境發生,無論操縱桿旁的人或被綁在鐵軌上的人都是隨機發生(你有可能是操縱桿者也有可能是被綁的人),那麼個體的平均死亡機率是 1/7,無一例外。當你一生如果遇到七次電車難題,你就會死一次;但當你一生只有遇到一次時,就代表你得死 1/7 次。由於你無法只死 1/7 次,那就只能選擇來用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了。無論如何,你逃不掉那 1/7 次的死亡。
這裡有個網站(來源),收集了網路上腦洞大開的電車難題,但很多卻十分寫實。這張圖是我最喜歡的:

聞氫哥會告訴你的電車難題版本
什麼樣的教育讓大家都只喜歡當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來思考問題?只願意當主角,不願當承受災難的人。「雙重標準」—這是我們當今人的原罪。如果你不願意承受災難,那你當然沒有資格當主角,甚至成為團體的一員都不夠格。想想當災難發生的一瞬間,在你腦子裡的,到底會是挺身救人,還是賺取名譽?真正的難題,反而是去檢視自身是否能夠接受得起考驗。
結論
最後的結論是,無論角色有無分化,個體有選擇其他個體承擔災難的權利;但角色不分化的情況選擇者也必須一同犧牲性命。這是立基在所有個體都相同承受了災難。不過個體有「相同地承受災難」才能被視為團體範圍內的個體,同時外部壓力也才符合它的定義。因此這個但書是多餘的。
我們還推論出:「當一個角色未分化的團體面臨外部災難的時候,內部的某個個體在處理災難的過程中躍升成為獨立角色,也有選擇其他角色來承受災難的權利」
其實任何最佳的團體策略,都是策略在執行後,團體不會因此標準而自我毀滅。你的標準會被別人同樣視為標準;角色的標準也同樣會被相同角色的個體視為標準。如果你有權選擇別人犧牲的權力,別人也理所當然同樣擁有選擇我去犧牲的權力。
整個推論完全沒有透過自由和功利主義的思考方法出發,亦或於最終選邊站隊。我想,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其實都只是一個完整的道德體系下的片面思考模式,是一些人性的部份擷影。他們因為化約論而被抽取出來單獨論述,使得它們無法全面地處理真實的社會問題。而那些討論它們的哲學家,也許只是出於某種原因,用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撰寫他們賺人熱淚的詩作吧。
後記
想要寫這篇文章時,去網路收集了很多資料。這裡採用的版本來自維基百科,但這卻不是原始的版本。原始命題其實情境又不相同,類似如下:「一架飛機正在駕駛中,突然發現飛機即將要墜機,飛行員必須決定,要不要躲開一個比較多人居住的區域,讓飛機撞進一個比較少人居住的地方」。在這樣的問題之下,決策者是強迫在團體內的,也比較接近我整理過後的版本。但像飛機,電車這種人造物,在定義成外部災難上是有問題的,這是原始命題的困擾點。
這種災難來自於人造物的情況下,到底應該能否視為外部災難也是很技巧的事。原則上參考上面提到的鐵道系統,因為鐵道系統是國家的公共建設,因此當它發生災難時,所有關係人都既可能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那麼意義上與外部災難是相等的,只是稱呼為「外部災難」怪怪的。
也因此,技巧性的部份就在於,如果該人造物的受益者或受難者都固定是局部的,那就有待思考了。維基百科在提出原始問題時指出最早是在 1905 年就產生了該道德問題的問卷。然而 1905 年,鐵道很可能並稱不上是「公共建設」,也不是「所有人皆受益」。當時鐵道的普及度一定相較有限。很可能就有一群人既坐不起火車,同時還要忍受火車帶來的噪音、污染或任何的缺陷,那麼,這時再來討論電車難題,答案就會有變化。
很可能這即是一種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家討論社會公義的一種方法。鐵路的建設一直以國家基礎建設為名,佔用了公共的土地資源,同時也破壞了大自然。但事實上它的受益群眾卻是有限的。一但這些建設與公民利益發生衝突時—好比撞死人了,那麼它的公義性將會遭受到執疑。以十九世紀法國在清朝勢力範圍的所做所為,就能很好的說明這一狀況。當時被法國佔領的雲南省看似在工業化的國家手下開始建設鐵道與電報網,那麼是否當地就邁入了文明,進入了工業化了呢?跟本不是,法國人建的鐵路完全沒往大城市裡走,而是連結了法國自己人佔領的礦場。並且直通越南,與自己的海外殖民地接軌。
我們回頭來假設一輛正在駕駛,卻突然失控的火車即將撞到鐵軌上的人。一邊是五個法國人;另一頭是一位當地的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社會背景之下,也許我們應該選擇直接壓死法國人,因為當地的中國人們跟本從來都坐不起火車,也不曾享受過火車所帶來的益處,這時,他們對於火車失控跟本毫無責任。
總之,四維模型解釋道德問題,技巧就在於分析團體邊界、壓力方向與角色有無。電車難題無論有多少變化型,只要把握這個訣竅都能迎刃而解。
後記二
完成這篇文章後我自己其實還是會常回來重讀幾次,少不了不斷重新推演其中的邏輯,尋找是否有盲點。如今也已經過了好幾年,果然有盲點。噗!
文章裡我把情境分為兩個種類,主要以整個事件群體內部是否有角色分化為界定標準。但,其實我沒有把操桿人是否與被捆綁的人同為角色區分出來。也就是說雖然群體內部有角色分化,但操桿者和被捆綁者依然有角色區隔的可能性。而我在文章裡的論點也時不時將兩種情況混為一談。
比如我在描述謝獻臣醫師的行為時就出現了錯誤,他並不是先藉由自我試驗來「進入團體」(該句也已經更正),而應該是藉由此獲得「角色認同」。但這個認同是與受難者的角色認同。在新興疾病之下所謂原有的醫病劃分並不存在,只有受難者與一般群眾的劃分。因此謝醫師的行為是先成為受難者,接著在受難者的群體內他同時還是醫生的邏輯後續才成立。這是指決策者將與少數的被捆者成為相同角色;才能下達決策裁決誰應該犧牲。
團體裡有角色分化雖然符合軍隊上戰場,醫師上疫情前線的情境,但如果決策者與受難者的角色依然不同,並不符合上述的情境。文章裡把陳時中比做決策者,那麼前線醫生護士的角色是少數的受害者,一般民眾就是多數的受害者;但如果無論少數與多數的受害者都是一般民眾,那就變成了中共中央政府任意地決策地區的隔離政策與有先後順序地分配醫療資源。如果我讚同那樣的決定,那不變成我這篇文章在替中共洗地!?
少數與多數永遠都不會是選擇的條件之一。也就是它並非是個足以構建出角色的界定標準。少數者是否為角色關鍵是在於他們是否有「選擇」。士兵與醫護人員當他們任職於特定角色時,已經為他們將要面臨的風險做出了決定。意思既為如果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當場認聳,他至少有返回一般民眾的權力。但一般的民眾沒有,他無論要被犧牲與否都沒有選擇權,這是問題所在。而且這應該才是列車問題真正的癥結點。
因此,在四維模型下,就算群體內角色有分化,但該分化是屬於決策者與受難者之間的,那還是不算。該情境還是得依群體內角色無分化來處理。文章主體並無錯誤(已點出決策者與受害者皆為角色)。但因對情境羅列不夠完善,容易造成誤會。
這些時日該文也已經獲得了不少觀看數,也有不少人贊同。但如果因為我的描述不準確而造成困擾的話,我也深深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