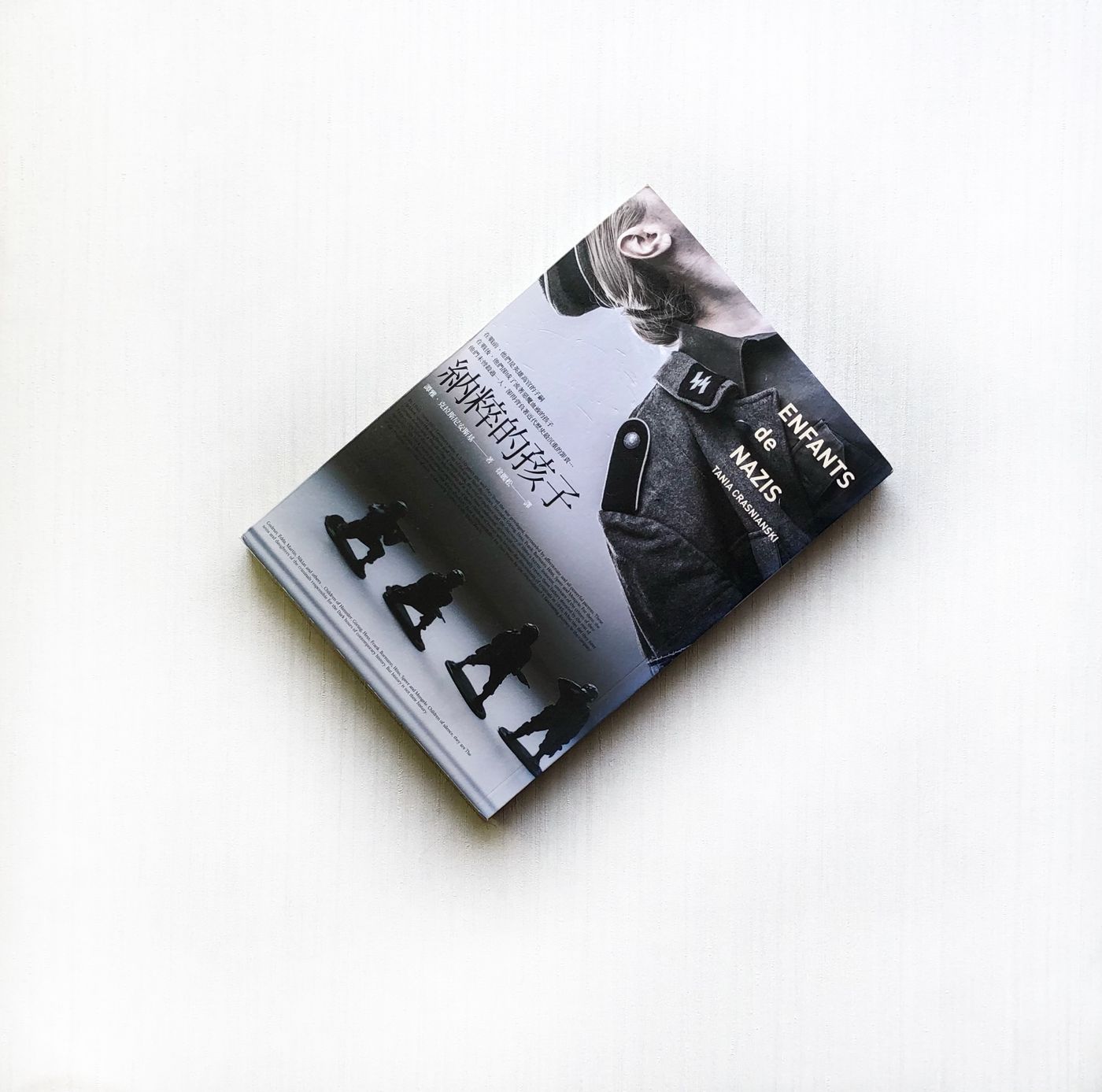近日每天都看到有關俄烏戰事的新聞,在眾多戰場故事中,除了烏克蘭人如何保家衛國,有另一類報導也引起了熱議:不想打仗的俄羅斯人民。有哭訴被騙上戰場的士兵、有找不到兒子的母親、也有單純渴望和平的人民。從這些報導中,我們會了解到戰爭的受害者或許不只被侵略國的人民;侵略國的人民也是在維持國家機器運作中被壓迫的一群。如此景況,令我想到約一年前上映的電影《波斯密語》﹙Persian Lessons,台譯《波斯語課》﹚。
注意:以下內容含有大量對《波斯密語》的劇透!!!

猶太人Gilles為了存活而對納粹軍人謊稱自己是波斯人,並在輾轉之下來到納粹中轉營軍官Klaus的手下,被迫要教導他波斯語。Gilles為了圓謊活命必須攪盡腦汁創造出他根本不懂的「波斯語」,就在即將無計可施之際,他從謄寫集中營囚犯姓名的工作中獲得靈感,將被害同胞的名字改為偽波斯語單詞,而故事就在這一節節的「波斯語」課堂中展開。
在我看來,兩位主角在電影中承擔了不同的「功能」。Gilles為了隱藏身份而和其他人鬥智鬥勇,是把觀眾帶入故事的主視角,也是掌握劇情節奏的角色;但Klaus,一個因為想出人頭地而加入軍隊的原草根階層,卻是導演更加用力去描繪的角色,也是我認為本作的核心 ——
他是平庸之惡中的「平庸」。

在電影作品中,這是個較為罕有的視角。「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由納粹大屠殺倖存的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1961年提出,並指出在實踐惡行成就極權的人之中,有很大部分其實只是唯命是從的普通人。但我們在電影中看過了很多納粹的「惡」,卻較少看到他們的「平庸」。

於是創作團隊創造了Klaus,一個雖然名義上是納粹長官,但實際上只是掌管後廚的廚師長。他畢生心願是到德黑蘭開餐廳,有着在戰場中不合時宜的浪漫和平靜。在片中你不會看到他殺人,只會看到他擬定菜單、檢查廚房、甚至還在閒暇時以「波斯語」寫了一首詩。而支線劇情中,還有更多德國軍官之間的複雜感情線,甚麼兩女爭一男啊、為了上位散播流言啊、向長官打小報告啊,甚至他們之間開的黃色玩笑還成了片中舒緩氣氛的節點,惹得戲院中一片竊笑。
「納粹」一直是代表極權種族主義的符號。但這一次,組成這個符號的人被賦予了臉孔 —— 他們會追求虛榮和地位,會到郊外野餐和唱歌,有浪漫也有七情六慾。原來,在成就極權的磚瓦中,有那麼多和你我一樣的隨波逐流的普通人。
到這裏的話,我們也只能說《波斯密語》展現了納粹的人性面孔,但絕對稱不上「被壓迫」吧?
關於這一點,必須深入去看Klaus這個角色。從片中幾個刻意描繪的細節,比如他對本應是戰俘的Gilles的偏愛、特意學習波斯語的「我愛你」、還有想撫摸Gilles的頭卻又不敢實際行動的猶豫,不難發現劇情中處處營造着兩位主角間的浪漫張力。同時,Klaus和上尉的對話中那位「兄弟﹙brother﹚」也提供了更多指向同性戀的線索。先是上尉指出調查資料顯示Klaus根本沒有兄弟,同時也評價這位「兄弟」在戰前就離開德國去了德黑蘭的行為「不是愛國的行為」。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Klaus略顯緊張地解釋,最後更以屬下間的八卦來轉移話題,突出一個作賊心虛。
從其他片段得知,Klaus的「兄弟」是因為不認同納粹政權的某些行為而選擇離開母國。這指的或許不只其種族滅絕計劃,還有對國內同性戀的迫害。自十八世紀德意志帝國時期起,德國一直有一條歧視同性戀的律例「刑法第一七五條」,把男性之間的性行為定為刑事罪行。而在1935年,納粹政府更將該條例所適用的範圍擴大及加重刑罰,因為建立納粹帝國的必須是「純種德國人」,即希特勒認為的最優越人種「雅利安人﹙Aryan﹚」,而不能生育後代的同性戀被視為是一種種族威脅。在修例後,任何有同性戀意圖或想法的人都可能會被逮捕並送往集中營。

也因此,劇中的Klaus大部分時間都在訴說他在戰後前往德黑蘭開餐廳的夢想—— 他嚮往的不是納粹的帝國夢,而是失去的愛情。在電影最後,納粹即將倒台之際,他第一時間選擇的是前往德黑蘭,並在和Gilles分別之際露出了真心的笑容。我們可以想像,有着同性性取向的他是如何一邊享受着納粹長官的身份,一邊戰戰兢兢地隱藏着最真實的自我。當看着窗外被鞭打虐待的戰俘、看着那一車車送往集中營的猶太人,他的內心深處是否也有一絲被納粹政權逼迫的兔死狐悲之感?
這是我認為《波斯密語》的劇本設計最出彩的地方。兩位主角一明﹙猶太人﹚一暗﹙同性戀﹚,其實都是在國家機器的壓迫下苟且偷生的人,都在訴說極權之下隱藏的自我。而導演對後者的塑造甚至比前者更多,使得Klaus的人物形象極為立體,令不少觀眾都大嘆可惜:「如果他們可以成為真正的朋友就好了」。
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前兩部分所說,本片花費了大量筆墨去塑造Klaus的平庸之處,使他乍看就如個普通廚師般無害。如此一來,不免令很多觀眾對結局感到遺憾,甚至有聲音質疑創作團隊在「洗白納粹」。這邊要為他們平反一下 —— 人家剪輯時已經三不五時插入一些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空鏡來提醒你們在這個看似歲月靜好的中轉營背後的悲劇了,要get到導演的用心良苦啊!

兩位立場衝突的主角真正的對峙在電影末段:Gilles親眼目睹中轉營中一位同胞的犧牲,也許是為了報恩、也許是已經堅持不住了,他決定頂替死去的同胞的弟弟前往集中營,接受死亡的命運。發現此事的Klaus在路上截下他並強迫他跟自己回去,兩人貢獻了本片中最有張力的一段對話交鋒:
「你要和這群無名之輩一起去死嗎?」
「他們有名字,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這些人並不比你差,至少他們不是殺人犯。」
「我沒有殺人。」
「是,你沒有。」「你只是做飯給他們吃罷了。」
這是一個受害者對加害者的控訴,也是創作者對「平庸之惡」的批判。Klaus的平凡、內心對納粹的惡行毫無共感、以至那種「我只是想做好我的工作」的心態,完全對應了漢娜・鄂蘭描繪的平庸之惡。要說同類型探討「納粹幫凶」的電影,2008年的《讀愛》算是較為人熟知的一部;但其著墨較重的感情線很容易覆蓋掉對平庸之惡的探討。而在《波斯密語》中,兩位主角的命運對比之下更容易使觀眾感受到「平庸之惡」有多麼平庸,而背後又有多麼悲慘的「惡」。
Klaus在最後得到了該有的懲罰。
他或許只是一個錯上賊船的普通人,但任何人在放棄對正義和人權的思考,選擇成為極權的螺絲釘那刻起,就必須承擔這份共業。
以上是我對《波斯密語》的一些分析 —— 我給予其構想很高評分,但可惜整部電影為了突顯「平庸」的部分而穿插了太多支線,又缺乏對一眾配角更深刻的描寫,反而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既不是群像戲又不完全是主角劇,有點可惜了主線這麼好的創意。
本片由俄羅斯、德國和白俄羅斯聯合發行,導演瓦迪姆·佩爾曼﹙Vadim Perelman﹚是烏克蘭人,整個作品就像是一部經歷過二戰時期的各國歐洲人民所創作的反思電影。然而,如今他們的祖國一些成了侵略國、一些成了受害國;時隔半世紀,人們依然被國家機器迫害,不得不說實在十分諷刺。
願我們都不要成為那麻木的平庸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