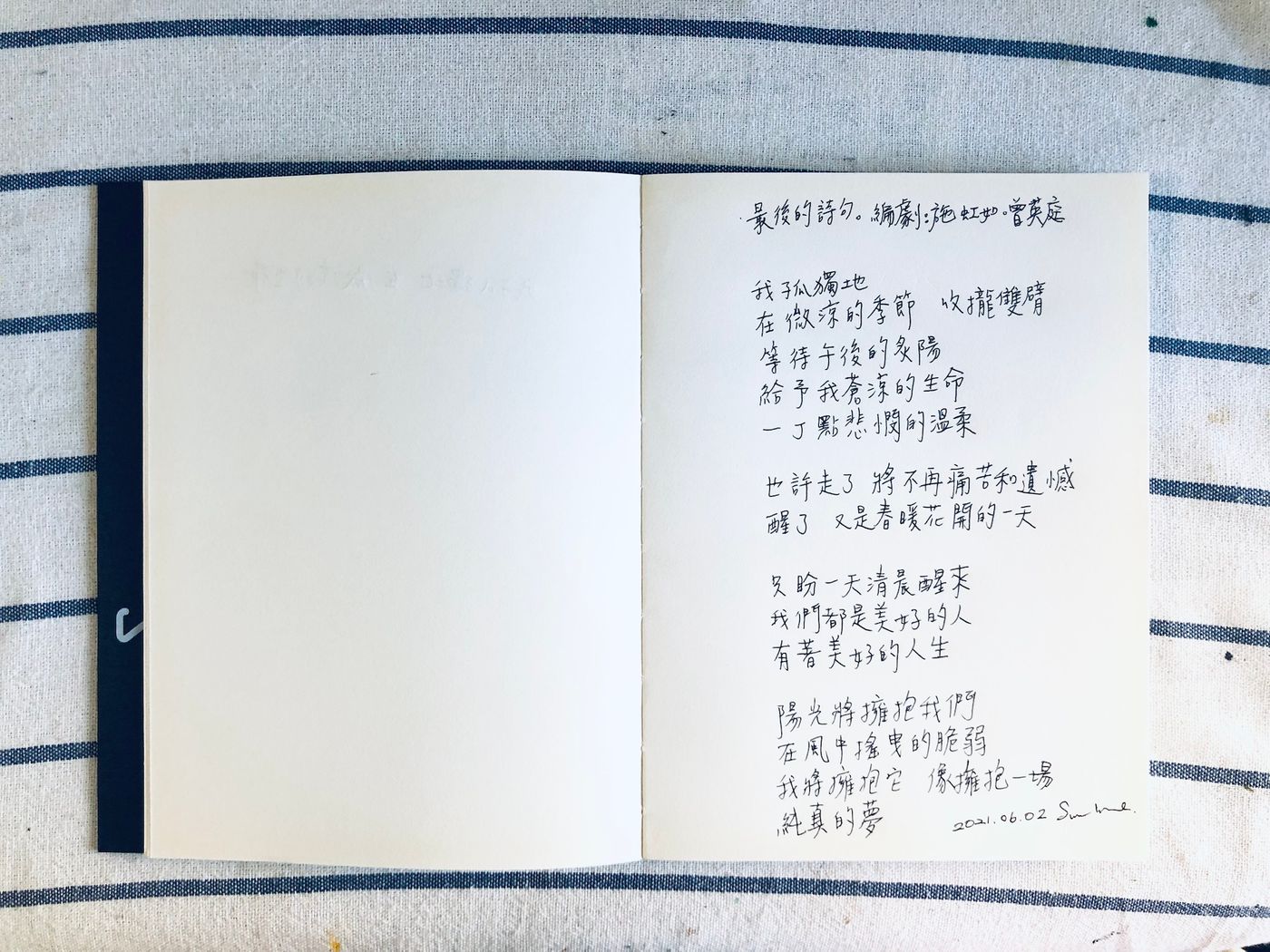「在富於詩意的夢幻想像中,周遭的生活是多麼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韓波
小說傳記式地敘寫詩人的一生,在二戰後共產革命浩浩蕩蕩的捷克,從出生至死亡,對於「他方生活」的不停追逐。
我想試著摘要劇情,但這對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好像很困難,它的精彩之處在於描述情感思想的細膩精準,和突然冒出來又長到頭昏眼花的哲學論述。不過幾個重要人物的介紹好像就能囊括重要的情節了。
主角雅羅米爾五歲便展現寫詩的天賦,很年輕的時候便自詡為詩人,終其一生以此為傲。他對於生命、愛情都懷抱崇高的理想,也受到革命的吸引,成為社會主義的忠誠擁護者。最後,他為政治服務的詩句在宴會中遭人羞辱,雅羅米爾意圖自殺不成,沒多久便得重病而死。詩人的母親獨力撫養他長大,和孩子有著深切的連結,在孩子長大後甚至化為病態的,會阻礙他的交往關係的佔有欲。(雖然沒有想在心得聊這個,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大概是我心裡數一數二精彩的部分!)
畫家在詩人很小的時候指出他的天賦,他是詩人很長一段時間的老師,也和詩人的母親有過一段不倫關係。他曾是詩人亟欲尋求認可的典範,也在詩人投身革命後,成為他所批鬥貶低的對象。(精神分析+《霸王別姬》的既視感)
幾次感情失利後,紅髮女孩成為詩人真正的愛人。她醜陋、庸俗,卻偶然得到詩人渴望已久的初夜,從此詩人決定以生命的重量愛著她。一日她決心告別長久的炮友(他們或許有著更複雜的精神關係但原諒我粗暴簡稱),專心致志愛著詩人,詩人卻因為她的約會遲到發怒,她謊稱自己是向即將判逃的哥哥送行,被詩人告發。三年後出獄,詩人也早已長眠地下。
詩:寫詩的人都是上帝的選民
無法定型的世界一旦封閉在一首有格律的詩裡,就會在突然之間變得明朗、規律、清楚、美好。在一首詩裡,如果死亡這個詞所在之處恰恰是前一行詩迴盪著鈴鐺聲響的地方,死亡就會變成一個有秩序而且旋律悠揚的元素。
之於詩人,詩在不同階段有著各異的意義。很小的時候,他就發現自己能說出引人側目的話,為了贏得關注和讚賞,開始產出越來越多的詩句。當他真正出於洶湧的情感寫詩,而察覺了詩文的力量──獨立於作者和現實之外、將經驗美化昇華、創造夢想的第二生命──詩成為了「生活之上」的,高貴而有序的精神世界。
投身革命後,詩句一度成為被塗在牆上的標語,隨即又被更直接粗暴的口號取代,詩人也不怎麼寫詩了。直到和紅髮女孩相戀,那些俗濫卻溫暖美好的字詞、韻律重回他的腦海。詩歌和革命成了一體,都是重構新世界的管道,他重拾詩句歌頌起了社會主義。
但每當詩人重遇那已經成家、身為警察的老同學,總要感嘆:你那裡才是真實的生活。這時,詩歌的世界就成了鏡子之屋,詩人被恆久禁錮在自己的映像裡,他渴望真實熱烈的感情,在耳邊炸裂的槍響,可他只會寫詩。
我認為詩歌也是一種「他方」。它曾是詩人熱切追求,藉以逃脫現實的空間。看似和可見可觸碰的、高度影響社會的革命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兩者創造的高度理想化世界,對現實的變形\對舊時代的全盤否定又高度相似。詩是比較柔和、比較個人、也比較拒絕失敗的那種革命,是天真的堡壘,個人信仰的自憐自珍。
文末是弗朗索瓦.希加的書評,他認為這是對詩歌的嘲弄。又或許這是對詩歌的哀悼,傷憐它淪為個人彰顯自我的媒介、政治的武器,失卻了藝術的純粹。但到頭來,藝術真的是追求著存在的至善標準嗎?每個優秀的詩人是否也都只是另一個現實逃犯而已?
生活:肉體即生即逝而思想永恆
如果死是必然的,讓我與你同去,吾愛,就在火焰裡,化為光與熱……
在我讀來,詩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為了生命的光輝服務。
詩歌是如此。當畫家告訴他:意象是隨機流淌的潛意識,只是隨機選中一人被發表,詩人仍為自己「被選擇」而感到驕傲。對於藝術,他沒有堅定的信念,只要能被看見,必要時它能是政治宣傳,也能死去。
愛情是如此。年幼時他著迷於詩句裡的而非真正的女體,喜歡「被裸體映照的臉」而不是裸體,他要那些標章般的,能妝點生命的高貴象徵。他為紅髮女孩的所有缺陷羞恥,卻聲稱自己深愛這些缺陷,好耽溺在自己的偉大愛情裡,轉身就能為了更偉大的革命理想將之出賣。
死亡是如此。他很早就在詩裡書寫死亡,但這不是思想早熟的表現,詩人只想在渺小、平淡的生活裡增添一點巨大而深刻的東西。(走過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年紀後好有共鳴)「在火焰裡死亡」的詩句重複了好多次,死亡在他心中也是一則訊息的展演;他要壯烈,成為熾熱亮眼的火炬,不要無聲無息地沉入水中。
很存在主義,實際上發生的一切都是偶然與無意義。詩人自認的大義滅親、紅髮女孩的三年牢獄、哥哥的下落不明,都只因為一個隨口的小謊;母親深愛的詩人是在不確定的地方受孕的,他終究因為肺炎而不是任何崇高的理由死亡。如同作者對詩的描述:「一切被肯定的事都會變成真理……詩人無須證明什麼;唯一的證據在於他情感的強度。」
意義只源於人的創造與詮釋,我曾覺得這樣的存在主義很有力量,卻在旁觀人物一生的自我催眠後顯得好虛無。你說什麼便是什麼,那麼輕易的「是」也能那麼輕易就「不是」。我們會終其一生奮鬥,掙扎犧牲堅持感動,都只為了一個自以為如此的信仰或價值。沒有人知道任一個行為對世界真正的影響,不想走進全盤的虛無,我們就只能活在自己可能同樣毫無意義的解釋裡。
他方:夢就是現實
夢就是現實,學生們如是寫在牆上,但是看起來似乎要反過來說才是真的:這個現實(街壘、砍斷的樹、紅色的旗子),就是夢。
我是被書名吸引的,簡短美妙的五個字,又好精準切合我的心理狀態。真實的生活總是在他方,我常下意識把當下的階段視為過渡,日常視為不完全甘願又必要的任務,底下潛藏的是對未來、另一種生活的想望;完成前者是為了向後者追逐,到手之後又成了乏味的日常。比如硬是要在不完文本的週間撥半天讀書寫作,這裡是我此時此刻的他方……
詩歌革命性愛,而書裡是這樣的。青春要展望遠方與未來,因為總還會有一種更美好理想的生活。即使它更像夢,我們總要相信那才是真實的,是我們生在世上注定要追逐擁抱的。
它永遠更好,所以應當永遠在生活的彼端,永遠不可及。書中有一段敘述各個詩人都曾在城市間輾轉流徙,都在跑,向著永遠不會抵達的他方。他方不是終點或崇高堅定的理想,他方只是他方,只是為了青春的熱烈而存在。生命需要那點火光照亮前進的路,於是我們任意創造,任意變動,它便可以在到不了的地方恆久不熄。
是不是更虛無了?即使是只在自己的詮釋裡有意義的理想,也沒有觸碰到的一天喔。
(我好不擅長解釋這種虛無感,真是抱歉。)
革命與時代:青春是投入未來而不往後看
我不是右翼也不是左翼,我是小說家。
人們說到米蘭昆德拉,總是不會忽略他書寫的時代背景。布拉格之春。蘇聯高壓統治的捷克。學生們的他方是共產黨革命,不是全有就是全無的那種天真蠻橫。
但我還是不會覺得這是「對共產黨的嚴厲批判」。學生揮舞著大旗,無關上頭的口號,重要的是那面大旗。詩人甚至沒體驗過無產階級的苦,他要的是激昂熱烈,是有血和抗爭的光彩生命。革命是任意的他方生活。
小說反映時代,可時代掏選出的是人性,時代本身亦是群眾集體的產物。我沒有否定革命或高壓統治造成的傷害,只是覺得作者著墨的重點不在此──政治口號是絕對的,威權的迫害是直觀的,但推動這一切發生的複雜人性大概更值得被如此精細地討論。望進歷史的切片裡,每個人都可能有好多身分和故事,他們都是宿命和個人意志交織的結果,可以高尚又自利,獨特又那麼一致,終滾成轟轟烈烈的時代巨輪。
不是共產黨便是別的,也許人總會致力於把自己的生命寫成史詩。那麼暴動也不過是比較戲劇化的一種人性映射了。
書末評論
昆德拉作品的顛覆性是簡單的、柔緩的、潛伏的,然而卻是徹底的、毫不留情的。
真的好喜歡書末的這篇評論,很精準地描述了我第一次閱讀米蘭昆德拉的感覺。記得闔上《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傍晚,一愣一愣地,踩著因為久坐而虛浮的腳步離開圖書館,不太確定自己看懂了什麼。可那句話卻在往後幾天不時浮現、膨脹:「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像從未發生過……」
說是完全因為一部小說也太誇張,但它當時也成了加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還真的過了一段提不起勁的,不太確定什麼值得追求的日子。
但或許米蘭昆德拉並不虛無。我不知道,依然不確定自己真正看懂了多少。也許他認為為了認定的理想奮鬥的生命是珍貴可敬的。報章評論或網路書店簡介永遠都說名作家「記載人性的光輝」,也不知道是我讀不懂,還是他們都在複製貼上。
總之,這些文字仍然是緩慢流過身上的一條河,也許仍有感覺在一點一滴滲入。如同讀完後又翻了幾篇書評,仰頭靠著椅背逐漸不想動彈。我說不清楚,很多應該要是思想的仍停留在感受的層次,也許又會在一點時間後想通什麼,我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