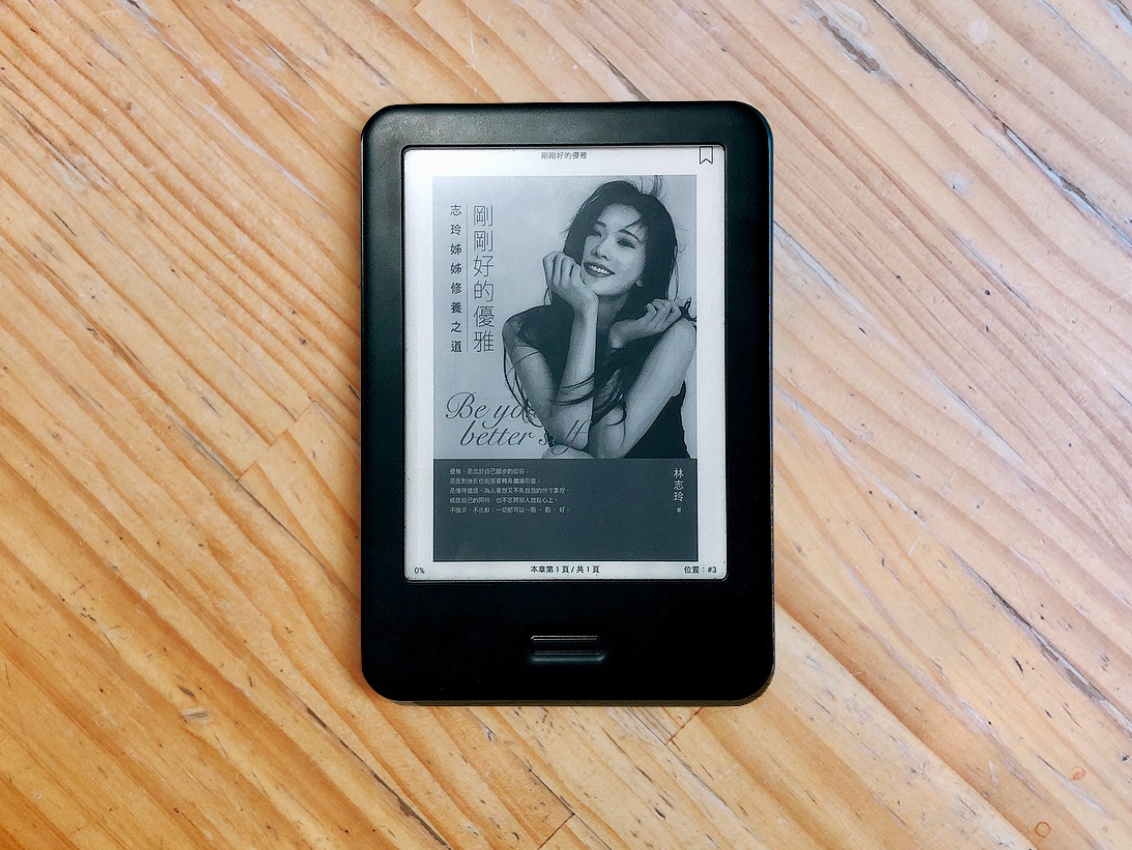《剛果廣場上的人們沒戴腳鐐》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在Sidney Bechet的自傳 "Treat It Gentle" 裡,他回憶自己所知的父祖輩生活時,提到一位叫做Omar的,在「剛果廣場」演奏打擊樂器的人。
「⋯週日的時候,奴隸們會聚集在一起,那是他們的自由日,他(Omar)會在那個稱之為剛果廣場的地方,開始在鼓上敲擊出節奏, 大家等待著他然後才開始跳舞以及吼叫⋯」
多虧了像這樣的口傳歷史,讓我們能藉此想像百年多前,這些非裔美國人音樂活動的精彩,與他們日常勞動生活的苦悶,有如何巨大的落差。
⋯你甚至可以說,只有在剛果廣場的他們,才是真正的活著。
只有在那裡,他們才真正掙脫了奴隸的束縛,掙脫了腳鐐—肉體上,以及精神上的。
離開了剛果廣場,他們仍然呼吸,仍然進食、睡眠,以及日復一日的勞動。
但他們很清楚:自己的靈魂,在離開剛果廣場的時候,就已經隨之死去。
經歷這樣的死與復活,或許就是那些歷史學家講的,在剛果廣場上進行的這些音樂與舞蹈,活脫脫的就是一種儀式:這些音樂與舞蹈,像是在他們靈魂的暗夜點燃火炬,同時也像在對他們的先祖招魂,讓他們可以跟自己的文化與傳統重新接續。
當我們觀看這樣的樂舞,或許我們在觀看的,其實是一個自由靈魂的樣貌——讓身體與性靈都從壓迫與監控中被釋放出來,回歸到自己的本然,感覺自己真的「活著」。
人生而自由,這在當代好像是種常識,我們也會自認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時代...我們看似能夠決定自己的生活,能夠為自己做很多的決定⋯然而,我們真正自由了嗎?
我們不再戴著腳鐐,但我們的靈魂也自由了嗎?
當我們演奏的時候,我們是否只是在換個地方考試⋯只是為了在舞台上,向大家證明:「嘿,你看!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吹對!」⋯只是為了另外找個領域,來證明我們比別人更好,更有價值,更有資格活著...?
我們把腳鐐帶上了舞台。
我們是試著透過演奏證明這些嗎⋯我們想在演奏上做到的,不過是如此而已嗎?還是當我們聽到像爵士或搖滾這樣的音樂時,有其他更深刻的事物,觸動了我們。
是那樣的一種深刻,讓音樂裡的一切都散發著光芒⋯如果少了它,我們在音樂上所追求的「正確」是為了什麼呢?
今日,剛果廣場延續著百年前的週日慶典。而當年在剛果廣場上舞動的靈魂,其實並未死去 ——他們化成樂音,在一代代音樂家的演奏中復活,為我們點亮靈魂的暗夜,也為我們展現:一個自由的靈魂,真正的樣貌。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