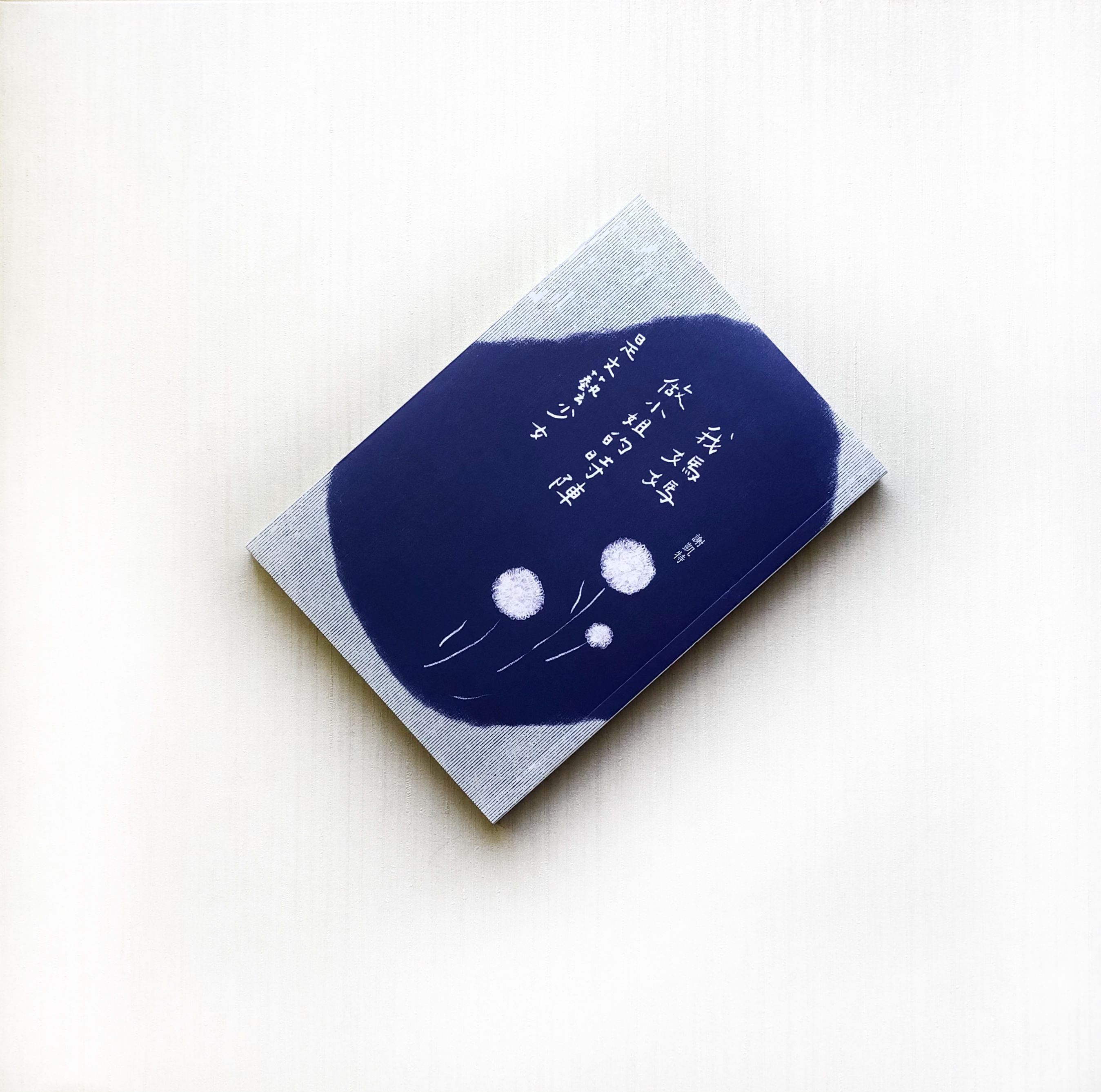母親過世幾週後,我有個接受新聞雜誌《明鏡週刊》訪問的機會,以下便是我與訪問者艾兒可‧許密特(Elke Schmitter)及菲利浦‧歐姆克(Philipp Oehmke)的對話,這段對談一直糾纏著我直到寫了本書為止:
明鏡週刊:您說您的母親終身致力於找尋方法,揭開他人的創傷,但自己卻不知該如何與兒子談論自己的創傷?
馬丁‧米勒:我試過無數次與她對談,就像您現在和我這樣,但卻踢到了鐵板,所以關於您題問,我無法進一步給您其他解釋,我不只是她的兒子,我也是心理治療師,也就是一個讀過傳記並深入分析的人,但是我並未滲透入其中,大家總有一天會接受這點的,這層阻礙也讓我在過去的三十年來無法接近我母親,我必須承認。明鏡週刊:您母親創造了一份獨一無二的作品,此作品裡說到:精神分析無助於精神創傷,但有另一個解除童年壓抑與重獲新生的獨特方法──我將試著向你們展示之。我們現在認為,在我們彼此對談了十分鐘後,您母親隻字未提她作品中任何一個自己人生歷程裡的重點,她無法將自己的方法使用在自己人生最巨大的創傷上。
馬丁‧米勒:即使她在她的著作中正確地看到了那麼多的事物。我的悲哀是,我這個戰後世代所生的小孩沒辦法與我的父母建立起一段情感關係。
明鏡週刊:請您幫助我們:關係喪失不正是您母親所譴責的、父母的殘酷與畸形的原因嗎?
當時的我作夢也想不到要寫一本關於我母親的書,她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到無法描寫的人。直到二0一0年的秋天,我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向一位美國出版業者介紹了她的作品,我才開始認真思考這件事。那位出版商認為,對我以及我母親的讀者來說,寫一本有關她的書將會大大有益。這段話縈繞在我心頭,引起我非常矛盾的感受,起初我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拒絕,認為寫一本書的念頭極為荒謬,然而即便情感上出現了劇烈的抗拒,此念頭卻揮之不去,我勉為其難地決定接下這個困難的計畫。
第一個問題是──我對我母親所知甚少,愛麗絲‧米勒──我在這本關於我母親的書裡,將常常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把她的人生歷程都封鎖了起來,將她的私人生活變成了一個被守護得嚴嚴實實的祕密,尤其是戰爭那幾年,她特別守口如瓶。誠如眾人所知,我母親是二戰時期在華沙存活下來的猶太人,但實際上她幾乎不曾提及那段日子,最多只是委婉地帶過或使用很有距離感的說詞描述之,就連對我她也鮮少提起,直到我四十一歲才獲知一二。我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所有與猶太人有關的,以及所有與波蘭有關的事物,都與我隔離得遠遠的,我既沒學過父母的母語波蘭文,也沒人教我任何猶太文化,我宛如文化工藝品般地長大,被當成瑞士人來養育,瑞士對我父母來說基本上是個很陌生的國家。我體現了所謂的倖存後的新開始,就像倖存者身上常可見的那樣。這是其一。
也就是說,我對這些實情所知甚少,但我卻對我那從未被議題化的母親痛苦領會甚多,這是現在的我在做了寫這本書所需的調查研究之後所了解到的事。從有關大屠殺倖存者所生之子的研究,我們得知這些孩子都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關注,他們必須代替在那段苦難時期所或缺的情感對象,因此孩子們成了父母的依靠與存在基礎。人們稱這種過程,也就是親子關係的反轉,為:親職化,即因創傷侵擾而感到痛苦的父母透過自己的孩子去追回情感上的支撐,就像我母親在她的第一本著作《幸福童年的祕密》裡強調的:孩子擁有一種非凡的天賦,他們能出色地領會父母的需求,即便父母未曾吐露。他們完全了解父母所期待的是什麼,並且表現出相應的行為反應,這也是我曾經做過的事。
我與母親的關係──我如今終於了解了──有著那種扭曲關係的所有特點,包括轉遞被壓抑的迫害創傷,也就是說,我母親和我以某種精神官能症的方式而非常接近彼此,我們由於一種從屬的親近而擁有緊密的連繫。透過這種方式,我在情感上成為了我母親大屠殺經歷的一部分──而我當然一無所知,無論是小時候還是長大後。我成了見證者,是的,是戰爭創傷的一部分,卻渾然不知當初究竟發生過什麼。我成了一段苦痛史的參與者,儘管或者正是因為我對這段過去並不了解。我可以說是經歷了母親受到的納粹迫害,也就是這種盲目迫害的後果。
德國作家暨時事評論家亨里克・布羅德(Henryk Broder,1946年生)在一九八二年鄂爾文・萊瑟(Erwin Leiser)的電影《劫後餘生》(Leben nach dem Überleben)裡是這麼描述大屠殺倖存者所生之子的命運:「我一直覺得自己彷彿被束縛在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看不到的,但卻使我深受重負的驚恐座標系裡,我無法與之對抗。」我又在這幾句話中看到了自己。
我記得以前我們去蘇黎士拜訪親戚時,我在他們家裡看到了一些我不認識的東西,餐櫃上的木頭人偶有種神奇魅力吸引了我,那是正統猶太教男性塑像,旁邊還有一座光明節燭台。然而我卻完全不敢去詢問所有這些東西的意義,那未曾說出的禁問完全發揮了作用,即使長大成人,我還是一再地面對母親的恐懼,她很害怕被別人知道她的私事,直到她過世為止,她都小心謹慎地留心著不要讓任何私事公諸於世。
直到先前提過的《明鏡週刊》訪問以及美國出版業者的建議,我對母親的這種絕對服從才開始不斷動搖。
即便滿腹罪惡感,我還是認為,相較於進一步向母親的讀者隱瞞她人生經歷究竟正確與否的問題,對我來說,我自己究竟敢不敢探究自己的故事、是否有勇氣去揭露我的人生根源,反而才是更重要的。
我當然讀過我母親的著作,在《拆除沉默之牆》(Abbruch der Schweigemauer, 1990)裡,愛麗絲‧米勒建議所有讀者揭開自己的真相、自己的故事,並解除壓抑。我現在認為,即便我長年讓自己做心理治療,而且也擁有幾十年心理治療師的工作經驗,針對這樣的案例,要去克服的不只一座沉默之牆,還有一座巨大的罪惡感之牆。
在這樣的情感狀態下,我開始著手撰寫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有許多早已被遺忘的記憶浮現而出,而且我真的認為自己能描繪出母親的人生。直到和我的編輯艾娃瑪莉亞‧波勒(Evamaria Bohle)討論時,我才意識到自己陷入了角色混淆之中,我主要是以我的情感體驗來刻畫母親,母親傳遞給我的價值觀瀰漫在「事實」當中。
我再一次從頭開始,拜訪了時代的見證者,我母親仍在世的親戚──她在美國的表親伊蘭卡(Irenka)與阿菈(Ala),我開啟了一個奇妙、有趣且至今都未知的世界,那是我母親在戰前成長的世界,這個世界被二戰與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殘暴地摧毀了。如今我相信,愛麗絲‧米勒之所以無法成為我的慈母,其原因就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那段迫害歲月緊緊包裹住的創傷之中。我現在非常驚訝,母親在其著作《教育為始》(Am Anfang war Erziehung, 1980)裡那麼客觀地描述希特勒的童年,是如何做到的。最讓我感到荒謬的,是在大眾的感受以及對我母親這本書的批評當中,一再出現低估了希特勒所作所為的譴責聲。人們再無法以更好的方式隱藏、壓抑自己的過去。

【購買本書】
博客來
學思行
金石堂
心靈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