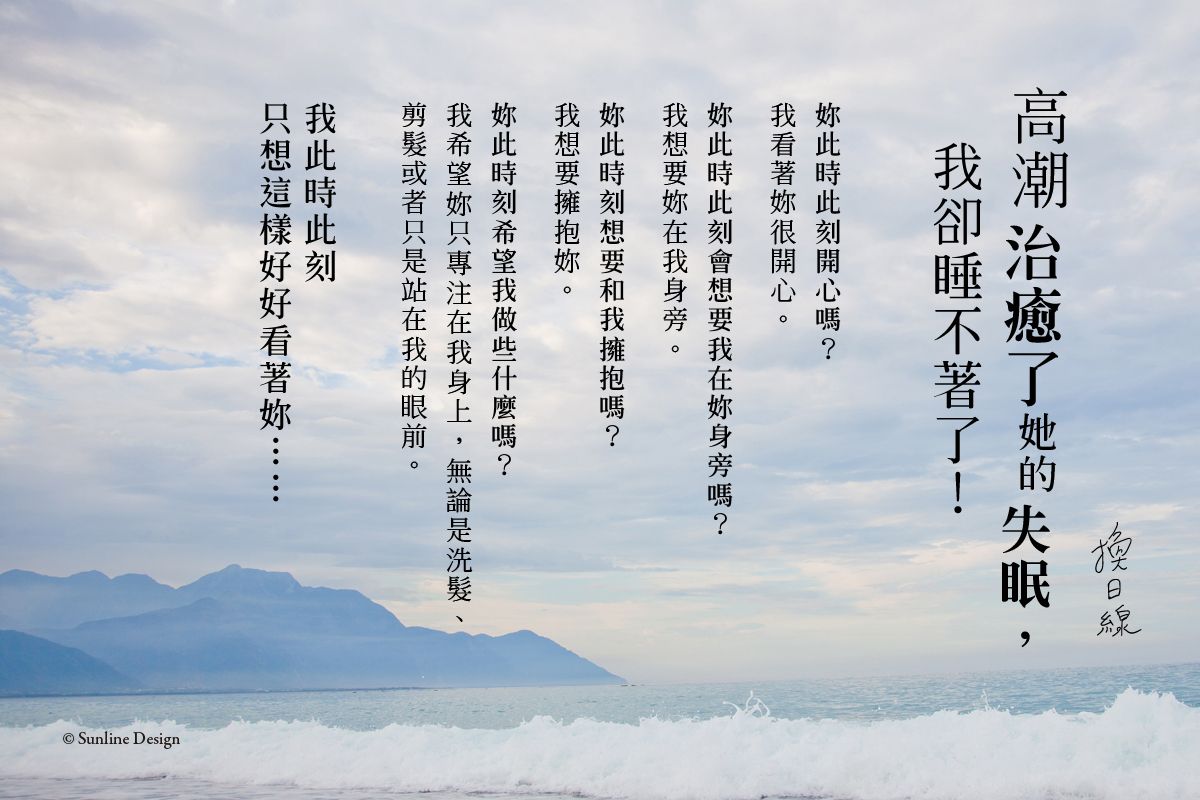「但我知道現在過這般生活的代價。」牧又話題一轉。「我知道這樣換著一個又一個的一夜情對像,我就不能期待我三十五歲的時候,會有和我牽著手在風雨裡散步的人,會有一起下班後疲憊地邊吃著消夜邊互相打氣的人。」
沒有想到,牧會是我實踐寫作慾念時,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的人物。
我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時間獨處,或者說,我努力為獨處騰出足夠寬敞的空間。長期練習下,獨處可以不限於身處於空無一人的房間,其精華是在身體週遭設立屏障,如魔杖輕輕向空氣一撥,即成功建立對外的保護網,可以開啟對自己的私密對話,包含日常生活的反省覆盤,情感的探索,人生盼望的梳理。哎就像小時候使用奇摩即時通,綠燈亮起,外在的我上線了,開啟與內在的我的聯繫通道。
我在獨處時想這一路上遇到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曾經的戀人們,思考如何描繪他們的一言一行,如何用最精準的筆法勾勒他們的神韻輪廓。精準,要更精準。我不只要質樸的筆法,我要高解析度的拍攝,但是這個角度無論如何是我精挑細選的,為他們挑選日常經典的瞬間,足夠代表整體的片段。
篩選是寫作最大的技藝,是一個人美感的彰顯,這與是不是能創造個好故事無關,嘿我是願意寫爛故事的寫作者,只要它足夠美。
我對自己說了好多人的故事,牧未曾列於其中,但當我坐在電腦桌前時,牧的身影卻浮現在我的腦袋中。
不,他不是我生命中可列為重要的人,他在我腦袋中的動態畫面,可能連湊個三分鐘的影片都不齊全。但我們相處之中我曾感受到嗡嗡作響的剎那,我曾感受到連結、共感,我們擁有不盡相同的生命,但有些核心品質是相似的,如果拿星體來比喻,我們可能有共同的土質或礦石。換個方式說,他身上有我定義是美的東西。
牧是朋友的朋友,一次共同聚會上打過招呼,當時沒有開啟對話。從共同朋友那聽來,他在父親開立的中小企業任職,是個認真打拼的第二代。那是一個男同性戀朋友辦的聚會,猜測高高壯壯的他可能也是相同的性向吧,別無他想。
幾個月後的某天,我在下班的台北捷運上碰到他。如果是我先看到他,恐怕會假裝沒瞧見,或點個頭後便移動往別的車廂的位置,但我們碰面時我已經先坐下了,他喊了我的名字,逕自坐到我身邊。牧當天穿白色圓領T-shirt,卡其色短褲,露出精壯的手臂,是個熱衷於健身的人呢,我想。
「我下週要去泰國。」牧說。他邊說邊打開手機示意給我看,「我先把交友軟體的地點改到泰國了,這樣我可以先安排好每天要見面的人,下飛機後嘿嘿,就可以開始見這些網友了。」
「你有跟義大利人交往過嗎?」牧冷不防問。「沒有,你有嗎?」「有呀,妳人生應該交一個義大利人的男友試試看。我認識的這個義大利人呀是個廚師,之前待在英國的米其林餐廳,現在在香港。他之前來台灣時就會來住我這煮飯給我吃,真的很棒。」「他年紀比我大上一輪,思想很成熟的,身體也練得很精實,但就是稍微矮了一點哈哈哈。」
「你們還有聯絡嗎?」「當然呀我們有空還是會微信聯絡,我三年前在香港念研究所時認識他,後來一直都有連絡,他每次研發什麼新菜色,便嚷嚷要做給我吃。」
牧仍把手機亮在我面前,滑著一張又一張新鮮臉孔。當然,因為他更換了所在地點,一路的大頭圖像都是東南亞臉孔,在滑過幾張裸露上半身的男體照後,開始也有女生的照片。
「咦,怎麼也有女生的照片?」我問。牧哈哈大笑:「哦女生我也可以呀。」「女生的話,我喜歡屁股大的,才有存在感。」
牧的目的地站到了,牧親密地拍拍我的肩,說聲下次再聊,轉身離開。
兩週後,牧傳了訊息給我,說是從共同朋友取得我的聯絡方式,想約個時間找我吃飯。我至今仍不能理解他主動啟動邀約背後的起心動念。我們不是彼此的食物,我們都心知肚明。
這次,牧先是快速分享精彩的泰國之旅的精華。根本是獵豔之旅吧,我邊聽邊想。喝得酩酊大醉的酒吧,內行人才會知道的同志咖啡廳,進去有興趣的眼神一勾便一同離開了。少不了的陽光,還有好吃的食物。牧把話鋒一轉提到他的性經驗:「哎至少一百人吧,數不清啦。」「這在我們真的是很自然的事,跟吃飯一樣。」
「但妳知道嗎?最棒的事不是性本身,而是結束之後,兩個人躺在床上開始說話。說一些平常不會隨便和別人說的事。」
「在這個情境之下,我們之間真的有一種很親近的感覺,性是通往這個魔幻時刻的鑰匙。妳能想像嗎?我可能連他的真名都不知道哦,但他可以跟我說人生最私密最不堪的事,甚至可以在我面前哭。」牧的眼神突然變得很認真。
「有一個一夜情的對象因為前妻劈腿離婚,後來再也沒有辦法對女人有性衝動。有一個對象提到最近為他姐姐的事心煩,他姐姐結婚後生小孩沒有工作,不敢跟先生要錢都跟這個弟弟要,弟弟不想給,但想到小時候爸媽重男輕女,每次姐弟吵架時弟弟一哭,爸媽就把姐姐衣服脫了,用封紙箱膠帶把她捆起來,連嘴巴也封得緊緊的,只留鼻子呼吸,再拿老舊的水管拼命地打她……。」
小屋子映著窗外微弱的月光,閃著螢火蟲般忽明忽滅的光芒,讓人渴望伸手去抓。
「但我知道現在過這般生活的代價。」牧又話題一轉。「我知道這樣換著一個又一個的一夜情對像,我就不能期待我三十五歲的時候,會有和我牽著手在風雨裡散步的人,會有一起下班後疲憊地邊吃著消夜邊互相打氣的人。」
「你有進入過一段認真的關係嗎?」我問。
「很久以前了。」牧一口氣把一杯水全喝完,彷彿在拚酒。
我以為那會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沒想到半年後,他又單獨約了我去國父紀念館附近一間地下酒吧。那兒有飛鏢,有桌遊,酒也好,吧檯的女生高挑可親,就是沒有任何客人。
「我要離開台灣了。」牧劈頭便說。
聽牧說了好長一段才聽懂,他喜歡上公司一個小他近十歲、剛畢業的年輕女孩子。女孩高挑亮眼,有著對牧來說完美弧度的臀部,牧觀望半年才敢去搭訕。
牧費盡畢生功力,安排了幾場接近求婚等級的約會,有夜景、有佳餚、有女方的好友,我相信他連重要橋段的台詞都背得滾瓜爛熟。
但在第四次約會時,女方觀察到牧的性向光譜向他詢問,而牧不想騙她。
「連這麼多年來一夜情的事情都沒來得及說呢,她就不再回覆我訊息了。」牧苦澀地笑。牧拚著想放下,但還是不由自主地每日等在她上下班及午餐可能經過的地方,只求和她眼神交會一眼的可能。
這是我認識的牧嗎?
「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人生還有很多該努力的事。」牧向我介紹他的創業想法,創立虛擬連結實體場域的交友社群平台,聽聞國外已有一些落地的實例。
「妳也積極一些吧!我們男生年紀越老越值錢,妳們女生三十歲以後身價就往下跌了呢。」我望著牧離開的背影,他向正當滿月的夜空凝視許久,落在街燈後的影子拖得老長。
這個城市的心事說來都是老生常談,盡是碎裂的玻璃片,我有時不想說也不想寫,怕寫起來就像費盡心思在描述每個碎痕的紋路如何如何不同這般無聊。
但有時又好想大聲疾呼,不是只有玻璃碎痕呀,我曾看過如螢火蟲般忽明忽滅的光芒,裡頭有恍若可稱之為真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