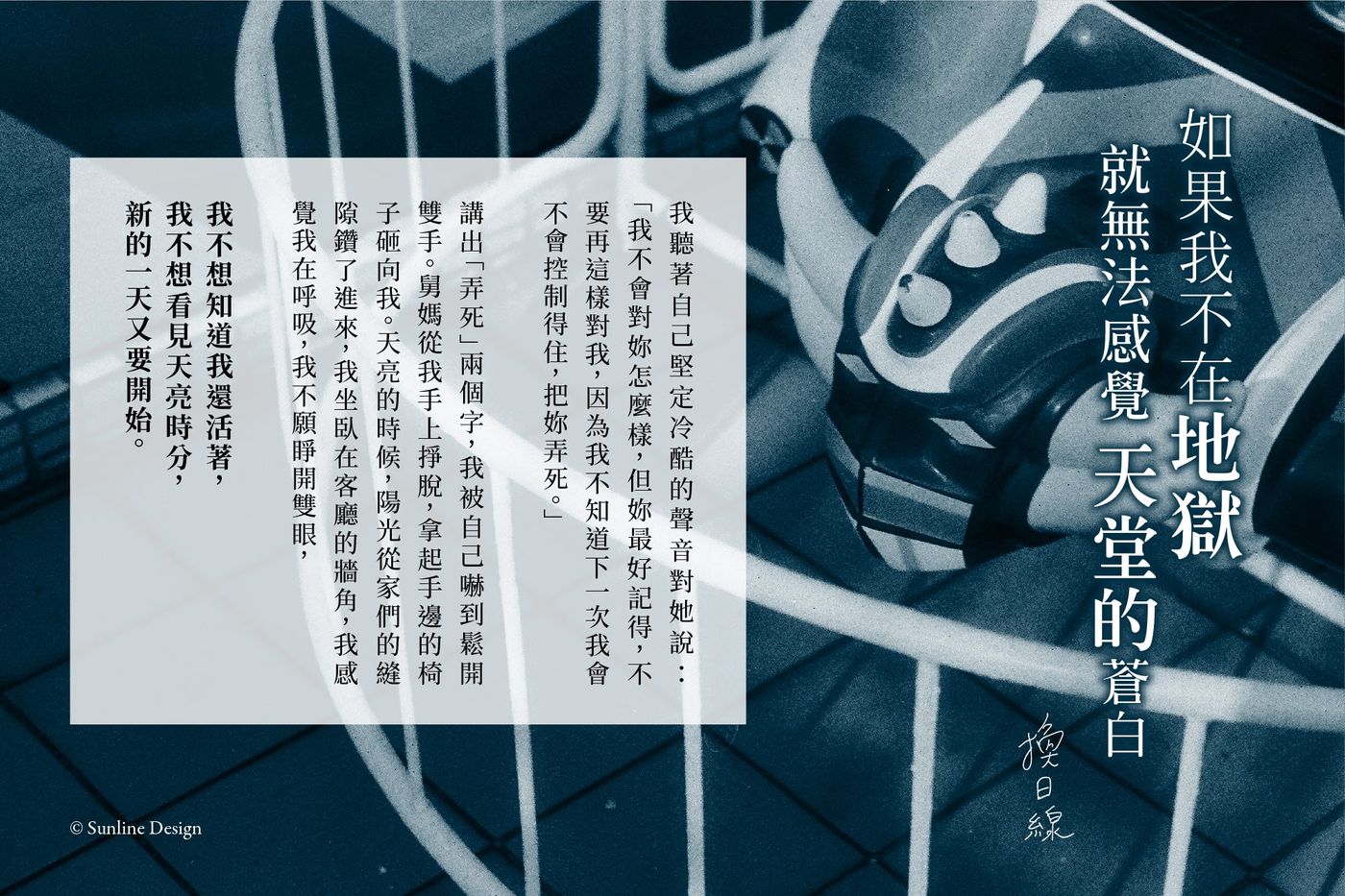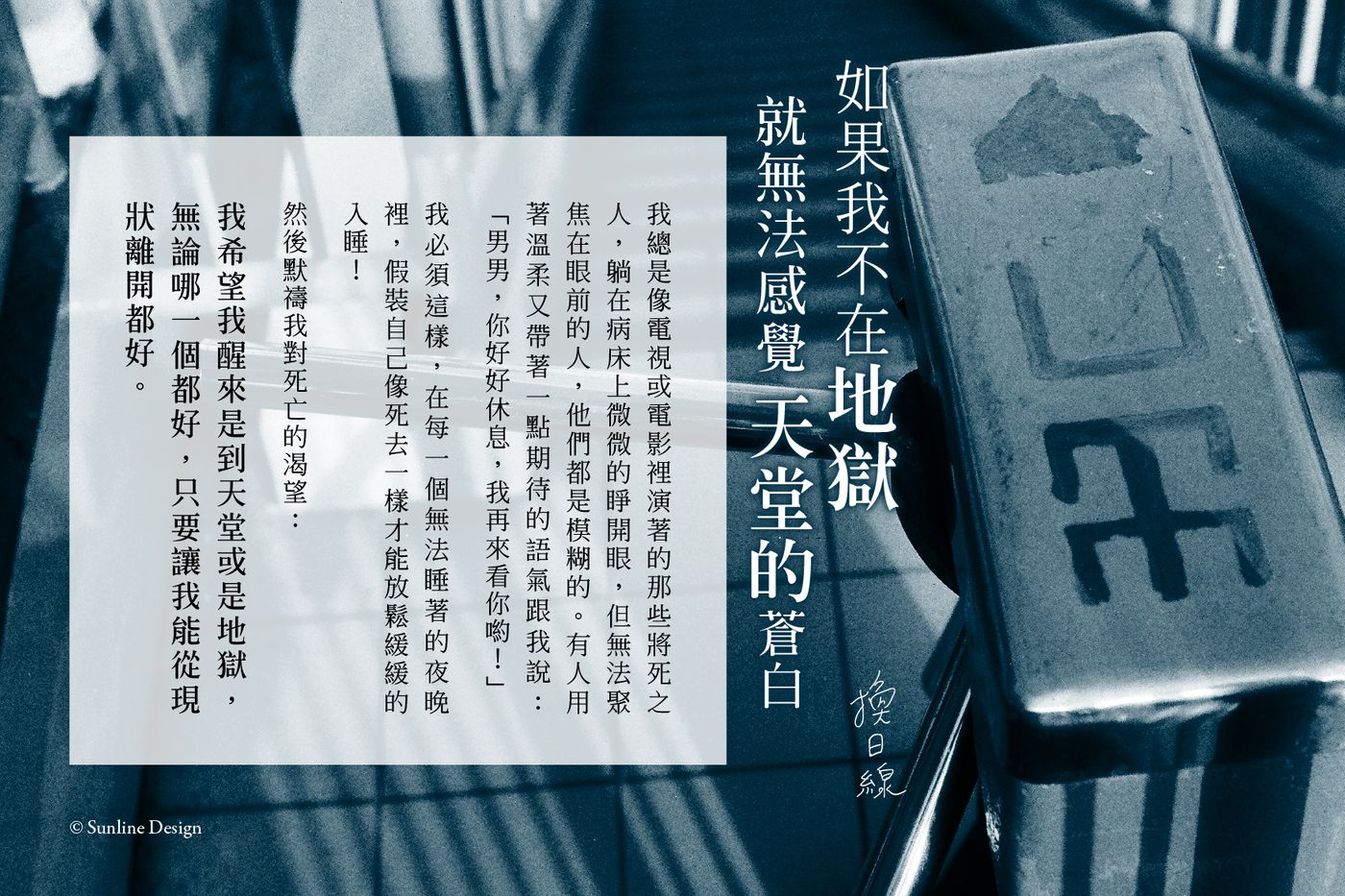
摩托車準備下橋的時候,為了閃避一台從右邊切換車道的摩托車,我將車身一偏被後方的來車撞飛在中央分隔島上。這是八月夏日的午後,整個柏油路熱得快要融化,熱氣還烘得雙腳發燙,我一定是在某個瞬間閃神了,才會在這個天天往返的下橋處發生了車禍。
跌落路面的瞬間我看見所有人車全都靜止住,而我擦過路面的四肢像被烈火灼上產生了劇烈的疼痛。我企圖從靜止的現場站起來卻一陣暈眩,腦中怎麼也沒有後來的畫面,我到底最後怎麼著地的?
我聽不到身旁任何聲音。烈日的陽光直接刺進我的雙眼,我記起孩童的時候,每晚我會在入睡前禱告:
我希望我醒來是到天堂或是地獄,無論哪一個都好,只要讓我能從現狀離開都好。
我以為這一摔再睜開眼,會看到牛頭馬面或者七爺八爺來接我去離去,我記不得到底通往陰間會是被誰接走?我只知道,如果可以最好越快越好,讓我從這世界離線,越快越好!
*
我沒有被帶走。等我醒來的時候,眼前的白景不再像烈陽那樣炙熱的紅白,而是拍照時拿來自訂白平衡的那種白畫面的白,色溫偏藍有點蒼白。我沒有戴眼鏡,視線糊成一片,我用手摸摸枕頭的兩側,想要找到我的眼鏡,但我找不到。
我身旁的聲音開始清晰起來,是儀器運轉的聲音、人的走動聲,我聽不太清楚,我閉上眼睛想要專注聽。我聽到有人在我附近,我想轉頭、翻身,卻沒有什麼力氣,只隱約看見有個人趴在我的床邊,但我看不清是誰。我的頭有點痛,瞇著眼又再度睡去,睡去前我沒有再重新演練孩童時,我緊張、害怕、睡不著覺時會演練的戲碼:
我總是像電視或電影裡演著的那些將死之人,躺在病床上微微的睜開眼,但無法聚焦在眼前的人,他們都是模糊的。有人用著溫柔又帶著一點期待的語氣跟我說:「男男,你好好休息,我再來看你喲!」
那個聲音有時候是父親,有時候是鄰居玩伴阿虎,有時候是我喜歡的女孩小綠。我會上演自己在這些人面前嚥下最後一口氣死去的戲碼,在我腦海裡向這世界道別,然後我會輕輕閤上眼,感覺自己像死去一樣;我必須這樣,在每一個無法睡著的夜晚裡,假裝自己像死去一樣才能放鬆緩緩的入睡!
然後默禱我對死亡的渴望:
我希望我醒來是到天堂或是地獄,無論哪一個都好,只要讓我能從現狀離開都好。
*
等我再度醒來時,病床旁圍了幾個人,他們像正在談論什麼?坐在我旁邊的陪病床上,傳來的是舅媽的聲音,陽光灑進屋內我看不清她的臉,她像是在為誰焦急而擦拭眼淚,母親站在舅媽旁邊看到我睜開雙眼,一邊抓著舅媽,一邊用手摸摸我的臉,我眨了眨眼,想從陽光下確定在我眼前的是母親。我還沒來得急開口,她就激動地衝出病房外大叫著:「家女,家女,男男醒了,男男醒了,妳先回來!」
腳步聲趴噠趴噠的從另一頭快速地朝著病房而來。姊姊還沒走進房內,我模糊地看著母親差點雙膝跪地的動作被姊姊攔下,「媽,不要這樣。」
母親膝沒著地,姊姊拉起她說:「快起來,沒事了,男男醒過來就好。沒事了。」
母親像是擦著眼淚走到我床前,跟舅媽一起摟著肩看著我。我沒說話。姊姊走近床前摸著我的頭,她的手熱熱的,我才有一點知覺,否則眼前一幕竟像夢一樣。平時對我咆囂的母親和舅媽,怎可能如此的溫柔,替我掉下兩行淚?
姊姊邊摸著我,邊問:「有沒有好一點?」
我沒有戴眼鏡的望著她,也像在夢中一樣,那個沒有我這個奴才侍候的公主,竟也會關心我的感受是什麼?
我輕輕地答了一句:「我躺多久了?妳們怎麼都會在。」
「妳們怎麼都會在?」我一直認為如果我真的死去,最不會替我哭死哭活、最不會傷心難過的,就是這三個人,這三個現在看起來跟我緊緊相依的女人。
*
放學回家我才剛走到家門口,就聽見舅媽又在摔酒瓶了。放學後我特意在便利商店發呆,想要等到舅媽在平日喝醉昏睡過去的時間後才回到家,沒想到她今天特別晚,在我必須回到家的時間,她才剛開始喝酒發瘋摔得盡興。我站在門口握著已經掏出的鑰匙,正猶豫不知道要不要在此刻進門,另一支酒瓶又砸向門邊,我嚇得滑落手上的鑰匙發出聲響,只得硬著頭皮插入鑰匙打開家門。
在巷子裡的透天厝一樓,陽光始終沒有辦法照進一樓的室內,成天陰陰暗暗的。在我打開燈之前,只有電視機開著,裡頭的名嘴政客正唇槍舌戰誰也不讓誰,想讓自己的聲量壓過對方。舅媽坐在客廳的角落正打開另一瓶酒。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留下那麼多債是要誰還?」她一面開酒,一邊大聲數落已經自殺數年的舅舅,她的聲音跟電視機裡的聲音結合在一起,我差一點就以為她也加入了電視機裡的戰局。她邊喝又邊舉起手邊的空瓶,再度拋向她還能使力的方向。
我想閃過她的酒瓶和她的視線,卻被她逮個正著,她的眼神正落在我的身上,她想起身卻站不太穩。我貼著客廳的牆邊走,希望趁她還沒站穩起身靠近我前,奔往二樓我的房間。
我的腋下滲出了汗,額頭的汗流進了眼裡,我不由得停下來眨了眨了眼,她已經靠在我身邊,漲紅著臉呵出酒氣,逼近我的臉對著我說:「男男今天怎麼那麼晚才回來,家裡的酒沒有了,你不知道嗎?」
她巨大的乳房貼上我的胸口,使勁地抓住我的陰莖,痛得我無法開口。我想要用力扯開她的手,卻使不上力,她看我作勢想掙脫,更用力的像是要將我的陰莖我身上拔除似的,「為什麼沒有買酒回來?還這麼晚,跑去哪鬼混?」
我痛得眼淚直流,抵著牆用盡全身的力氣推了她一把,她踉蹌跌坐在破碎的玻璃酒瓶旁。舅媽還沒起身,母親從門外衝進來連手上的東西都還沒放下,就從我面前拉開了舅媽,然後甩了我一個耳光。我一手捂著臉,一手摸著我的褲擋,瞪著眼前兩個女人看。
母親邊開口大罵,邊扶起舅媽,「你怎麼可以這樣推舅媽?跟你說過多少次,不可以對舅媽沒大沒小的!」在我想要說出舅媽剛剛扯痛我的陰莖時,母親又開口了,「還站在那裡幹嘛?還不去拿掃把地掃一掃,等一下我們踩到怎麼辦?」
母親隨即轉頭向舅媽賠不是:「大嫂,拍謝啦,男男不懂事,妳不要跟他計較。我們進房間睡覺了。」
我沒有動作。當作看戲般的,繼續看著母親跟舅媽在我眼前一再重播的劇情。
舅媽搖搖晃晃撐著母親站起來開始呢喃:「秋華,妳要知道如果不是阿爸把要給你大哥的最後那塊地給妳當嫁妝,你大哥也不會因為替人作保還不出錢走投無路去自殺。」
因為這場戲太常上演了,在她們邊晃邊走進舅媽的房間前,我在心裡默唸著母親接下來的台詞跟著母親一起接下後面的話:「都是我們不好,讓妳受罪了。如果不是男男他父親把賣地的錢全部帶走,今天也不會這樣⋯⋯」
我拿著掃把摸著那邊火燙的臉頰,一不留意踩上一塊碎玻璃刺進我的腳掌。腳上的血和眼裡的淚像被按下沖水的馬桶,一洩而出。我拄著掃把停在客聽的正中央,看著腳上滲出的鮮血哭了起來。
姊姊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地從二樓走下來準備出門上晚班。她向舅媽的房間探了探頭,面無表情經過了我的身邊,看了我一眼說:「哭什麼,男孩子這樣哭很難看。」
姊姊沒再說什麼只靜靜地穿好鞋,出門後她重重地關上了家門,想要從那扇門發出什麼訊息,像是一種宣洩或是一種抗議。我啜泣得更厲害了,眼淚一顆一顆的從臉頰滑到下巴滴到胸前,蹲下來拔掉腳上的玻璃時,我的手機響了。
姊姊傳來LINE的訊息:「我的停車費繳費單你上學的時候拿去繳。」
我還沒解鎖手機,她又傳來:「快點把玻璃掃一掃,不要再忘記幫舅媽買酒了。」
玻璃刺進腳掌的地方已經不太流血,我用手輕輕地碰觸那塊玻璃的位置,深怕一不小心,再往肉裡扎進去;我用最迅速的速度將它拔起,本來已經被血塊凝主的傷口又開始冒出血,我脫下制服擦去臉上的淚水,也往腳上的傷口蓋去,直到我感覺它不再流出鮮血。
那晚我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上我和姊姊童年睡在上下舖時,我在天花板畫下的圖。我想起那些夜裡和姊姊在爸媽關上我們的房門以後,一起拿著手電筒在天花板上畫畫的事。每次畫累了以後,我們會一起擠在我的上舖,姊姊會輕輕拍著我的背到我入睡。有時我一個人在上舖睡不著,會探頭跟下舖的姊姊說:「姊,我睡不著,可以拍拍嗎?」然後從我上舖的被窩鑽進下舖她的身旁倚著她入睡。
直到父親離家後,我再也沒有和姊姊同床。
姊姊跟我說:「爸爸走了,以後你要像個大人一樣,睡不著要自己想辦法。」
我和姊姊原有共用的書房、臥室,變成各自獨立的房間。沒有上下舖,我再也無法在天花板畫著那些獅子、老虎、大象。再沒幾年,連原來我和姊姊一起畫的一家四口手牽手的圖案,也隨著屋裡的濕氣加重長出了壁癌,一塊一塊地剝落掉。
我望著天花板想著這些事,聽著樓下舅媽和母親的聲響,直到她們的聲音慢慢消失在黑夜裡。我想像自己將要死掉躺在病床上,父親回來了,母親靠在父親身旁,姊姊握著我的手說:「男男要快點好喔!我們都在等你一起回家。」我躺在自己床上微微點著頭,閉上眼緩緩地睡去。
我希望我醒來是到天堂或是地獄,無論哪一個都好,只要讓我能從現狀離開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