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台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全國進入三級警戒,公司改為居家上班、學校遠端上課,我們從原先線上、線下交替且並存的生活,改為只能線上。社交恐懼、網路成癮者彷彿找到合理依傍的浮木,但為什麼我們更加不快樂?
英國面對疫情,在2020年3月~2021年1月實施了三次封城,近期英國國家學術院發表「疫情長期社會影響報告」(THE COVID DECADE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societal impacts of COVID-19),其中針對7,000位父母或家庭照護者的情緒調查顯示,情緒、焦慮或注意力困難皆在封城時的6月出現高峰,孩童有心理狀況必須就醫者,也成長了35%。而不論是年輕或老年人,回顧2020年4月~5月的孤獨感受,都相較以往顯著上升,尤以16~24歲最多,中位數從8%成長至50%。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於《在一起孤獨》這本書中,分析了兩項「人性化」科技:機器人與網路。撇開人工智慧是否能取代人類的討論,網路確實成了疫情下必須保持社交距離的救星。包含電子圍籬監控人流狀況;遠端的課程教學、視訊開會,還有維繫情感的社交工具。
但事實上早在病毒來臨前,我們就已將與人連結的重心,轉向網路了。
書中提出的疑問包含:科技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但是否讓我們害怕交流?我們對科技的期待日漸增高,是否導致對彼此的期待日漸降低?最誠懇的敘述莫過於:“constant connection ,but alone together.”(在網路世界我們看似無時無刻的聯繫,但卻更加孤寂)。
科技雖來自人性,但卻隨著其發展漸漸主導人性。在實體聚餐中我們有一部分時間盯著螢幕,或在對方侃侃而談時,餘光感受到桌上手機正在召喚。身體在場但心卻在別處,戴上耳機、滑開螢幕就能進入他方,所以共時性下已不再有純正無雜質的地方。我們倡議儀式感,也只因真實互動容易被暫停,所以以清場姿態立定一段不被打擾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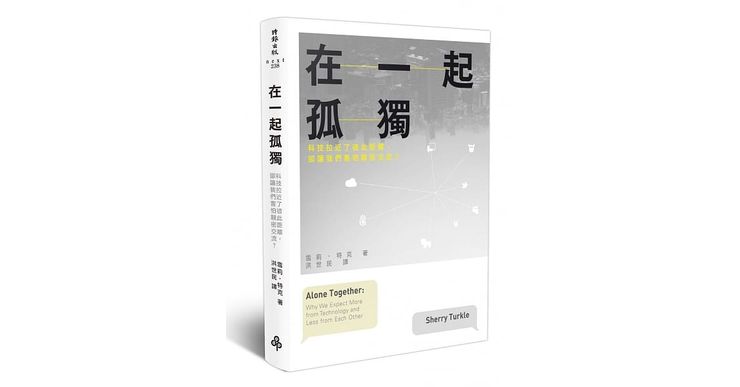
作者指出網路使人期待「零失和」的溝通,我們可以在對話框前再三斟酌字句再按下送出,對於不滿意的論述還能選擇收回,且無論是交談的內容、時機,甚至終止方式,都有較高的掌控力。而若將這樣的標準套用在真實的與人互動,對方的一時語塞、言不及義、毫無刺點的平凡故事,似乎都變得難以忍受,但完美的對話,真的能導向完美的關係?Line群組淪為單向執意分享資訊的平台,也更弱化了與人交流最重要的傾聽。
不可否說,今天我們登入社群網站、更新狀態,都不只是輔助溝通需要、補足現實生活中的交談,而是為了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如Instagram限時動態結合了想和他人聊天(私訊回覆)及經營自己形象(完全公開); 向同溫層提問、抱怨也讓我們輕易外化問題而非檢視問題。過往我們披荊斬棘進入網路世界,現在倒轉為拿著手機,才有勇氣進入真實叢林世界。
書名點出的孤獨,包含我們密切相處仍然孤獨,以及我們似乎無法自處。作者分析,青少年在9~13歲拿到手機,且被要求必須接爸媽電話後,也意味著他們沒有獨處的權利(和能力)。人願意讓渡自由進入Mark Poster超級圓形監獄為之監控,訊息的通知提醒著你的網路第二身分,人變得要有充分理由才能獨處。
當我們產生情緒:思念、憤怒、嫉妒、渴望擁有……,它的對象都是人,暫時用話外之音如網路短片麻痺自己、不正視源頭,可能結果會更感空洞。這也回到書中的另一命題,與機器人互動可以取代與人嗎?作者的回答是,關係、作伴都不該被簡化成與某樣東西互動來討論,而機器人之所以無法被稱為人,也是因為他終究無法如人一般理解人,網路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