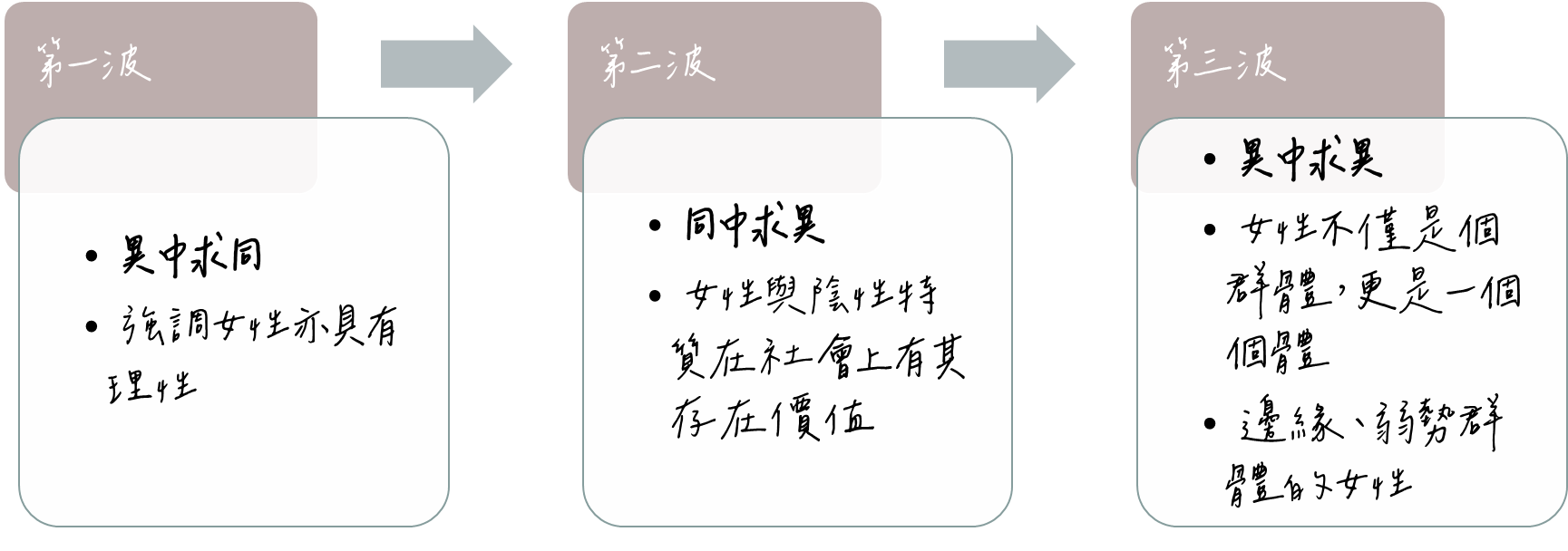頭戴白帽,身披紅衣的女性們走入了我的人生,紅色是生命的顏色,同時也隱含反叛的能量。藉由影集我初次接觸到瑪格麗特愛特伍作品(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我首次感受到有別於《動物農莊》,《1984》帶來的恐懼,由女性創作出來的反烏托邦世界竟然如此迷人,卻又如此殘酷。《使女的故事》像是給女性看的恐怖故事,它不賣弄突發驚嚇 (Jump Scare) 也不以血腥為號召。瑪格麗特愛特伍創造出了一個看似架空,卻又如此現實到令人戰慄的世界。

當使女成為無名女性的發言人
加拿大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提到:
「切記,在這本書中我所用的所有細節都是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的,換句話說,它不是科幻小說。」
寫作《使女的故事》之前,愛特伍花了很多時間田野調查,她蒐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受壓迫卻無法發聲女性的故事,將她們的生命歷程雜揉進她的小說中。無外乎,《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如此有血有肉。使女們的形象成為全世界無法發聲女性的代言人。
瑪格麗特愛特伍出生於加拿大,父親是植物學者,從小她與兄長在自然中嬉戲成長。愛特伍擁有作家,詩人,評論家,社會運動倡議者等多重身分,她敏銳的目光總能看到當今社會不堪的問題,一語道破複雜問題的癥結點,也許能歸功於長年觀察植物的經驗。1962年愛特伍進入哈佛大學就讀的時期,她在全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最高學府學習文學,憑藉著對於文字的熱誠徜徉於浩瀚文海中,在這之前他已經出版第一本詩集Double Persephone。哈佛作為最高學府,愛特伍發現隱藏在這棟四百年建築物背後的男女差距。1960年代哈佛圖書館並非完全歡迎女性進入,甚至部分圖書館只開放給男學生使用。在女性主義尚未抬頭的時代,女性主要仍依附在家庭與傳統價值。愛特伍如果有機會她想要進到這些"被禁止"的圖書館中借書,但事與願違。學術殿堂卻因為性別束之高閣。

愛特伍將他在哈佛的所見所聞雜揉成為創作養分。《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國,有著19世紀維多利亞式建築美感,基列國中主教夫人們身著藍綠色大衣,每一位都是飽讀詩書,才藝雙全的優雅女子,但是,最終他們都敗在”生育"一詞,這一個理應是象徵人類未來的名詞,卻硬生生成為這群女性的絕望來源。無論這群女性擁有甚麼過人之處,大學教授、公司主管,商場女強人等頭銜在極權統治之下毫無用武之處。另一方面,成為使女的女性只能落為生育機器,會行走的子宮。主教夫人們眼睜睜看著丈夫以神的名義與使女交媾,自己只能眼睜睜盯著他們行房。
此外,違反規矩的使女將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吊死,愛特伍親身抵達拍片現場時,看到這一幕時仍會發出感嘆「我怎麼會寫出這麼殘忍的故事。」她知曉這個情節皆出自於筆下,但她自己不忍卒睹。看到這一幕的同時,我們的生命彷彿已經與使女們產生連結。身為生活在二十一世界,感受著前人們奮鬥過的痕跡,當代女性們能夠男性在同個職場工作,擁有投票權,受教權。當某一天某個時刻,我們理應擁有的一切瞬間被奪去,女性再度回到無法做選擇的時代,《使女的故事》一部殘忍的末世寓言,直截了當劃開了女性們內心深層的恐懼。
相較小說中嚴肅的文筆,愛特伍以獨特的幽默感擄獲了世界各地讀者的心。日常生活中她就是再平凡不過的女性,以寫作維生,閒來無事喜愛拔拔雜草,每日花時間沉浸於書店,喀拉喀拉打著鍵盤,創作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故事。身為女性,女兒,妻子,母親,作家,愛特伍筆下每一位女性皆有各色面相,在藝術家朋友眼中,瑪格麗特愛特伍擁有耀眼的光芒但不扎眼,她的謙遜溫和令人印象深刻。身為得獎無數的暢銷作家愛特伍,除了自身創作外,同時關注於女性議題,深知世界的某個角落仍有無法出聲的女性們,他們因為各種原因被剝奪了發聲管道,愛特伍決定將他們的故事寫進作品中,以小說中的角色們代替他們發聲。無論是《雙面葛蕾斯》中的被貼上無數標籤的女主角,抑或是受困於宗教與威權下,失去人權與自由的使女們。

她自認為自己不是社會運動者,因為社會運動者窮盡一生擁抱理想為社運付出。
「我常被找去代表這些人說話,是因為我沒有正職工作,去講話並不會危及我的生計。」愛特伍一派輕鬆地說道。
社會運動者走上街頭以身體力行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小說家以筆代戎,他們的筆就是武器,就我的觀點愛特伍與社會運動者並無二異。她追求著更平等且美好的未來,對於世界上不公不義之事深痛欲絕,只要還有呼吸她就不曾停止觀察與批判。藉由著作發表,她受邀至各大場合演講,面對著年齡層、性別不一的觀眾,她相信她的作品擁有力量,能夠改變世界。
如今的女性並非如過去被描繪的如此楚楚可憐,溫柔婉約且脆弱不堪,一切歸功為女性權益發聲的各方人士。2016 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第五十八屆總統,擁有著商人光環,強調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同時提出反墮胎,反對提高最低基本工資等政策。川普狂人形象結合性別歧視言論,無疑是將美國從1980年代為女性權益努立成果蒙上一層陰影。
長年推行女性運動的人士紛紛穿上使女的服裝,頭戴白帽,身穿紅衣,走上街頭表達不滿。現實中,她們不再如小說中使女的處境,被動接受殘酷世界的來臨,這群社會運動人士希冀能在小說成為現實之前奪得話語權,奮力抵抗。

以睿智的目光回敬這個殘忍的世界
愛特伍在某次訪談中提到,當她還沒甚麼名氣的時候,她有次將成冊的稿件寄到某間出版社,卻遲遲沒有下文。直到愛特伍稍有名氣並且得獎後,該出版社才回信聯絡她。編輯給了一個令她哭笑不得的理由:
「因為有位女職員懷孕變得健忘,沒有將稿件從抽屜取出,導致出版社沒有回信給你。」
愛特伍接著說道:「我看到稿子被擱置在書堆最下層。」
因賀爾蒙影響改變孕婦身體,為人母的不適卻成為了出版社編輯的藉口。愛特伍的口氣有些戲謔也有點無奈,因為她知道這件事情一點也不好笑。女性的身體除了不應成為他人的藉口,同時也體現出女性的身體、性事,儼然成為茶餘飯後日常話題,笑話的背後是某個群體的遭難,更顯得世界不平等。
以《使女的故事》與《雙面葛蕾斯》為例,愛特伍的小說作品以女性視角出發凝視著由父權架構出的世界。階級,父權,被剝奪感控制著故事中的女主角們。映射出歷史上生活在被父權世界綁架的女性們,她們失去的能動性以及選擇權。就跟川普當年的墮胎令一樣,她們無法選擇要不要將腹中的小孩生下來,在此時她們的身體已經不是自己擁有,而是獻給男性的祭品。
美國藝術家芭芭拉·克魯格:「你的身體就是戰場」
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Barbara Kruger


圍繞著一樁殺人命案,女僕葛蕾絲被指控為殺害主人的兇手。改編自19世紀真實發生兇案。《雙面葛蕾斯》主旨並非在找出兇手或是偵探解謎過程,一名出身低賤的愛爾蘭移民少女,受到貴族家庭的欺侮,她反抗的過程又有誰在意呢?也許一般大眾們與故事中的心理醫生一樣,在意的只是葛蕾斯當時的意識是否清醒, 她從哪裡來?她的故事 (Herstory) 就在歷史 (History) 中被人遺忘。
攤開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愛特伍細細閱讀信中的一字一句。因為她知道這些信件乘載的是不同女性的生命故事,不可承受之重。這些女性可能沒有名字,有些人可能也已不在人世。當女性成為使女之後,她們就失去了姓名,而成為某位不知名大主教的物品。June 從此成為了Offred。(Of Fred在英文語意為Fred的(所屬)之意。),使女的故事與神隱少女中的千尋一樣,頭也不回地前往奪回姓名的旅途。
被奪走姓名,就會找不到回家的路。—《神隱少女》
即使被剝奪名字,也請不要忘記自己是誰。—《使女的故事》

面對到由男性為中心建構出來的歷史。《雙面葛雷斯》中隱含一個有趣的觀點:
這世上沒有女的莫札特,因為沒有女的開膛手傑克。There is no female Mozart because there is no female Jack the Ripper.
藝術史評論學者諾克林同樣提出了類似疑問: 「為什麼這世界上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無論是殺人犯,藝術家,或是天才音樂家自古以來就是男性的領域,愛特伍就讀的哈佛大學也是如此,女性的故事囚禁於經年累月的桎梏中,在這些問題背後,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是問題的本質與從古至今的社會架構。愛特伍藉由前人的論述,容納自身觀點創作出一本本叫好又叫座的小說,除了商業上的成功,愛特伍的作品乘載的概念影響了後世許久。
《使女無懼:瑪格麗特愛特伍》由Nancy Lang & Peter Raymont兩位紀錄片導演,以深刻動人的鏡頭語言,側寫瑪格莉特愛特伍的人生故事,這一部紀錄片如同她本人的個性,安靜細膩,不以張狂,憤怒的態度為訴求,卻十分強大。當使女成為走出小說,被拆解成符號,這股安靜的力量即成為襲捲全世界的女性浪潮。我無法一一訴說《使女的故事》帶給我的人生啟示,生育也許不是現代女性人生必經選擇,愛特伍已不間斷地提醒世人這條革命之路還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