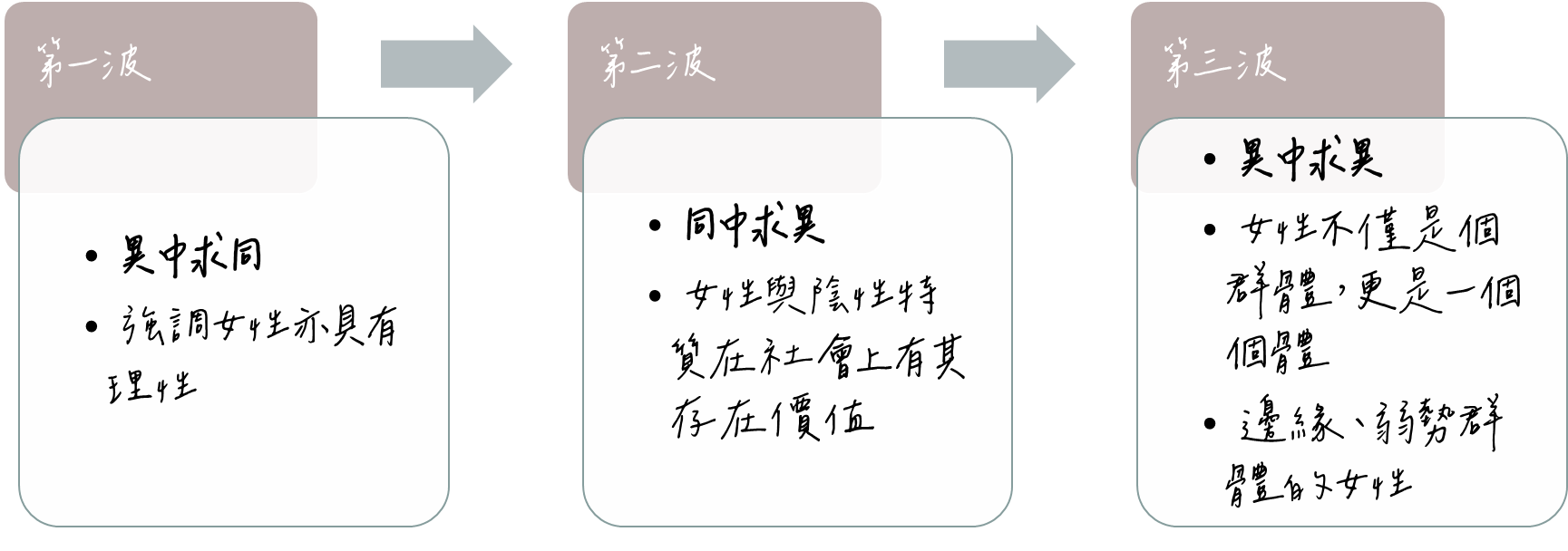☼ 文章同步發佈於《潺時》ISSUE. 15:立春

What now takes the place of those things I wonder, those real standard things? Men perhaps, should you be a woman; the masculine point of view which governs our lives, which sets the standard, which establishes Whitaker's Table of Precedency, which has become, I suppose, since the war half a phantom to many men and women, which soon, one may hope, will be laughed into the dustbin where the phantoms go, the mahogany sideboards and the Landseer prints, Gods and Devils, Hell and so forth, leaving us all with an intoxicating sense of illegitimate freedom–if freedom exists....
—— Virginia Woolf, The Mark on the Wall, 1917
吳爾芙(Virginia Woolf)1917年的第一篇公開發表故事 The Mark on the Wall 中以其標誌性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手法書寫而成,透過敘事者女子對牆上的黑點之想像,探問父權秩序與女性想像之間的關係;而至1958年,懷孕的安妮・華達(Agnès Varda)拍下了《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L'opéra-mouffe,1958),從孕婦的視角出發,以細膩而敏感的鏡頭語言,記錄下此種特殊的女體經驗與迸發之想像。觀賞華達的短片時,我無法不聯想到吳爾芙的 The Mark on the Wall,她們在兩種非線性敘事中,各自解構了傳統的秩序空間,進而於文字、影像中,建構新的、充滿流動性與生命力的陰性場域;更透過一種虛幻、脫離真實的想像,掙脫與破壞現實束縛,遁入且陶醉於那「不合法的自由」(illegitimate freedom)中

▍失序,性別空間的重建
在吳爾芙的短篇故事以及華達的短片中,空間場域與社會性別角色有著緊密關聯。於 The Mark on the Wall 中,我們透過敘事者女子的第一人稱視角,先聚焦看見牆上的黑點,而後隨著她的幻想推進,她的「身體存在」感也越來越明顯,我們慢慢明白那個黑點位於一個家中的公共空間——客廳,不是女子的臥室,也不是書房或工作室,而是一個「開放式」的共享環境。而在《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中,巴黎的穆浮塔街成為貫穿的空間場景,隨著華達的鏡頭,我們從小攤販,走到咖啡廳,再至烘焙坊,從一個市集穿過另一個市集,街巷無疑也是一個公領域,且更勝於房屋中的客廳,它將個體與整個社會,乃至世界連接,有著更強烈的開放性。
如建築歷史學家珍・藍道(Jane Rendell)曾提及,「空間」絕不只是以幾何學衡量的惰性存在,而是人類日常生活中不斷變化的場域,與個人、社會、乃至兩者間的活動密切相關,因而不論在吳爾芙的文本或是華達的影像中,選擇一個具一定程度開放性,且能使個體走入環境之空間場域,作者必然有其欲使故事中女性主角與社會對話、互動的目的。
在 The Mark on the Wall 中,傳統的客廳空間被顛覆而重建,不同於維多利亞時期文學傳統中的客廳與女人,總是在優雅、安靜、華麗的環境中,沏茶、享用甜點,處於安分的秩序之中,扮演著其後天的性別角色,於此吳爾芙在空間中加上的牆上之印記,成了雪白的權力與秩序上的「污點」,象徵著不安與失序,而如此「失序」恰恰從敘事者「我」的女子主觀視角開始蔓延,在她的「發覺」與延伸想像中,傳統空間的性別權力關係被顛覆,牆上的黑色圓形印記,也就成了通往新空間的孔洞(即便敘事者於想像後段發現那並不是一個洞),隨著吳爾芙的文字,讀者如被吸入黑洞中,在另一個平行的想像空間中,以黑點作為仲介點,回望現實空間。吳爾芙棄男性主導的現實與秩序於不顧,使讀者在短時間內遁入她的陰性幻想——失序,或說,秩序的重整。
而在《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中,街道則更像是給予敘事者想像的泉源,也像是一種女性身體經驗延伸的空間。懷孕的女性在大多公共場域是不被歡迎的,然此處,華達正顛覆著此一社會空間對女性的限制,電影開首,我們看見女性隆起的孕肚與乳房,赤裸不遮掩的女體,是隔著紗的,是必須被隔在私領域空間中的,但接著下一個鏡頭,跳接來到了人群嘈雜的市集,巨大的南瓜被剖開,挖出南瓜籽,而呈現中空的型態,似於女性身體之隱喻。此開場片段,透過空間的轉換,和其中女體的「變形」,我們看見「懷孕的女子」從現實的私領域空間,走入帶幻想基調的公開場域,女性獨特的身體經驗與心理變化,便能開展於街巷之中。如同吳爾芙的敘事,這樣的空間轉換與重塑,有其失序、顛覆的意義,我們近距離看見女子的孕肚波動起伏著,即如 The Mark on the Wall 中的「污點」,是一種打破慣性與惰性的存在,《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接著便由華達的鏡頭/敘事者女子的視角,展開其陰性書寫的「日記」(Diary of a pregnant woman),既私密又與社會連結,在此場域中,她以歌劇之音符,重整自己世界的秩序。


▍幻想自然,女體之自然
在《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中,章節〈對自然有感〉與〈妊娠〉相連結,我們看見海灘、驕陽、蔬菜、植株、與花朵,她高歌:「魚在蛋裡,芽在肉裡,白鴿在水裡」。再次地,自然的秩序在敘事女子的想象中被錯置,白鴿在透明球裡徒勞地向前舞動,女子光著腳跑入後花園,幻想的境地中,女性與自然密不可分,自然展現的是一種流動性,打破既有事物的秩序與位置,重新孕育與創造,正如其身體所處的變化,妊娠是自然,自然在奇想中被擁抱,在顛覆中重獲新生。
同樣地,在吳爾芙的意識流中,自然也是陰性的(her),她是自由、舒展、平靜的新秩序。
[S]o Nature counsels, comfort you, instead of enraging you; and if you can't be comforted, if you must shatter this hour of peace, think of the mark on the wall.
「自然」(nature)透過吳爾芙的意識流,在室內、人造、傳統的秩序空間內被幻想,被作為有生命、有性別的角色喚起,不同於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許多男性文學家喜以「呼語」(apostrophe)召喚自然,以展現自己的創造力,在詩行中「無中生有」地呼喚四季、花草樹木、和一切自然物,此處,吳爾芙的文本和華達的影像中,女子異想世界裡的自然不再遙遠,而是滋生於其陰性想像,本於其與世界真實的感通而重建的「Nature」,是她們的「對自然有感」,也是一種「妊娠」的女性身體週期之自然。
介於噁心與渴望之間,介於腐爛與生命之間
身體自然的感受與經歷順勢被華達以影像具象化,我們看見牛肚、牛心、動物腦⋯⋯等器官,那是一種介於美味渴望與噁心排斥之間的身體狀態,也是介於生命力與死亡腐朽之間的符號,代表著懷孕女子的身體經驗。她在街道上散步,走入花店,拿起玫瑰,而後啃食,音樂從神秘不安漸漸隨著女子食花之過程,被咀嚼地平靜而悠遠。花店之花,介於自然與人為之間,既象徵生命,卻又因被切斷自然之根,得以被安放於花店,為人欣賞,對懷孕的女子來說,那幾乎就是自己的身心感受,渴望孕育生命,卻又為必然的「斷根」,與伴隨的身體經驗之噁心、疼痛,而感到恐懼。正因擁有如此身心經驗和感受,所以她將花放進嘴裡,一瓣一瓣地啃食,她要花成為她的一部分,而不是遠觀的被凝視物,這便是由女性身體經驗而生的,與自然之感召。
如果戴洛維夫人要自己去買花,那麼華達便要懷孕的女子——自己親吻那朵花,自然與女體在美幻中被吻成一線。

▍女性幻想介入現實,而男性介入女性幻想
I must jump up and see for myself what that mark on the wall really is–a nail, a rose-leaf, a crack in the wood?
在吳爾芙的意識流中,幻想是介入現實的,正如牆上的印記介入她的平靜生活,介入她的思想中,她的想像同樣地乘載著現實,透過牆上的印記,她在異想中回應現實,關於歷史戰爭、關於父權秩序、關於權力關係⋯⋯ 她嘗試在「非現實」中找到「現實」的答案——那究竟是蝸牛、玫瑰花瓣、還是木頭上的裂痕?她仍在探問「真實」,而這正是女性幻想(female fantasy)體現的女性自我賦權(empowerment),看似如意識之流水般柔而虛幻,實則具強韌的力道,她知道她必須要「跳起來」看清楚牆上的印記,吳爾芙以 “must”(必須)一帶有強烈使役性的詞彙,以及 “jump up”(跳起來)一動作表達敘事者女子欲找出真相的心情,不是站起來,也不是走過去,而是「跳起來」——意志與行動才是幻想的內核。
Everything's moving, falling, slipping, vanishing.... There is a vast upheaval of matter. Someone is standing over me and saying–
"I'm going out to buy a newspaper."
"Yes?"
"Though it's no good buying newspapers.... Nothing ever happens. Curse this war; God damn this war!... All the same, I don't see why we should have a snail on our wall."
Ah, the mark on the wall! It was a snail.
然而最後男性介入了想像,女子來不及動身,來不及「跳起來」自己看看牆上的印記,就被男人打斷,並「被告知」現實,而這一連串的女性幻想意識流,便在男人的聲音中消散,她對秩序的探問與挑戰,仍舊被收束於男性主導的「現實」之中,正如其前言,「男性的觀點仍支配著女性的生活」(“[T]he masculine point of view […] governs [the women’s] lives”)。故事戛然而止,但我相信最後一聲「啊」(ah),並不代表女子被動地接受了男性的「現實」,它反而帶出了一種悔恨(regret),甚至輕蔑(contempt)²,是女子對其幻想終結的不滿足,也是吳爾芙對父權慣於介入女性想像,而強加男性主導的現實之鄙棄與控訴。

▍幻想之音,歌詠女體現實
延續前論,於《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中,華達也在幻想中體現了其自我賦權,〈親愛的,不在了〉與〈歡慶〉二章,她從想像走入現實,如果說1917年,吳爾芙筆下敘事者女子的幻想仍被男性打斷,那麼我願相信,1958年,巴黎這名懷孕女子,終於以日記、以歌劇,吟唱著自己真實地存在,不被打斷,存在於於此醉人的女性幻想之中。
「活著,但不在」、「死了,不在了」——她在想像中高歌生命,吟詠可貴的現世,一張張老照片,將虛幻與歷史連結,活著而不在場的是無限開展的非現實想像,死了而不在的是消逝的現實,於是透過懷孕女子紀錄的「日記」與「歌劇」,她讓此段女性身體經驗的現實「存在」,存在於流動的幻夢,存在於私密細膩的情緒裡,這些被認為的「陰柔」(feminity)其實真真正正地介入了生活,「懷孕」一屬於女性的特殊現實,在幻想的歌聲中,被紀錄著。

▍結語:幻想中歡慶,我們存在
「幻想」(fantansy)作為一種與現實背離的思想途徑,在吳爾芙與華達的敘事中,卻成了女性接近現實的方式,在父權主導的社會秩序下,唯有透過想像,她們得以繞過阻礙,在看似虛幻的陰柔中賦予己力量,而後重建一個女性幻想的空間,在那裡,他們「歡慶」,樂音裡飄蕩耳語——親愛的,我和我的身體存在,我們存在。

註釋:
¹ 標題致敬《懷孕女子的異想世界》(L'opéra-mouffe,1958)中其中一章節〈親愛的,不在了〉。
² According to Merriam-Webster, Definition of ah, “used to express delight, relief, regret, or contem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