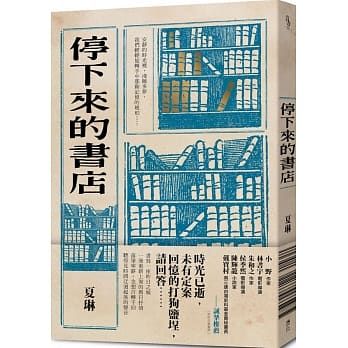本文刊載在《聯合文學》 2021 年 12 月號
若能為「記憶」賦予形體,例如山巒、房子、書、人或任何物品,人會選擇什麼物體?陳雨航在〈時光電廠〉直指,自己的記憶源頭是花蓮木瓜溪畔旁的清水電廠。除了他兒時曾住過那裡之外,那邊的山谷地貌,得費盡一番功夫才能抵達,途中溪流百變的樣貌,不斷地沖刷微弱的童年記憶。
等筆者重返故鄉,電廠已圈在保護地範圍,只能在鐵門外遙望電廠,徹底成為局外人。原是讓兒時記憶延長保存的電廠,就在那天起,使記憶徹底成了虛空。所以筆者在尾末寫:「在記憶毀壞之前,那樣就很好。」
《時光電廠》收錄陳雨航不同類型的「記憶」,有童年時光的探尋、文壇友人的往事、旅行發生的小插曲等。各篇章雖主題各異,卻匯流到同一處地方,那裡便是記憶的集散地。
記憶不是將某個瞬間固定下來的片段,而是綿延的對話過程,塑造了此時的自己。
記憶時常是污濁的,混雜他人的記憶,甚至包覆未能解釋的謎題,如〈時光電廠〉記得母親說某區是阿美族工人宿舍,但筆者不曾看過房內有人。又好比〈臺東旅次〉提到父親出外與神秘的 M 舅會面,讓筆者忍不住想像 M 舅趁他熟睡時來訪,了結與傳奇人物見面的心願。
記憶是否毀壞,除非有現實物體幫忙回溯,否則根本無從辨別。所幸,時間除了製造記憶的斷點,有時會增強記憶的真實感,像〈星夜殘影〉兒時記不清楚的電影,多年後看到歷史資料,驗證當年確實有電影巡迴隊走訪電廠,筆者才敢確信記憶尚未崩壞。
這些集體記憶構築的「歷史」,往往就是記憶能被拾回,確保沒損壞的重要地圖。
儘管個人的記憶常是閉鎖的,外人難輕易敲開。然而在〈冬日的邂逅〉中,筆者意外地進入日本舊書店老闆的回憶,一名舊日本帝國的海軍航空隊軍人。兩人分屬不同世代,筆者卻能從遙遠的史料,卻藉此打開另一個人的記憶。
《時光電廠》乍看是一位六零年代輩作家的回憶散文,但是文內總散落著歷史感的細小物件,讓後輩讀者能侵入筆者的記憶,捕捉到時代尚未毀壞的樣貌。
延伸閱讀:《躊躇之歌》

陳列同屬六零年代輩的作家,曾在 1972 年因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入獄。
《躊躇之歌》前半段,紀錄被捕那年的心情,穿插禪寺的幽靜、辭職準備考試的焦慮,以及情治單位的無理訊問。入獄怎麼可能不氣憤,但書中展現的是靜、焦躁與絕望,三者如麻繩般交纏。後半描寫出獄後參政,沒有高亢熱血,反而懷念山中的歲月。
這段壓抑的記憶,類似《時光電廠》的舊書店老闆,需要歷史幫忙敲開,讓後輩讀者能更接近白色恐怖的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