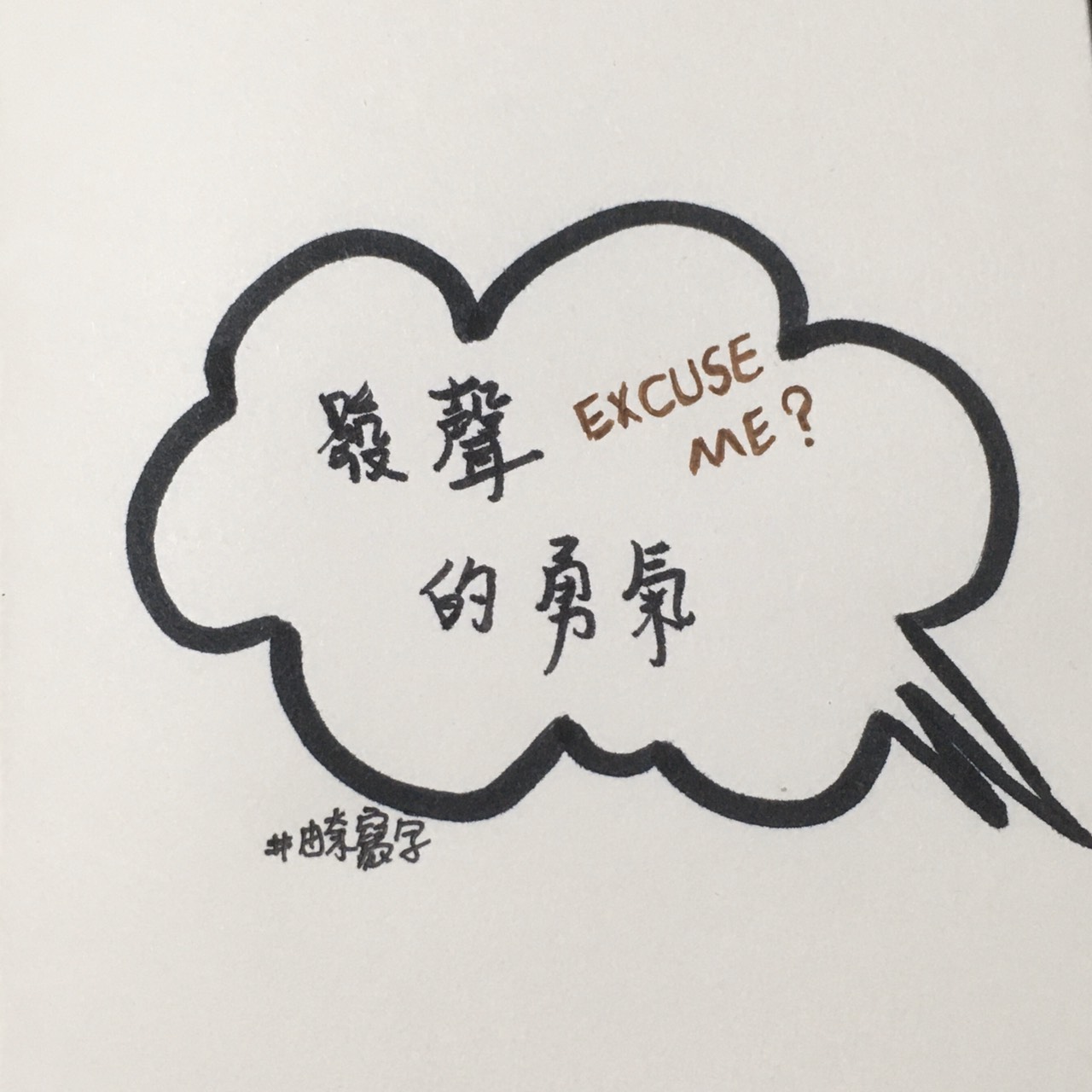善意的眼,感恩的心

台中旱溪媽祖廟,三級古蹟樂成宮。香火鼎旺的廟宇,偌大的停車場,偏偏還是有人違規停車。一部小貨車或許是臨停,挺霸氣地堵住小弟的車子。車主沒有留下任何聯絡資訊,既然進退不得,我們只便守在一旁枯候。
終於有人邁著大步向小貨車走來,急於返家的小弟大喜,立刻迎上前去:「先生,請問這車是您的嗎?」
來人臉色大變,聲音飽含怒氣:「你看我像開貨車的嗎?」
那名男子在小弟連聲道歉中怒氣沖沖地離去。我望著那個怒火衝天的背影,忍不住就想:開貨車又怎麼了?不偷不搶的正當職業,怎會讓閣下氣成這樣?
我想起此前多年的場景。
留職停薪那年,搬到新居未久,每天一早開車送小孩上學。車子開回社區停車場,我這才穿著家居服,趿著拖鞋,慢悠悠晃到巷口的早餐店。
總是單點吐司夾蛋,配店家的報紙下肚,彷彿日行的早課。
連著去了幾次,有一天照常送上餐點的老板娘突然問我:「有工作嗎?」
有工作嗎?留職停薪要算有工作還是沒工作?如果給出留職停薪的答案,是不是還得解釋原因?
算了算了,那就當沒有吧。
老板娘見我搖頭,便說:「那要不要來我們店裡工作?」
留職停薪本為調養長期工作透支的身體,我笑著拒絕了她的好意,回家的路上,忍不住揣測她的視角。
這個女人穿得很平常,總是上班時間來,總是點最便宜的吐司夾蛋(因為我吃人道素),連飲料也捨不得喝(她不知道我等著回家喝咖啡),應該是失業?
她的推測完全合理,只可惜不是事實。
即使與事實不符,她的動機不失良善。可如果套用停車場男士的有色眼鏡,這個場景最後的對話可能就會變成:「妳看我像洗碗端盤子的嗎?」
也曾在寒冬的夜晚,開車送小孩上書法課,好不容易找到停車位,索性就在附近晃蕩,等候小孩下課。
孩子早在我下班後就餵飽了,自己的胃腸還空空如也。正巧看見路邊亮著暖光的麵攤,我走了進去,叫了一碗乾麵。麵送上來的時候,還附了一碗堆滿食材的熱湯。
我指著那碗湯,老板娘一臉同情地說:「請妳喝的。」
她看見了什麼?
一個落魄的女人,一臉茫然地走進來,只點了最便宜的乾麵。這麼冷的天,連一碗湯都捨不得。
她不會知道我本來不愛喝湯。我的落魄、空茫,來自職場掏空的身體,還有與公婆同住被踐踏的心,就是與手頭拮据了無關係。
她對我的解讀無疑是錯誤的,卻是美麗的錯誤。我沒有作出任何解釋,但不愛喝湯的我把熱湯喝得精光,走出麵店的時候,渾身暖熱。
把場景拉到我隻身跨海,在北大博士班進修的場景。
時值寒冬,出門著涼,大陸北方的酷寒攀附在我的太陽穴,偏頭痛痛得我寫不成硬梆梆的論文,索性寫家書給在台灣的老父。寫著寫著,忽而就想起國中校長,已故世多年的汪沱先生。
汪校長有一年從馬公到台北開會,夜宿師大的校友樓。他沒忘記當年的畢業生正在師大就讀,跑到女生宿舍找人。室友回說我家教去了,汪校長留了話,要我去校友樓見他。
家教結束,我依約前去,已近晚上十點。汪校長劈頭給我一頓好罵:「妳不好好跟著教授作研究,準備讀研究所,跑去家教做什麼?」
氣極敗壞的汪校長說了一大串,時隔多年,我只記得這個開頭。我頂著他的罵,不敢稟實以告:親愛的校長,小女子出身清寒,如果不是考運夠好,正好考上全公費的師大,我老早就業去了。我一心等著師大畢業,好幫辛苦的老父養家呢。研究所?想都沒想過!
那當然只是我的內心獨白,汪校長一句也沒聽見。
想到汪校長,當然就想到推我去北大讀博士的李教授。蒙他青眼獨具,一路推著我往北大前進。我頭一次應考回來,準備申請留職停薪才發現台灣不准現職教師到對岸進修。李教授接到電話,一聽到我不願為了進修辭去教職,氣得在電話那頭大罵:「妳就想一輩子當一個中學老師?」
我心裡嘀咕:當一輩子中學老師又怎樣?
然而我終究在兩年後離開教職,重新考進北大。博士學位在望,忽而想起李教授那年的怒吼。當一輩子中學老師的確沒什麼不好,尤其在當時任教的文華高中,真是如魚得水,只是距離為中華文化發聲的夢想很遙遠而已。
兩位對我鍾愛有加的師長在不同時期拋出的怒吼言猶在耳,斯人已遠。我在博士生宿舍默默咀嚼往事,一股感恩的熱流泉湧而上,原本困擾已極的偏頭痛居然不藥而癒。
人間事紛紛雜雜,事件唯一,解讀可能不一。因著不同的解讀,可能得出迥異的感受。以善意的眼去解讀外在事件,不難換來感恩的心,因此充滿正能量,得以繼續在人間世快樂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