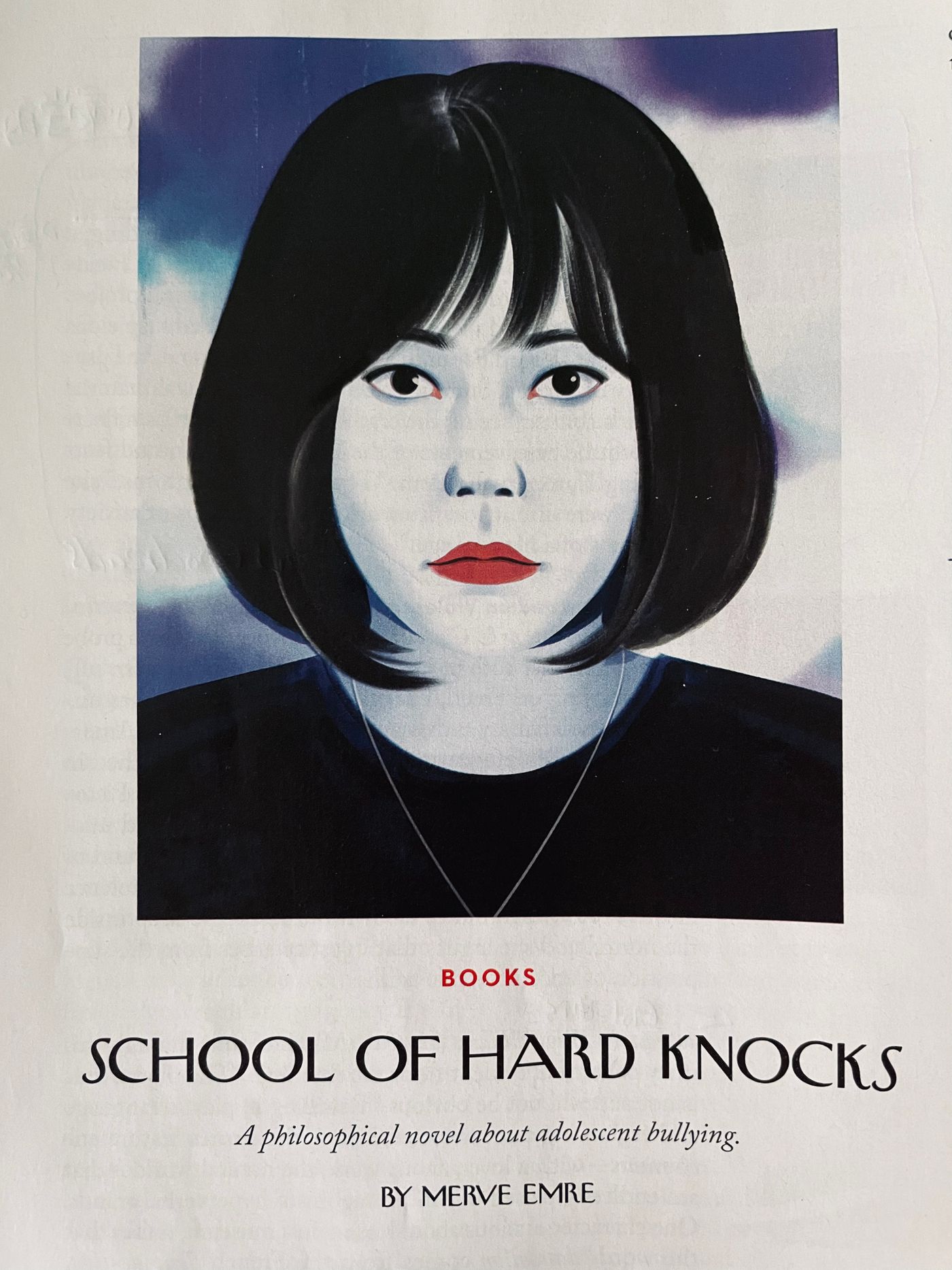去年是希臘,安哲羅普洛斯,寧靜悠揚霧濛濛,一群人走冷冽且長的邊境;今年是日本,大島渚,烈陽下廢墟殘垣,汗流浹背,有時流血,血是毫不在乎地撒向大地。那是大島渚的時代,個個淡漠的面容下蟄伏洶湧暴烈的心。
是眼睛透露了一切。《被迫情死的日本之夏》裡佐藤慶飾演的主角被問起:為何慾望被人殺死?他回答:「有人殺我的時候,那人會看著我,我會映照在他的瞳孔裡頭。那個時候,我就會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是誰、自己想望的是什麼,去認清與追求自身以及自身的渴望。比如《絞死刑》裡沒有成功死去且失憶的死刑犯 R,如初生的嬰孩卻不斷被眾多長官叩問自身是誰,只為喚醒犯罪的靈魂才得以再次行刑;比如《日本春歌考》裡四個高中生透過反覆吟唱同一首歌的變奏、延伸,去想像青春尚未實現的慾望。

那些壓抑的慾念因眼神流露出來。集結眾多個人的張望與想像就是一個國族共同的想望,每雙眼睛每張目光皆凝視同個民族漫長的歷史與傷痛,一億個不同的宿命是各自的星體去形成一個宇宙。戰爭遺留殘敗苦痛也使人創造強悍的生命力,死亡是死也是接續生命的起始。《儀式》裡用一個家族反覆的婚禮與葬禮,去展示整個國族戰後無力的頹敗宿命。那些大島渚電影裡頭數不清的自絕與殉情與強迫他人陪同赴死的情節,以及強暴以及被強暴之後堅韌地繼續活下去的慾望,都使我困惑卻實實在在地感知,那是生命。
對於死的想望是出於生命狂熱,對於性的慾望是因為生命狂熱,對於犯罪的渴望是能夠激起生命的狂熱……。大島渚的電影裡,個個炙熱的眼神使我無法不將所有的情感流向對生命本質的追求。《白晝的惡魔》裡連續犯案的英助,流淌犯罪慾念的眼神使我想起惹內的《竊賊日記》,反反覆覆一來一往的鏡頭亦使我無法不在腦海浮現雷奈的《去年在馬倫巴》。

從初期充滿生存困惑與衝撞的《青春殘酷物語》、《太陽的墓場》,到中期伸張在日韓國人被壓迫的《歸來的醉漢》、《絞死刑》,直至後期明確張望慾念的《感官世界》、《馬克斯我的愛》,大島渚的電影自始至終都訴說著人類在生活的壓抑之下追求生命之上的慾望。遺作《御法度》裡北野武對著暗夜盛放的櫻花樹一劈,散亂零落的花瓣紛飛,那也嘩啦啦地劈向我的心坎裡。
就如刻在大島渚墓上一句他所深愛的短歌:「深海に生きる魚族のように、自らが燃えなければ何処にも光はない。」要同深海裡的魚一樣活著。自己不發亮的話,就只能身處無盡黑暗。大島渚用他的目光,讓鏡頭下個個淡漠的面容之中,眼神有光,眼光有神,身處時代的絕望哀愁而心有燃燒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