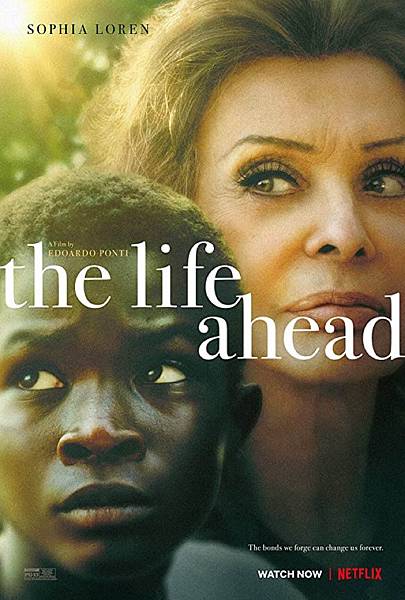如果人生是四通八達的道路,女性自出生的選擇往往就比男性少,成長過程至成年更會被周遭逐漸限縮,如果再加上種族歧視、移民身份、菁英主義的限制,不知不覺,就會被逼到窄巷,關進不見天日。

電影《聖奧梅爾殺嬰案》改編自法國2013年發生的「法比安娜・卡布(Fabienne Kabou)殺嬰事件」,敘述來自塞爾維亞的法國移民蘿倫斯・柯利(葛絲拉基・梅蘭達Guslagie Malanda飾)被控告殺死女兒:她將自己十五個月大的女兒艾莉絲放在法國北方城鎮聖奧梅爾(Saint Omer)海灘上,讓漲潮帶走她的生命。已孕的文學教授與小說家哈瑪(Rama,凱伊傑・卡加梅飾)為了改寫希臘神話的新作《美狄亞邊緣人》,也因與蘿倫斯的身份背景相近,便前去旁聽她的審判。
我們面對刑案加害人,往往先訴諸「善惡」的審判,更進一步則是了解「動機」,但善惡由何而生?動機如何判斷?電影片頭,哈瑪在課堂介紹美國女作家莒哈絲在創作《廣島之戀》「如何敘事昇華現實」時,提到「汙名會存在記憶」,更強調「女性是恥辱的客體」,以此為前提,女性還未落筆就已是罪惡的化身,除非在寫作者有意識的書寫下「備受恩寵」。這正是這部電影試圖呈顯的方式──讓我們看見一個接近真實的女人。過去拍攝紀錄片的導演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曾在訪談中提到:「不可能回到那個審判現場,所以不可能拍成紀錄片,只能用這些素材來編造一個虛構電影。」
電影中所有演員的法庭臺詞是真實的庭審記錄,在拍攝現場,也請來了聖奧梅爾居民參與演出,飾演旁聽民眾,是一種「紀錄劇場」的形式。導演在「紀錄片」與「電影」之間的灰色地帶相會,為的不是窺視或展演,既無意為蘿倫斯柯利脫罪,更無意審判她,而是呈現她的人生,她複雜的內在,讓觀眾在這種游離中,「看見」蘿倫斯柯利從不可知的透明而至認識,再從認識而意識到女性的不透明性。

蘿倫斯柯利是塞內加爾移民,塞內加爾位於西非,自1864年成為法國殖民地,二戰後的1960年6月20日才正式獨立,其中主要民族為沃洛夫族占了全國人口的40%,但其官方語言為法語。蘿倫斯從小父親不許她說母親的沃洛夫語,母親更嚴格要求她能說一口流利優雅法語──每個人生來就得面對一個既有的語言世界,無論種族或性別,蘿倫斯所擁有的都不屬於自己;而相較於語言的慣性與滑溜,得以留駐、經由思想而生的文字更需要嚴格的自我審視,因而她的哲學教授說她善於言辭卻寫作凌亂,嘲笑蘿倫斯想要研究德國語言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而不是「來自她自己文化的人」──這是移民者的困境,要融入當地,就必須捨棄一部分的自己才能躋身文化系統,再被評判「那不是你」。蘿倫斯自小沒有朋友,不擅交際,成績優異愛好文學,父母離異後由父親供她上學,但當她拒絕法律選擇哲學時被斷了金援,只能選擇保母換宿維持生活,跟房東文森太太與堂姐均無法相處,此時24歲的她,成為57歲呂克先生的外遇對象,被他藏在工作室裡直至懷孕,呂克先生絲毫不想負責,發現時已無法處理,還懷疑不是自己的孩子,蘿倫斯回答「別擔心,她是我的」並只能生下女兒,為了照顧她,整整六個月沒有出門,孩子長水痘卻沒有看醫生,付出龐大犧牲的同時,「父親」卻能置之不理,在法庭上更一味只談自己,毫不在乎她的憂傷。
逐漸走投無路的人生,外在矛盾致使內在世界崩塌,她的失敗無法解釋,因而法庭上男性檢察官的鞭笞均針對她的「不完美」質疑她的動機邪惡,這樣的批判如此熟悉且毫不意外,若在台灣,想必亦是絕大部分男性對她的審判。她在法庭透露曾向靈媒求助,聲稱自己被巫術掌控,後發現極可能是負責調查的預審法官訊問時誘導蘿倫斯作此解釋,既呈現了她的孤立無援,亦如哈瑪創作《美狄亞邊緣人》被認為題目太平凡、「美狄亞」少為人知難得讀者青睞般,女性的真實聲音與思想總是缺乏理解的管道,若非蒙上費解的色彩以便貶斥,就是受到重重阻撓。

這部電影除了移民、女性處境,還有母女關係的複雜苦楚。蘿倫斯和哈瑪皆與母親不睦,前者的母親奧黛爾(Odile,Salimata Kamate 飾演)待她嚴格,要求她的姿態教養,為了不讓她遭到輕視,以致關係緊張;蘿倫斯懷孕,每月一次與母親通話,能一眼看出哈瑪有孕的奧黛爾,懵然不知她生下女兒。哈瑪得到母親厭女的愛,生活與懷鄉的疼痛和愛一起給予女兒,對女兒的嫌也是對自己的嫌。母親怕女兒步上自己的後塵而日夜工作,女兒更怕複製、同時必須加倍壓抑因其而生的疼與愛,原該最為相似與理解的母女,造就了彼此無法親近的距離。
蘿倫斯仰慕的哲學家維根斯坦曾言:「對於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虛構的角色哈瑪,正與蘿倫斯的充滿話語相反,影中幾乎保持緘默,感知卻幾乎與蘿倫斯同步,一如女性觀眾的我──看女性電影的好處是,沉默是終於能專注於女性的處境與感受,不若其他不是邊緣就是異化,然後被逼消音;但女性的苦痛平日迴避淡化的,也會在此刻凝聚起來直接撞擊,就像蘿倫斯最後面向攝影機,似是給予哈瑪,但更是給予觀眾的微笑,當時的我心頭一震,彷彿被問著:你懂得了什麼?觀眾感受的未及當事人的十分之一,蘿倫斯一次次的「我不知道」既是對自身行動與意識的身不由己,也是生活加諸給她的、無法擺脫的痛楚與孤獨,使她無人可訴,只能逃避進幻覺與巫術,一如最後她的律師所言,她想隱藏的不是女兒,而是自己。

電影的最後,蘿倫斯的辯護律師分享了這麼一段故事:蘿倫斯曾經夢見未能活過兩歲的女兒艾莉絲,與她同在監獄當中。這樣的夢從何而來?律師從科學解釋母親懷孕期間,DNA與細胞會與胎兒互相轉移,並存留印記伴隨一生,這些細胞被稱為奇美拉細胞:
「奇美拉是一種古希臘的異種怪獸,擁有獅頭與羊身。我們女人都是奇美拉,我們的身上有母親也有女兒的痕跡……我們女人某種程度上是怪獸,是有人性的怪獸。」
至此,殺嬰的、被妖魔化的母親還回人形、獸形,這番話使始終處於防禦的蘿倫斯初次哭倒在律師懷中,也使我們看到更接近真實的、女性猶如困獸之鬥的處境:除了母女相互交織的科學事實,女兒往往害怕自己成為另一個母親,更怕女兒成為另一個自己。來不及和母親、也與自己和解的蘿倫斯,最終只能與女兒在夢裡相伴;但即將成為母親的哈瑪,試著親近原本疏遠的母親,片末三種融合的呼吸,伏在母親膝上撫著肚子的她,還有機會得到母親少一點憎惡的愛,和成為一個少一點懼怕的母親。

看女性電影的時候,自然會想「如果是我的話」。從《美國女孩》、《親愛的童伴》、《正發生》、《家家》、《媽的多重宇宙》,直到這部《聖奧梅爾殺嬰案》,去看各種不同母女關係的衝突與和解,傷痛與殺伐,藉此了解「母親」這個身份、以及自己的極限與可能。尤其最近讀著台灣各種metoo故事,從這部電影裡亦確認了早已存在的恐怖:害怕兒子成為欺壓女性的男性,害怕女兒遭遇任何無法避免的損傷。對我而言,除了避免踏入蘿倫斯的悲劇,更需試著與哈瑪、和這些電影裡的女兒們一樣,持續尋找與母親和/解的可能。